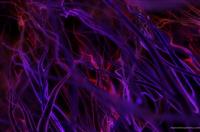梦里依稀慈母影,半眠词阙著诗文。
随而反复记下:身为不系之舟,随波逐流;随波逐流,天凉好个秋。心比黄花之瘦;黄花之瘦,千里念幽幽。
此心何以微衰,有秋雨正滴疏桐,喧哗的楼后楼左的孩子们,仿佛是另外的世界,仿佛一切都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现在,只有那半梦半想之类的眠间,微哀忧愁。
清晨醒来,匆忙一阵,借此中秋探家,如是左手玻璃板上,是母亲当年的一封信,在她故乡许昌贺庄老家的旧厨中,含悲翻出。其时家人太多,不忍阅读,只是打开,依然笑对着大家说:“哎,她真的是了不起,这是她72年写的,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代课教师还未转正,仍然热情高涨,衷心工作。”
当时满座长辈兄弟子孙,颜开荣荣,我自心中悲伤隐隐,不必人知。想到姥姥当年的那床稻草,三四岁的自己,睡在她的脚下,何人能会?念觉传说中母亲当年读书的模样,掩饰着何人能知?只是笑着对在座的妻子说,看看吧,好好学习你的婆子,看看她是怎样工作的;然后和众人交谈乡村的秋天。
在巨大的客厅之内,在一尊领袖雕像的旁边,我的右手是我的骄儿,他在据此不远的高中上学,他是否感觉到他奶奶的存在?他父亲的童年?我写下的《神童的前身》,他是否看过?那地窖内,五岁时带着红薯,母亲绳拉我到地面的光亮;那姥姥后园里,已经不在却长存于心的高大柿树,那树上闪闪如星的黄色柿花。
昨晚饭时,儿子不见我,发现我躲在厨房看书,他不惊讶,只是令我惊讶的说:“快出来吃饭吧,我不看电视,你看新闻吧。”我抹抹汗说,这一点儿马上做完。这是我和儿子冲突又矛盾的好久,我的反思的汗水吧。我为何不能容忍他的错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即使有误,不还是我的错吗?干嘛只看结果,不负责过程?干嘛只有斥责,没有协商?难道要他主动和我协商对话?我的母亲是如何教育我的?
外面夜色滚滚,没有凄凉,只有思念母亲的神伤。
我的家庭和母亲的家族,已经无能而怨哉,余则前途茫茫,却定有光亮,随一切去吧,右边是过去,左边是现在。身为不系之舟,随波逐流;随波逐流,心为柿花之瘦,零落香幽幽。我的母亲;我的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