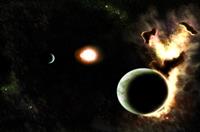从道路纵横起伏的街市,听到故乡的人们纷纷传说,远方的省份,正有一群高人从那里迁徙而来。他们身高过丈,食量惊人,因为本土资源已不能满足他们生存,水资源匮乏,土地资源紧缺,空气质量恶化,粮食生产恐慌,只好离乡奔此以图存。
正在听说这样的困境,却仿佛一瞬间,便看到那通往外省的土街大道上,这样的人群大步而来,他们有着欧洲人的面孔和肤色,其中也有矮瘦而骨嶙峋者同步而行,不断向这里涌来。我看到街道上我们的乡人正聚众欲加抵抗,还有一队身背武器的士兵,给人一些安抚和希望。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只一个人在四处躲藏,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妻子的,在纵横而高低起伏的街道上,或者进入一座楼宇,或者翻下一道生满绿草的斜坡,躲藏着越来越多越来越近践踏而来的巨人,那些侵略者。看不到自己的怯弱或者矮小,矮小和怯弱。
那时的街市上,到处是慌乱的四处逃跑的人群,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天空正有一道巨大的水流一样迅速的流雾,从不知何处的远方滚滚而来,那是白色的辽阔的不际边界的天空,天空下无法眼望至界的白色水流。这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朋友,从远处出现,然后他忽然又已消失。
如此,我从噩梦中惊醒。
起床看表,只有凌晨四时,却再也无眠,辗转反侧,在恍惚之间,仿佛又回到那冥界的噩梦里,下意识之间,我恐惧地握着儿子的手也不能安然深睡,如此这般,熬到黎明时分,听到妻子起床的声响,街道上传来的隐隐市声,才终于回到这通俗的世道。
这样惊恐的噩梦,不止一次,必在酒醉至深于神经处屡现,难道人体的神经是通往另域的道路?那些闪电一样痉挛的神经路线?不知者以为我何忧,知我者知我向愁。苦哉,这一粒世界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