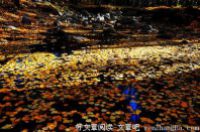《想像的共同體》是一本由Benedict Anderson / 班尼迪克.安德森著作,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380,页数:3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想像的共同體》精选点评:
●有别于大陆版而言,台版的亮点在于附录部分画龙点睛,《旅行与交通》是关于作者本人对于本书全球20多个译本的出版社与译者的评述,很有意思,一方面反证了本书所探讨的主题,另一方面也把作者不喜欢的-ism好好批判了一下。另外在附录中,提出了用爱尔兰与台湾作比的学术问题,非常值得人们深思。从“血腥的星期天”到“二二八事变”,其中的共性和殊性,值得思考。
●其实台版并没有多出多少内容,再读,深深被注释和段子折服。
●补导读、最后一章和附录
●前部分還可以,後大部份太乾澀,完全看到雲裡霧裡,台版最後增加了後記之類,值得一讀
●在作者看来,民族主义首先起源于欧洲殖民地,吊诡则是领导者系殖民者后代,欧洲自诩为民族主义发源地,则是另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神话破除,建构民族想象,则通过共同的语言、资本主义—印刷、“同时”的想象、官方民族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反动)、人口调查(身份划分)、地图、博物馆(被发现与陈列的共同的历史,区别于神话传说)等方式。这些方式有出于自觉设置有时系不自觉模仿,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个个案例,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视野很开,同样,然试以一隅之见统照整体,也见其自负。亚洲特殊性,在此付之阙如,民族主义是否如此“现代”?是否如作者所说首先发生在欧洲的殖民地上?作者一心想驳斥霍布斯邦的欧洲中心主义,然而自己在说道欧洲与拉美双线平行的时间观时,是否也不自觉的落此窠臼?事例皆欧洲与其殖民地(东南亚、美洲),似不言自明。
●歐裔海外移民和報紙推導印刷資本主義的部分特別精彩~~
●很多部分不太懂,还需要消化,其实比较可惜的是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分析在这部名著中基本上是缺位的,尽管其他许多现象在中国也曾经上演,但毕竟我们与欧洲与殖民地,甚至与日本和泰国又都十分不同。附录之中对台湾的期许和分析,包含感情,但是我读得最“懂”的部分~
●被中断的朝圣之旅的美洲的民族主义 印刷资本主义方言化的群众民族主义 对群众民族主义反动“俄罗斯化”的官方民族主义与最后一波群众官方相结合加上殖民地政府“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影响下的民族主义。
●左到受不了。中国版删节的《历史的天使》是本雅明的梗,其中反对把赤柬罪行归为传统遗留,顺带黑了苏、中、柬等“假共产党”。讲台湾与帝国的那段还可以。
●孩子般的思维视角
《想像的共同體》读后感(一):也许想像出来的人口地理分布造成的既成秩序是矛盾纠纷的根源
“如果我们忽视了地图和人口调查关键性的交汇,那就很不明智了。因为,通过划定——为了政治性的目的——“客家人”、“非塔米尔斯里兰卡人”和“爪哇人”等的界线,新式地图帮忙把人口调查的正式机构所想出来的这些没完没了的系列范畴实实在在地分离开来了。而反过来,人口调查则通过某种人口学式的三角测量从政治上填满了地图那徒具形式的地形图。”
《想像的共同體》读后感(二):简评
《想象的共同体》就是那类书:你没读过,但也听过结论无数次。
尽管如此,读后还是有不少之前的望文生义被修正。例如安德森其实很同情一些类型的民族主义;又如他并不认为民族主义是独角兽一般的凭空想象,而是某些人想象一批拥有共同特点的人群为“某民族”(例如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国民根据经印刷资本主义洗礼后的共同方言想象自己属于苏格兰、捷克或斯洛文尼亚),被关注和检讨的不是“想象”本身,而是各种微妙且经不起推敲的想象方式。安德森说:“所有比成员之间有著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个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42)
读之前不知道论述中涉及到这么多欧洲史和殖民地史材料,对相关知识的无知使我经常跟不上安德森的思路。所以未来系统学习后(至少读一遍本书反复征引的Febvre and Martin: The Coming of the Book和Seton-Watson: Nations and States)须重读。
另外,长句子的翻译应该可以处理得更顺畅一点。译文如此颇感费劲。
《想像的共同體》读后感(三):閒書好看,一世感情也不能廢
在物理距離上(不包括負值)經常接觸的親近朋友之間,我有個漂書(傳閱閒書)小圈圈,《想像的共同體》1983年出版後就成為民族主義研究教科書般的範例,去年底後知後覺買到,2017開年,這是我轉給友人的第一本。
我的拍拖技巧止於中學,大學歇了四年,放眼周圍求偶戲碼還是小時候玩膩的老梗,興致缺缺。後來到香港,上了年紀,重新領會契約精神,不“拍”不“拖”,不玩mind game,不擺架子吃飛醋反覆試探左右求證。明白自己要甚麼,遇見的時候大原則投契,心裡感念,原來你也在這裡,如此就是一場好的相遇。
扯遠了。所謂停留在中學的拍拖技巧有甚麼?比如,我們會重新命名一對般配的暱稱,發條鳥小姐和病毒先生,白菜小姐和黑兔先生,模擬成一夥的,來圈定一種情感想象的共同體。當我們學會語言,我們就開始虛構,當我們有了彼此關聯的命名,我們的虛構就有了根基和方向。因為情感是不連續的,脆弱的,受人類腺體分泌的荷爾蒙影響。“持續不斷的愛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瞬間一瞬間的愛”(Barbara Fredrickson)。那些關係中發生了積極共鳴的微小瞬間(micro-moment of positivity resonance)逐漸合理化命名,令想象角色更加生動,令我們的相處模式成熟和親密。
但熱戀的高燒總會過去,“發條鳥小姐”和“白菜小姐”仍是不實存的,是針對不同伴侶虛構出來的;就比如,“香港人”這個民族概念是不實存的,是針對與英國殖民的恩仇和與大陸政經形勢的拉鋸虛構出來的。為何民族會在我們心中激起強烈眷戀——遠比我們的熱戀關係更無畏,更尊貴,就像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德國哲學家)所說:“鄉愁是最高貴的痛苦”;為何民族主義富有歷史宿命感,仿佛天然合理,毋庸置疑,明明這是十八世紀才誕生的思潮,卻風行世界,主導現代國家劃分,成為我們在蒼茫人海體認自己時理所當然的參照系,甚至解釋力強大到足以撐開“民族”的皮囊,去吞下如中國這樣的古老而龐大的文明體系。
作為歷史切身入戲的觀眾——愛爾蘭血統,中國雲南出生,避難回英美接受教育,重新投入東南亞研究——Benedict Anderson的解答精彩而澎湃,以一種逆反的東方主義情懷反思歐洲中心、反殖、反大國霸業、同情小國獨立自治。另外,比照台灣時報文化版,上海人社版刪去的第九章《歷史的天使》,其實也正是成書的誘因,內容雖然闕如,不過篇名取自華特•班雅明,有頗為磊落的普適性,錄在下面:
《想像的共同體》读后感(四):想像的世界之力( power of Za warudo)
(幹為什麼新起的標題這麼中二)
(混作業用讀書筆記)
(不要看簡體字版本 有機會看繁體字版一定要看繁體字版)
(安德森寫的是好高明的學術黑話 把他的學術黑話再用我自己的話講一遍真是無上樂趣)
“想象的共同体”是知名东南亚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一个广为熟知的概念,意在使“民族”这个复杂幽微、众说纷纭的概念从情感和文化的维度得到诠释。他在导论即把“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且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而据译者吴叡人在导读部分所言,这个“主观”定义的创见在于,巧妙地回避了发掘“民族”的“客观特征”的障碍,而直指集体认同的“认知”面向。本书正是在把“民族”作为一个认知主义的基地上架构完成的,是探究“民族”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想象如何成为可能、又是如何在历史中得到演进和显现的。
在细读本书之前,我曾持有对“想象”一词的成见,认为将头脑中的主观之物来作为论证核心是十分不“科学”的作法,然而这个成见在安德森清晰且富有诗性的论述下很快得到了瓦解——“想象”不是“捏造”与“虚假”,而作为民族的共同体真实存在且繁衍不息,“主观”也并非绝对的“主观”,个体头脑中看似抽象不可验证的意识实质上共享一条能够对现实施以影响的链条,它来自文化、来自历史、亦来自于人之造物。本篇读书笔记则希望对本书涉及以上三个部分中令我印象深刻且赋予我新知的内容加以总结。
首先是文化根源,18世纪末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一部分程度上承接了过往宗教作为一种崇高之物、回应偶然并赋予宿命以意义的使命。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两个原有的文化体系:宗教共同体和王朝的解体,当然两者解体的催化剂并不相同。前者是由于新世界不断被人们纳入视野以及宗教神圣语言式微的合力,导致这一共同体崇高而权威的面纱落下;后者则是长期国家中心观的影响下、国家边界模糊及血缘统治混合所带来的君主正当性的消退。然而,安德森在文化根源这一部分着力最多的,是对时间的理解,因为这才是真真切切驻扎在人们头脑之中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是“认知”的投射。他由宗教的宇宙普遍性和现世特殊性引入(前者体现在教众共享的,无法被实际图像或声音完全描绘出的教义;后者体现在教义从上帝传递至教众这一过程中必须经由的媒介),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的矛盾,这一矛盾原本借由垂直化的神谕式时间(无法用理性在水平次元上建立起来的关联)得以解释,然而随着宗教的零落和新技术暨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兴起,一种与“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相异的“同时性”得以成形。崭新的时间观将神祗全知的能力也赋予凡人的读者,“社会”的存在被清晰地认识到、在小说中获得了触手可及的实体,由此“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共同的时间”,并成为了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民族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报纸上印刷的日期、小说中复数名词造就的社会景致都与现实达成了巧妙无声的共通,印刷技术使这两类出版物迅速盛行,沟通虚构与实在的媒介出现在每一个人手中。“一个匿名的共同体”随着水平化的“共时性”而建立。
除此之外我还关注的是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这三样看似与民族主义毫无关联的事物。然而在安德森的视野下,这三者在东南亚正是“殖民地区进入机械再生产时代后随之变化的权力制度”,形塑了殖民地政府想象其领地的方式。就人口调查而言,“人口”的范畴不断靠近以种族界定的范畴,殖民地政府则不断以行政手段实体化其分类观所想象出的“认同”、力图将每一个“人”分配进标签和层级,其真正用意在于对分类做系统性的量化——量化代表着经济之剩余和可武装的人力资源。而在人口调查难以附会的宗教性机构,反殖民的力量在积蓄,因此殖民政府不断尝试将宗教共同体纳入人口调查的范畴。地图的神秘角色则经由泰国历史学家东猜·维尼察古所揭晓,随着旧本土空间观被新西方地理学话语覆盖,地图变得“先于空间现实而存在”、成为“它声称要代表的事物之模型”,边界、领土等新空间概念逐渐为人所知。东猜在其著作《图绘暹罗》中则更加详细地论证了泰国的“地缘肌体”被塑造的过程。地图的符号化赋予其能够被无限再生产的能力,使其能够被作为一种识别标志而在想象中成为反殖民主义的象征。博物馆与考古通过细碎的测量、拍照、重建等一系列手段将被殖民者纳入层级结构中,以彰显殖民政府的正当性与被殖民的“本地人”的在古迹保护层面的“软弱”。根植于机械化再生产时代的考古学具有无限可复制性,它在展示国家机器权力的同时也创造了能够被殖民地人民所采用的能够被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广泛符码。这个过程中“想象”的主体从殖民政府转向了被殖民者本身,复原后的古迹成为“解放后”的后殖民国家国民互相确认彼此民族身份的共享之物,而古迹复原者前殖民政府则悄无声息地退场。
如果说在第二章节我还迷惑于时间观的概念下那种神学与哲学杂糅、虚构与现实交汇的朦胧“臆想”式论证,在靠近全书结尾的第九第十章我则深为这种优雅而富有灵性的论证所折服。“想象”并非“虚构”,而探索“想象”在现实中折射的无数可能才正是理论的迷人之处。21世纪的民族主义与19、20世纪相比诞生了更多新生的元素,也蕴含了更多的力量。错综的地缘政治和挣扎的民族认同之下,“想象”与“共同体”是同样重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