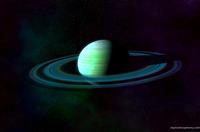第十五回 吴月珍情陷雨坛寺 盖玉秀发难四牌坊
上回说到屈宝驹为了早一点将吴月珍弄到手,在她喝的绿豆汤里下了春药。使她性欲大发,失去了控制,任其他肆意猥亵。就在二人欲火烧心,上床欲作交媾之事时,闻香突然醒了,说她刚才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说:“娘,我刚才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梦见屈媬爷突然变成了一只凶恶的白眼狼,扑在你的身上,要吃你的肉,先咬你的脸,又咬你脖子和这里(她指了一下自己的胸部),吓得我大声哭喊,一下子就哭醒了。”
吴月珍急忙拉好衣裳,说:“屈媬爷不是在这里吗?好好的!”
闻香说:“可能是他又变回来了,娘,没有狼了,我放心了,我睡了。”说罢,倒床便睡着了。
吴月珍慌乱的整理好衣衫,对屈宝驹说:“屈区长,你快走吧!刚才我差一点做了一件丢人的丑事,要是被别人晓得了,我也无脸活在世上了,我对不起我薛大哥,你快走吧!”
屈宝驹苦笑了一声,说:“这件事不怪你,只能怪我不该来看你,造成这么大的事情。唉!也该咱俩有这段姻缘,两个人为什么都控制不住自己嘛。月珍,你休息吧,我走了!”他说完,依依不舍地走了。
吴月珍急忙下床去关上了门,把闻香抱到身边,搂着她,眼泪不禁象一串串雨滴似的流了出来。她恨自己太下流无耻,为什么要生出这非份之想?前次她的身子被区大升偷看了,她都以为这是她一生中的奇耻大辱,现在自己的身子居然被他触摸了,抚弄了,亲吻了,这更是她不能自我原谅的。这种无耻下流的女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找块石头碰死了之。想到此,她又想到了闻香和小双,她们还小,还需要母爱,不能因为自己失去了面子而放弃了对孩子的扶养义务,这样的母亲也是不负责任的,可耻的。思来想去,整整苦熬了一夜,最后决定苟且偷生,忍辱负重地活下去。和屈宝驹斩断情丝,发誓以后不再往来了,回到吴家咀安心做一个贤妻良母,改变命运的事情就等儿女们长大以后,让他们去做吧!外面的世界大,风浪也大,危险更大,一个女人要避过这风浪,逃脱这危险,难呀!何苦呢?
再说屈宝驹离开了珍玉阁,在区公所里找了一乘床和身躺下,也一夜未曾合眼。他想到的却是吴月珍的女人味太浓,浓得叫男人失魂落魄。可惜还没有入港,便被闻香的一个恶梦惊飞了。他惋惜,他遗憾,他又百般思恋,各种感情交织,他彻底失眠了,眼前总晃着一团洁白、柔软、香暖的肉蒲……
第二天早晨,吴月珍带着女儿去了嫦娥山庄工地上,见到丈夫,心头还咚咚直跳,也不好意思多说话。
薛振川见妻子精神恹恹不振的样子,关心道:“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听说你昨天喝醉了,本想来看你的,哎,我也喝醉了,一点也动弹不得,不是永泉他们给我想方子醒酒,恐怕现在都爬不起来了。唉!真对不起你们母女俩。”
闻香说:“爹,我屈媬爷他去照顾了娘的,还专门给娘熬了绿豆汤喝。”
薛振川说:“哎呀,五兄弟这个人待人就是真诚体贴,想的也周到,让他费这么大的心,我们应该好好记住他的大恩大德,闻香,二天你挣了钱,都该好好报答你干媬爷才好。”
吴月珍听了,心里立即涌出一股酸楚之情,鼻子一扭,差点儿流出泪来,也不好再说什么,愣了一阵,说:“大哥,家里事情多,我该走了。”
薛振川对妻子招呼道:“等一等!这是屈五兄弟送给你们母女二人的金银首饰,带回去吧!哎!我们结婚都十七年了,我从来没有给你买过这么贵重的东西,既然有了,也该打扮一下。”
“不,我……你,他的东西,我们不……”吴月珍有口难言,不好说下去,勉强收下了。于是,吴月珍辞别了丈夫,背着闻香回家去了。
回家的路上,她仍暗暗咒骂自己的堕落无耻,对不起爱她疼她的丈夫。看看到了雨坛寺,心想:自己昨天晚上犯下了罪孽,应该向菩萨忏悔,改过自新。这样,菩萨也许会饶恕自己,给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她牵着闻香进了山门,只见山门大坝的黄桷树下、大榕树下、大槐树下全坐满了逃荒乞讨的灾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个面黄肌瘦,蓬头垢面,见上山来烧香拜佛的施主,便蜂拥而上,伸出一双干瘦如柴的手来要钱讨吃。几个值门的和尚大声吆喝,挥棒乱打,也打不走他们。
吴月珍本是个糍粑心肠,哪里看得这般苦戏,除了香炷钱,全都散给了乞讨之人,还把带回来的杂包也全散给了老人和小孩。
吴月珍买了香炷,进了正殿,见第一个内操坝上的右边搭了一个丈余高的木台,木台上设案摆钵,焚香化纸,四个老僧端坐上方,头顶烈日,微闭双月,手持佛珠,念念有词。这就是雨坛寺在设坛求雨。神坛下面有无数的求雨灾民,纷纷向神寺叩头作揖,而后向一个陶缸里扔求雨钱。
吴月珍身上也没有钱了,只好把屈宝驹送的金首饰扔进了陶缸,然后径直进了大殿,向雨神菩萨叩了三个大礼,烧了一炷香,尔后又进了第三个大堂——观音殿。这里是她要来的主要地方。这里面也有一个内操坝,左边搭了一个戏台,现在正在演连本戏《王十四娘打叉》,这台戏共有一百本,现在已唱到第七十多本了。吴月珍无心观看,进了观音殿,向观世音菩萨虔诚地忏悔祷告。她念完了,正要起身离去。
从旁边走来一个老方丈对她施了一个礼,念道:“阿弥陀佛,欢迎女施主光临寒寺。请女施主再来抽支签吧!也许能给你解除许多的困惑。”
吴月珍虽说从小就信神拜佛,但多数时间都是在家中焚香燃炷,烧纸化钱,除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三次观音庙会赶赶庙会外,平时很少进寺庙去,跟和尚就更没有打过交道了。听和尚一问她,心头就非常紧张,连忙说:“我不抽签,也不问卦,我只是来烧钱化纸,求菩萨保佑的。闻香,走!”
方丈合撑念了一个阿弥陀佛,说:“女施主且慢,我还有几句话必须要对你讲,瞧你脸上正桃花灼灼,艳气浓浓;思心如春,情意如迷。一定是碰上了男女间之难解难消之忧事了?再看你印堂之间,黑红之运正交错争夺,如不及时解开这个预兆命运之疙瘩,必将有一场血光之灾降临于你和你全家。丈夫惨死,儿女离散。家破人亡,永受艰难。”
听他这么一说,吴月珍顿时心慌意乱起来,急忙问道:“大师,那我该怎么办?”
方丈双手一合,念了声”阿弥陀佛”,将手一指对面,说:“请女施主随我来!”
吴月珍迟疑了一下,还是随方丈进了一个小佛阁,她叫闻香在门口坐着等她。
待吴月珍坐下,方丈仔细观察了她一阵,又闭目念了一会儿什么,才睁开双眼说:“女施主貌若天仙,本是月中的嫦娥转世,可惜,送子观音送错了人家,让你受了三十几年的苦楚。这下子好了,过了今年,你将有一个人生大转折,只要把握得好,便是大富大贵,大吉大昌,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和福禄吉祥啊!”
吴月珍听了,心中一喜,问道:“这是真的吗?”
方丈严肃地说:“老衲一生为人解忧排难,造福于民,佛家圣地,岂有诓谝之理?女施主认识字吗?”
吴月珍答道:“刚认识了几个字。”
“好,你脑子不要想,拿起笔来,随便在这上面写一个字,我便可以替你仔细分析,得出这祸在何处,福在何方?如何避祸,如何迎福?”
吴月珍拿起笔来,略一深思,写了一个人字在白纸之上,呈给了方丈。
方丈说:“让我看看,你这人字签有没有。”他拿起签盒,摇晃了好一阵,念道:“人字签,快出来,女菩萨,福气来!女施主,你随便在里面抽上四根吧!”
吴月珍的心情很紧张,希望能抽到一枝枝全是好签。她选抽了四技。恭恭敬敬地交给了方丈。方丈将签打开一看,高兴地说:“恭喜女施主,这四枝签都是人字签,又全是上上签。真是命运全是前生定,半点不由今世人呀!但是这四枝签也可以说是下下签,它道出了你许多的不幸,让你一时难以接受,甚至产生抵触情绪,生出新的一些祸端来。”
“这,我不明白!”吴月珍真听糊涂了。
“你不明白不要紧,待老衲详细给你作一番解释。这签上面有四句话,是菩萨送给你的,也是你的命运决定的。不管上面说的是福是祸,是喜是悲,是苦是甜,这都是你人生的真谛,生活的妙谛。相信它,才能遇难呈祥,化险为夷,万事如意,否则就相反,刚才我已讲了。”方丈耐心地讲解道。
吴月珍只得说:“哦,我明白了,你念吧!”
方丈拆开第一枝,说:“我先念第一枝!”
一撇一捺认作人,好比两足把道行。
一生要走多少路,坎坷曲直总不平。
方丈问:“这意思你明白吗?”
吴月珍说:“这句话很清楚,我懂,人活在世上,总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有灾有难,有疾有病,这是常有的事,也是上天定死了的。请大师念第二枝。”
方丈说:“女施主真聪明,好!那我念第二枝。”
人字添一认作大,好比枷锁颈上挂。
大字与你不同老,二九之年须再嫁。
“这……!”吴月珍摇了摇头,表示不明白。
方丈平静地说:“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吧,你听了之后,一不要着急,二不要生气,不然就要危害你全家人的性命。人表示是你本人,一表示是你现在的丈夫,两个字合起来为大,大也指你丈夫,他的排行一定是老大?”
吴月珍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说:“对,他就是排行老大。”
方丈仔细的说教道:“那就对了,大字今年有血光之灾,杀身之祸。轻一点也有牢狱之苦。他已戴了一个大枷锁。再说大字与你水火不相容,金木不相生,不能让别人喊你大嫂,大娘。人能配二念作仁,仁字当先义为重,儿作相来女为雄。人字配三仍为仨,仨人同行可作师。人字配五仍念伍,队伍强大多威武。人字配九念着仇,仇恨仇杀难以休。人字配十仍念什。什物零零杂无章。看来这人字只能配二,配三,配五。你只能作二嫂,三嫂或五嫂,或者只能作二娘,或者只能作二娘,三娘或五娘三嫂或五嫂一旦你作了大嫂,大娘,便对你有百害而无一利。你和丈夫的姻缘只有十八年,二九一十八,十八年后你必须另嫁他人。二次出嫁,珠联璧合,恩爱无边,百年似锦,洪福齐天。还可以保你以前的丈夫平安无事,儿女不受伤害。否则,菩萨就会降罪,让你夫死子亡,全家遭殃。”
“不,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是骗人的。”吴月珍从椅子上忽地站了起来,激动地喊了起来。
闻香听见母亲的惊叫声,急忙冲进屋里,问道:“娘,你咋个哪?”
吴月珍害怕女儿听见了不好,急忙掩饰道:“没有啥子,你出去吧,不要再进来了,冲撞了神灵不好。”
闻香看了一眼和尚,指着他大声说:“老和尚,不许你对我娘胡说八道,如若不听,我二天定要杀了你的秃头。”
吴月珍急忙把女儿拉了出去,说:“闻香,不要对人没礼貌,快出去!你胆子也太大了,菩萨你都敢得罪吗?就在这儿坐倒等我!”随后又进了禅房,对方丈说:“大师,小女儿人小不懂事,不要见气哈!你继续说吧,我相信你的话,大师!”
方丈也不生气,轻轻地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孩童之言,我们是不会计较的,真的不会计较。女施主,你也切莫激动,这是签上所言,神灵所定,千真万确,不可怀疑。怀疑神佛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女施主,下面还有两首,请听完之后,再作摈斥不晚。女施主,请坐下!听老衲再念。”
吴月珍只好强忍难以平静的涌动的情绪,坐下来,听方丈继续念签。
方丈继续念道:
人字加口念作囚,一女二男心中留。
一个耿勇感情深,一个嘴巧最风流。
吴月珍听罢,不好再说什么了,她目前的心境不正是这样的吗?这还有什么可强辩的呢?难道菩萨真晓得自己的一言一行吗?
方丈也没有问她,继续念第四枝:
人字加二念作天,老天在上不可瞒。
大小事体全知晓,道尽方可保家安。
吴月珍一听,更吓得魂不附体了,心想这寺中的菩萨就是灵验,大小事情他都知根知底,一清二楚。不能隐瞒,否则就会株连全家人的生命安全。自己死了不要紧,可千万不能死了自己心爱的丈夫和可爱的儿女们啊。心头一阵发酸之后,便把和屈宝驹如何从相识、相知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方丈。最后仍责骂自己鬼迷心窍,伤风败俗,差一点儿丧失了自己的贞节,败坏了屈宝驹的名声。
方丈听罢,心中好一阵欢喜,屈宝驹要自己帮助办的事情和自己要办的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了。但脸上仍然很冷峻地说:“从签上所言,这不是你的过错,也不是屈宝驹的过错,你千万不要再自责了,自责多了也会危害家人的。这是前世姻缘定死了的,风水轮流转,谁也不能改变。想不通不行,必须想通,否者,我前面已经讲了。女施主,你和前夫的姻缘已经完结了,第二个丈夫已经出现了,女施主,恭喜你了。”
吴月珍惊慌失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怔了好半天才说:“不,大师,我不能离开我薛大哥,求求你,重新给我看一看!”
“阿弥陀佛!姻缘本是前世修,不用争来不用求。你薛大哥虽然好,但缘份已尽,再一起生活下去,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呀,你若是真正的爱你丈夫,你就应该及早离开他,让他有一个生存的机会。你和屈宝驹是金玉良缘,莲荷并蒂,天作之合,伊美千秋。”方丈说完又闭目念经了。
“不,我现在和将来都是薛振川的妻子。大师,你替我想一想办法吧!”吴月珍哀求道。
方丈说:“看来你和薛振川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我也为之感动,我替你求求菩萨吧!可是要花一笔钱呀。”
吴月珍一听有希望挽回,“卟咚”一声跪倒于地,向方丈叩首道:“多谢大师!只要你能挽回我和薛大哥的姻缘不散,保住我一家人团团圆圆,不管花多少钱,我想办法出。”
方丈觉得为难,但又装出十分热心的口气说:“唉!求人难,求菩萨更难呀。我准备为你念上七七四十九天的姻缘经,感动观音菩萨,让她把你们的姻缘延长六十年。这样下来,香蜡纸烛,灯油钱大概要六千六百六十六块钱。十天之后必须交来,逾期不交齐,我也无能为力了。”
吴月珍心头一惊,六千六百六十六块钱,这么大一个数,家里哪里有这么多钱哟?现在家中全部只有五千块钱,其中还有几千块是屈宝驹送给闻香的,因心存种种担心一直不敢用,其它的钱是她一分一分积存起来,准备讨儿媳嫁女儿用的,女儿兰花已经年满十六岁了,明年便要出阁了,嫁妆陪奁少说一点也要五六百块钱,福娃讨婆娘费用就更大了,修房子,置家具肯定要花去上千块钱。这些也顾不上了,先挽救家庭不破裂再说。可是还要差一千多块钱怎么办呢?不能得罪大师,先答应下来再说。于是答应道:“请大师放心,十天之内我一定把钱送来!”
方丈叮嘱说:“菩萨面前无戏言,十天内一定把钱送来。错过机会,我再也帮不上忙了。还有,你回到家后,千万不要背上包袱,稍有伤感,就将前功尽弃,求神不灵了。也不要告诉丈夫和儿女们,他们会破坏你的计划的。若屈宝驹今后要来找你,你不能不予理睬,而应慷慨大方,以欢悦之心与之应酬。至于他,菩萨自会教他如何做人的,只能由神佛劝之。切记!阿弥陀佛!”
吴月珍点了点头,站起身来,昏昏沉沉回到家中,当即翻箱倒柜寻找东西,
女儿兰花觉得母亲举止异常,奇怪地问道:“娘,你在找什么东西?”
“我,不关你的事,你做饭去吧,弟弟妹妹快放学了。”母亲本想一句话把女儿支走,不让她知道这些事情,想了一下,又说道:“噢!兰花,娘有一件事情想问你一下,假如明年永泉要与你结婚,娘没有钱给你做奁陪,你会不会有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呢?有多少钱置多少东西,我不会怪你的,永泉也不会有意见的。娘,你问这么早干什么,我还不晓得望永泉的心定没定死哩,他至今还叫你师娘,你叫他改口,他一笑了之。”兰花有些埋怨又带责怪地说。
吴月珍说:“他过去叫惯了,一时改不过来,你也不要责怪他。我看他是最喜欢你的,这次摆席的糖,他一个没吃,全给我了,本来是带回来给你们吃的,结果全散给了雨坛寺那些灾民去了。哎,只要你不怪当父母的,娘心里就不难受了。不过不一定,只要你爹在,也许能挣更多的钱,给你置个双铺双盖,床柜衣架所有行头全都做齐,让周围四邻的人都看一看,咱薛家的姑娘还是有面子的。非要他屈家才有钱吗?”
女儿走到门口,又退了回来,迟疑了半天,才说:“娘,我有几句话,早……早就想对您说了,您愿意不愿意听,不晓得?”
吴月珍见女儿说话吞吞吐吐的,责备道:“有什么话就讲嘛,含言不吐的我看不惯。”
兰花大着胆子说:“我说出来你不要骂我呦?你二天还是少和屈区长往来一点好,我都听见有人说闲话了。说屈区长迷上你了,你也看上他了……”
“不要说了!”母亲打断女儿的话,干涉道。又停了一会儿,说:“从今天起,我和他再不往来了,真的,娘已下了最大的决心了。”
“娘,你别生气,我二天再也不说了!”兰花小心翼翼地进了灶房煮饭去了。
桂静娴在嘉门镇只住了一天,便要回成都去,提出要屈宝驹送她。屈宝驹虽然不大情愿,却不敢推辞,骇怕父亲骂他,只好硬着头皮去了。桂静娴等人来时是坐船从成都经乐山、叙府、泸州到嘉门的。回去时,却要坐轿子回去。坐轿子虽然没有坐船那么颠簸,但是却很慢,路上走了三天,又在成都住了两天,回到嘉门镇时,已是第七天的日子了。他心中挂念着吴月珍,进办公室呆了一会儿,便想去吴家咀看她。正要关门出去,团总老禹却送来了一大摞子状子。据老禹介绍,这些讼状都是告雨坛寺广智和尚的,说他以救济灾民为名,大肆骗收强要他们的钱粮,使得他们朝不保夕,日子越过越艰难。这些告状的人几乎都是嘉门区各乡各保的殷实人家,也是嘉门区的纳粮交税的主要大户。把他们惹毛了对政府肯定是不利的。屈宝驹对雨坛寺的做法非常不满,对广智和尚更是十分恼火。这个小小的雨坛寺,本应该是积德施善之地,自四叔突然出门远游之后,这里就接二连三出些怪问题,先是搞全面派捐,被制止后,现在又开始搞上了傍大户的勾当,尽给他添乱子,找麻烦。他心头明白,这广智和尚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巧立名目,搜刮民财,是得到了父亲暗中支持的。不然他们不敢这般横行霸道,乱闯乱进。还有人看见雨坛寺的和尚们最近在大街小巷的饭馆酒店里,吃肉喝酒,划拳打码,故意招摇过市,伤风败俗,破坏戒规。不仅这样,还蒙拐诱骗,奸淫敬香妇女及逃荒在寺内的姑娘和媳妇。这种人竟能当住持,清雅圣洁之地岂不成了藏垢纳污的污秽之地了吗?他早有心要铲除这根恶瘤毒根,无奈父亲对他屡有招呼:“你娃儿不懂,广智和尚当雨坛寺住持,对咱屈家是有一百利而无一害的。他比你四叔强十倍。你四叔是手臂往外拐,煽动外人整我们,而广智和尚却一心一意为咱屈家卖力。咱屈家能脚踏泸县、荣昌,手伸川东南,除了上面有人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神明护佑。这神明是谁?你以为是那些石头打的、泥巴塑的菩萨吗?不是。而是寺里那些披着驾裟的和尚们和观里的那些道士们。菩萨神像那是死的,他们才是活的。你把他们限制死了,不给一点好处,他们是不会替你卖命的。你娃儿要想当稳这区长,干成一番大事业,离不开这些三教九流哟。屈宝驹耳在听,心头却在想:这话未免太耸人听闻了,一个刁秃和尚、披发道士还能左右天下政局吗?!可那天晚上给他春药之后,才领教到这秃头和尚的不寻常。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窥视之中。说内心话,他虽然憎恨这种卑劣的行径,但毕竟帮了他一个大忙,使他获得了与吴月珍亲昵的一次机会,让他从心理上得到了一次很大的满足。提起吴月珍,他心头又巴心巴肠地想起了她。一晃七天过去了,不晓得她现在如何?是胖了还是瘦了?是在想他还是在恨他?他在这七天的日子里,虽然颠沛于轿上,身边还有桂小姐陪同,但却没有割断他对她的思念。昼思夜想,归心似箭。他决定先去一趟雨坛寺。顺路去一趟吴家咀,看望一下他日思夜想的狂恋中的情人。
他先去了嫦娥山庄,见到了薛振川,也没有询问工期情况,只见下堂屋的瓦已经盖好了,只说了一句:“嘿!你们的速度真快哟!”接着又说:“大哥,我要去兴隆场检查旱情,你带不带信?你一直没有回去过吧?”
薛振川说:“我们太忙了,八月十五你要办喜事,我们不敢耽误呀。只是你嫂子带了一个口信来,叫我带一点钱回去。我有几个钱都打发了外地来的灾民了,你刚回来,工钱又没有领。我也不晓得她要钱干啥子?”
屈宝驹说:“哎,大哥你放心,我先给你带一点回去,五百块钱够了吧?”
“够了,够了,你去问清楚,她拿钱干什么?我晓得她不会乱花钱的,一定有什么急事。你看,我又不能走,代劳你去看一看了。你也劝大嫂几句,叫她不要太劳累了!”听见有人喊他,薛振川应道:“嗳!听见了,马上来!五弟,对不起,不陪你了。”说完,便爬到房子上去了。
屈宝驹目光送走薛振川,心头泛起一股股涟漪,心想:“薛振川大哥为了我的新房,没日没夜地干,我却去胡思乱想人家的爱妻,这也太狼心狗肺了吧?应该打掉这念头才对!可转眼又一想:吴月珍这么一个千古绝色的女子,不应该嫁给一个没有地位的石匠木匠,一个只晓得干活的黑大汉。她应该重新获得新的婚姻,建立新的家庭,做一个新的女性,来展示她的风采,新的魅力。想到此,他又觉得和吴月珍相好,是心安理得的事,不应该受到人们无理和自己良心的谴责。于是,便回到珍玉阁,拿了五百块钱,叫上老祝老季二人,便到兴隆场去了。
一路上,屈宝驹见沿途的旱情越来越严重了,现在的濑溪河是彻底干透了,成了一条宽阔而弯曲的大公路,原来车到田里的水,栽秧后经太阳没日没夜的照晒,可怜得一点水也被它争(蒸)去了,秧田一块接一块,全干裂了。人们只有眼巴巴看着秧苗一天天枯黄,最后枯死。人们赞美的”天干三年吃饱饭”的嘉门区将成为历史,米粮之仓也将变成缺粮之乡哪。
屈宝驹不敢想下去,也不敢面对现实,只是心头在盼望老天爷快些下雨,以解苗危、民危和自己的官危。正想得浑身不自在之时,听老祝问:“屈区长,雨坛寺到了,现在去不去?”
屈宝驹说:“既然都来了,就去看一看。广智和尚若真有此事,你们就对他不要客气,该讲就讲,该批就批,决不要让步、迁就,让他逍遥自在。他若不服,你们可以组织人把他撵出雨坛寺去。”
二人听了,不敢答应。屈宝驹觉得奇怪,停下脚步,回头问道:“你们为什么不答应?”
老祝说:“屈区长,你不是不晓得,广智和尚是你父亲的拜把子兄弟,我们见了他躲都躲不赢,还敢去撵他?你不要给我们出难题了!宁愿叫我们去受刑都可以,也不愿去惹这毛驴头。屈区长,你千万不要叫我们去坐蜡台哈!”
屈宝驹不屑一顾的说道: “一个小小的和尚就这么可怕吗?告诉你们,这次我是背着我父亲,专门来收拾他的,我才不怕他哩。背书背不好,就让他连爬带滚。走一个,少一个祸害,到时候,你们听我指挥。”
两个人不好得罪顶头上司,表面上直应承,心里头却在盘算如何去敲打这边鼓。
屈宝驹本想打广智和尚一个措手不及,哪知他们人刚一踏上山门,广智和尚已亲临山门外迎接他们来了。他合撑而道:“欢迎区长大人光临敝寺!愚僧在此等候多时了。”
屈宝驹暗忖道:这家伙真狡猾,你怎么晓得我们今天要来呢?看来这和尚真会神机妙算,不是一般之人,今天须小心处事,不然打蛇不死,反被蛇咬,告给父亲,还得挨日诀。于是客气地应酬道:“劳驾大师久等了,我们今天去兴隆场办事,路过贵寺,想随便进来看一看。请问僧叔,你是怎么晓得我们今天要来贵寺的?”
广智和尚合撑道:“昨天晚上我占了一卦,便知晓区长贤侄今天要来敝寺查询,而且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而来。不要怪愚叔多心,请贤侄先看看情况再说吧,那时你再如何惩罚本僧,老衲决无半句怨言。”
屈宝驹也没有说什么,便径直进了山门,来到寺院大坝前,只见地上齐刷刷跪了一大片灾民。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人人愁容满面,伸着一双枯黄黑瘦的双手,捧着大小不一、新旧不一的土碗陶钵,一起高声喊道:“区长大人,行行好,救救我们灾民吧!”那声音哀转凄凉,催人泪下。
看到这个情景,屈宝驹对雨坛寺和广智和尚的满腔怒气一下子消了一大半。原来这小小的雨坛寺竟汇集了这么多的灾民呀,凭他们寺里的储存能养活上千个灾民吗?有钱之人不出一点钱粮来赈救他们,难道让灾民们活活饿死不成?我们家不是也出了几百石粮食吗?想到此,他对那些喊冤告状的人,却有了另外的看法,认为这些大户人家是为富不仁,见死不救,有些不尽人情了。
广智和尚见屈宝驹的愠色有些减轻,叹息道:“里面还有许多!敝寺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可僧多粥少,不,应该说是灾民多,粮食少。车薪杯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呀。向大户人家化缘,可他们哪里像你父母亲那样慷慨大方,一下子就出了五百石。他们不出倒罢了,竟还攻击谩骂我们寒寺巧立名目,以救灾为幌子,强取豪夺他们的财产,把我们比喻成虎豹豺狼。事实胜于雄辩,这情景屈区长你是亲眼看见了,我们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么坏?”
屈宝驹听罢,肚里所存的一半气恼已全消了,说:“攻讦之言不可信。僧叔,我决不会偏听偏信,只听一面之词的。灾民大量涌入贵寺,是对贵寺的无比信赖,但对你们的赈济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你们不辞幸苦,多方筹措,千方百计救济他们,坚决不要饿死一个灾民。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乡区政府,我们一定大力支持。对你们今后的行为,只要是对灾民有利,你们可以大胆去做,我们决不乱加干预的。”
广智和尚脸露喜悦,合手说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屈区长真是一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我代表滞留暂居在敝寺的全体灾民向你致谢!”
屈宝驹心想,到这里来一次也不容易,何不乘此机会到四叔的寮室看一看,也扫除人们对智聪大师去向不明所说的种种存疑。广智和尚听说屈宝驹要去看他四叔的寮室,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紧张,却故作爽快地说:“好的,我现在就引你去。”边走边说:“你可能在外面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说智聪大师是被我们谋害了!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这智聪大师是你父亲的亲兄弟,又是你亲叔爷,我们敢加害于他吗?再说,智聪大师是你父亲的亲兄弟,又是你亲叔爷,我们敢加害于他吗?再说,智聪一生清贫如洗,没有半文余钱,我们害他有何作用?区长,你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对!我也有你同样的想法。”屈宝驹点头应道。
几个人来到智聪大师的寮室,广智和尚令一个小沙弥开了门,屈宝驹推门而进,只觉得这屋子冷浸浸的,灰尘已铺满了桌椅。神龛处突然卷起一股旋风,直扑屈宝驹,弄得他睁眼不开,忙退了出来。
广智和尚说:“这房子好久没有人住了,霉气太重,还是到我敝舍坐一会吧!”
“不,我想回四牌坊去一趟。”屈宝驹说罢欲走。
“贤侄,请稍等片刻,我还有几句要对你谈。”说话间,广智和尚用眼睛瞟了老祝他们一眼。
屈宝驹会意,对老祝等人说:“老祝,寺里的事今天就算处理好了,你们回去写个通知,要求全区各乡保的富户人家积极行动起来,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全力支援背井离乡、逃荒要饭之灾民。若有反对者,他们今后的利益不受我们保护。你们回去吧,也许我要明天才回去。”
老祝二人答应后,回嘉门镇去了。
屈宝驹跟广智和尚进了一间禅房,这是广智和尚的寮室,小巧而隐秘,把外面喧嚣的世界陡然隔断了,显得格外宁静。
广智和尚待屈宝驹坐下,说:“公事公办,私事私办。刚才公事办过了,我现在对你再说一点私事,这事本不属于我关心的范围,但出于对贤侄的爱护,也不得不说出来,不然,我就对不起你父亲对我的大恩大德了。”
屈宝驹说:“僧叔,请不必客气,有什么话请说吧!”
广智和尚说:“愚叔虽然现在为僧,从小跟刘神仙学《易经》,占八卦,能算命,能看相,一个人的生死运程能预测得八九不离十。”
屈宝驹说:“这个我听我父亲夸过你。所以那天叫你带人去请神,按理说,那应该是道士端公的事。”
广智和尚说:“不,你父亲请我去除了请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替你看一个人的相。”
“替我看相!”屈宝驹紧张了一下,问道:“看谁?”
广智和尚微微一笑,说:“你未来的夫人桂小姐呀。”
屈宝驹松了一口气,让不住还是问了一句:“她的命运如何?”
“这叫我咋说呢?”广智和尚欲言又止。
“但说无妨!我对她也不是很在意的。”屈宝驹催道。
“有你这句话,我敢说了。”广智和尚故作玄虚地说:“但我说重了,请贤侄你千万不要生气!桂小姐右嘴角有颗黑痣,那是一颗克夫痣,你若与她结婚,最长不出三年,最短也许一个月不到,你就要染病而死。”
屈宝驹吃惊地问:“有这么严重?你对我父亲说了没有?”
广智和尚说:“我暂时未对他讲,我要先对你讲了以后再对他讲,以免叫你措手不及,接受不了。”
屈宝驹沉默了片刻,问道:“那我该怎么办?”
“第一你是坚决不能和桂小姐结婚的。第二你可以另选一个和你八字相生的、前世姻缘定死的女人作妻子。我已是一个出家之人,对红尘间男女之风流事本不应该过问,但为了贤侄的前程命运之大事,我就只有得罪佛主,为你指点迷津了。”广智和尚端详了一阵屈宝驹后,又继续说:“察看你的脸色,你对她已经是迷入心窍,爱入骨髓,对她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牢记心头,难以抹去。如今已是日思夜想,吃饭不香,睡觉不宁,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闭眼就来,睁眼不去,独钟独情,一个心思想着她。对其他女人视若芥草,无论她姿色有多么美,地位有多高,家产有多厚,你均不感兴趣。你说我看得对不对,准不准?”
屈宝驹睁大双眼,惊奇而佩服,僵直地点了点头,没有什么话可说。
广智和尚继续说:“你虽然对她有百般爱慕,她对你也颇有倾心,可惜她是一个有夫之妇,况且她对丈夫是恩重如山,情重似海,爱夫之心,坚如磐石,除了其丈夫,其他一切人均无缝隙可钻。虽然对你启动了一下情愫之窗,也只是你对她做了一点手脚,不是她的本意。要想真正得到她的芳心与爱心,这是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恒心的。最后还要使出一些狠心的手段。否则,你将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屈宝驹冲口说道:“不管有多大的难关,我也要得到她。”
“唉!你不得到她也已经不行了,你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相思症。你由于思念过度,已积思成病。刚才我对你讲了,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到晚上入睡,便与她在梦中交欢,一夜数次,次次遗精不断,一则要酿成强中之怪病,二则要造成阳萎之丑病。久而久之,难以治愈,便成了一个废人。你在三个月之内,若不与真人媾合,以阴精弥补阳气,你就会精尽身亡,变成一具骷髅。这正是古人说的:芙蓉白面,不过带肉骷髅;美艳红妆,尽是杀人利刃。”
屈宝驹听罢,起身向前两步,跪倒在广智和尚跟前,说:“僧叔所言字字是真,句句属实。请大师设法救救愚侄,无论你要多少报酬,愚侄一定倾囊而出。”
广智和尚扶起屈宝驹,说:“贤侄请起,愚叔一定为你帮忙。不过,愚叔是出家人,从不爱财,只要你们幸福美满,我就高兴了。”尔后又严肃地问道:“你再考虑一下,你最后是选择桂小姐还是选择她?”
屈宝驹干脆地说:“这不容考虑,我本身喜欢吴月珍,肯定选择她。”
广智和尚警告般地说:“啊!可她男人不是你的朋友吗?自古便有朋友妻不可夺之训导呀。再说,薛振川也不是一个莽打杵、二杆子,两句话便哄得他把老婆都卖了。他不仅武功好,群众威信也高,夺他的妻子,比高衙内夺林冲的妻子还难十倍哟。”
屈宝驹祈求道:“我并不愿意做这个不光彩的事情,被人千古唾骂。可是,薛振川存在一天,吴月珍就会跟他一天,做他的妻子,而不做我的妻子。请大师想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既不伤害朋友,又能将吴月珍娶到手。”
广智和尚沉呤了一阵,说:“顾其仁,不得起歪心;顾其义,不得加害朋友。要在这两者中间找一个两全其美之策实在不容易。如黑白选其一也,要么无毒不丈夫,割断朋友之义气;要么恋情心中留,舍弃对她的追求。”
“不,我宁愿得罪朋友,也不能放弃对她的追求。”屈宝驹已经情魔入髓,不可控制,直接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广智和尚说:“这就好办,其实我已开始为你做准备工作了,除了春药,还给吴月珍戴了一副精神枷锁。据我所知,吴月珍对其丈夫实在忠心不二。要把她真正征服,就必须用她的致命弱点。打蛇伤七寸方可奏效。”
屈宝驹问:“她有什么致命的弱点?”
广智和尚得意地说:“她信神信菩萨呀,利用这一点便可以众心理上征服她。等几天就有好消息了。”
屈宝驹心中一喜,又跪了下去,拜谢道:“多谢僧叔的鼎力相助,我和吴月珍完婚之日,一定请您老人家坐上席。”
广智和尚平淡地说:“出家人不坐你们的上席。”
屈宝驹说:“我一定出许多钱,把雨坛寺装饰一下。”
广智和尚仍然平静地说: “我也不强求。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五月初四那一天你把桂小姐叫来敝寺,我要对她算一卦,让她主动放弃你,不让你背任何主动离弃她的罪名。”
屈宝驹满口答应道:“是,我一定叫她来。”
广智和尚挥了挥手,说:“去吧!有什么好消息我会告诉你。”
屈宝驹千恩万谢,离开了雨坛寺,先到四牌坊去了。
进了四牌坊庄园,才听蒋贵善告诉他,他父亲带着侄孙女到荣昌县城去了。今天是他亲家葛富城的六十大寿,屈宝驹、葛丽华带着儿女们昨天就去了,还把戏班子也带去了,可能要耍三四天之后才可能回来。
屈宝驹不愿在此久留,正要出大门去,只见一个穿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女人从侧边的院子快步走廊走了出来,并主动叫住了他:“哎!五兄弟,先别走,我正有事要找你哩。”
屈宝驹一看是大哥屈宝骏的五姨太盖玉秀,不得不停下脚步来,问道:“五大嫂,你好!找我有什么事吗?”、
“非要有事才找你吗?你当兄弟的陪当大嫂的说几句话就丢了你的面子是不是?”盖玉秀身穿一件红绫短袖旗袍,披着长发,摇着一把荣昌绸折扇。她来到屈宝驹面前站定,用左手背托着丰腴的瓜型腮帮子,右手将扇子轻轻地摇着,斜着身子,用一双挑逗的媚眼,盯着屈宝驹看了一阵,继续说:“五兄弟,你这么久都不回家来一趟,是不是把五大嫂忘记了?”
屈宝驹见盖玉秀这个姿势与这般神色,心头很不自在,赶忙说:“五大嫂,有什么你就说嘛!”
“说就说,你认为我不敢说是不是?你是咱家的一方土地神,在这嘉门区就要数你的官儿最大。你也是受过新思想教育的人,懂得什么叫民主、民权、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不纳小妾。你说说你大哥做得对不对?现在这个年代了,别的地方妇女早就放了脚,还剪了头发,穿了短装,和男人们一起上街,贴标语,喊口号,游行示威。他却把我当成金丝鸟,关在笼子里不让出去,剥夺了我的一切人身自由。那几个婆娘还有娘家可回,不高兴了就回娘家住上十天半月的,他也没什么?办法。唯独我倒霉,从小就是一个孤儿,一无娘家,二无亲戚,走没有走处,去没有去处,成天关在这牢孔孔里准备把我关死呀?你大哥当乡长,捞钱比你在行;要论谈感情,你比你大哥在行。你是个有人情味的男人,讨女人喜欢。今天五大嫂太闷了,你陪我到外面耍一耍吧!”
屈宝驹听了盖玉秀这番话,怔怔地望着她,一时竟不晓得如何回答她。
“喂!你是聋子还是哑巴哟,我说了半天的话,你连一个屁都不放一个?”盖玉秀睁大了杏眼,不满地吼道。
屈宝驹回过神来,连忙解释说:“你,我,唉!大哥也是为你好嘛,五个大嫂中数你最年轻,最漂亮,大哥也最喜欢你,你应该知足了。”
盖玉秀用鼻子哼了一声,极为不满地说:“哼,你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你大哥最喜欢我?凭哪一点?就凭他把我当一个花瓶,当一个欣赏品,当一个玩物?告诉你,我是有思想的人,我不喜欢过那种监狱般似的生活,我要到外面去见见阳光。人家杨森的姨太太都可以剪短发,穿短装,在街上自由自在地走,甚至跑到长江、沱江去洗冷水澡,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怪我当时眼睛瞎,嫁拐了男人。原本想摆脱那些戏霸的纠缠,能找到一个知心知已的男人过一辈子,这下可好了,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咱们女人的命好苦哟!哎,我说了半天,姓屈的,你究竟带不带我出去耍哟?”
屈宝驹哪敢答应,但又不敢拒绝,只好应付说:“好!好!等我忙过了这两天,我一定接你到嘉门镇去耍几天。”
盖玉秀高兴极了,说道:“两天后一定要来哈?不来的话,我可要骂你是个乌龟儿子王八蛋哟,天天骂,日日决,骂得你耳发烧,决得你脸发热。”
“一定!一定!”屈宝驹边答应边走,像躲瘟神一般迅速奔出了四牌坊。一抹脸上、身上,全是汗水,长长吁了一口气,叹道:“唉!又是一张连环嘴,惹不起!”
屈宝驹看了看时间,快临近晌午了,赶到吴家咀去吃午饭是最好的了。
可他到了吴家咀,却碰了一鼻子的灰。
要问什么原因?欲知详情,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