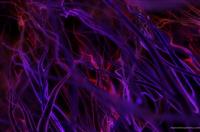我是善才徒,门内无师兄,四载终成事。须臾到我手中已有四个年头,古朴沧桑感已褪去大半。我也长得高出这琵琶四尺,前些年自己无感,外人有言,说我是美人胚子,定能有沉鱼落雁之色。果真如此,倒不是自夸,事实罢了。较他人学艺五载入门,我则四载就已大成,恩师姓穆,据了解曾是宫中乐师之长,了不得的一位善才,世上能与他匹敌的也仅是他的同门师兄,兼宫廷乐师教习之长,曹善才。还有隐居幻山避世不出的钱善才。恩师曾意气风发,锐意太盛,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众乐师嫉其巧技兮,谣诼谓其以不尊。被逐出宫,恩师各处漂泊,四海为家,后因无处可去辗转回京城,靠自己老友的资济下活了下来。那时对曹善才和钱善才没什么印象,只觉得他们虽能与师尊齐名,但绝无可能技艺比师尊还高超。
在我豆蔻前后,恩师带我去跑了首次演出,他叫我演奏时仅露半张脸,不要让别人看到我轻云蔽月之绝色,我应下了。及楼,漫天霓裳,飞粉胭脂,莺莺燕燕。我扭过头,登上主台,摘下面纱,仅露半面。似乎没有人察觉到我,客人们依旧是逗着歌妓,饮着佳酿。我转手一拨,声音似刀剑般锐利,扎破了喧闹的气氛,扎破了客人的心。随着演奏的推进,客人们的惊异之色越发浓郁,早没有当年之青涩,早没有先前之杂音,恩师技艺我已领悟大半,配上须臾之名器,比上恩师也是不逞多让。娉娉袅袅,卷上珠帘,有青涩青春,丽人羞涩之感,仿佛兮若流风之回雪倒可作为此曲之情调。随着轻轻一捻,柔弱结尾此时场中鸦雀无声,不论是客,还是妓,似乎都在回味,都做着梦呢。我也不矫情,装起琵琶,起身随师尊走出青楼,待走了几步后,方听到楼内的欢呼喝彩。
从此演奏变得频繁,人们越来越好奇我这个乐师,一日一曲,绝不多弹。“少爷,这就是京城名楼。”一位公子摇着折扇,迈着步子走进,恰好我刚开始演奏,弦音一挑,如电流般刺激了他的大脑,他顿时看向我,目光灼灼。舞弦灵动,天地为之动容,云彩为之飘摇。曲罢,我刚起身要走,却闻一声:“姑娘技艺惊人,在下没有听过瘾,可否赏脸再来一曲?”“一天仅一曲。”声音若天籁,我答到。“若允,则赏姑娘红绡百匹,绝不食言。”“说过了,不弹就是不弹。”我皱了皱眉,冰若寒霜。“叨扰了。”公子也不恼,摇着扇子,悠然而去。“少爷,这人好生不知好歹。”“不要忘了我们元家的家训。”公子怒斥一声。“是奴才错了。”
他又怎会知晓,我对待外人的冰冷恰衬托了对恩师的温暖。
“徒儿。”“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