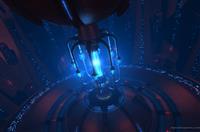罗朋在江堤走来走去,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
罗朋理了发,穿上洗过几水的西装。黑皮鞋擦了油,在阳光里一闪一闪。
罗朋走过来的时候,看见江堤下外滩公园里有一对一对的情侣,他们或者十指相扣,在鹅卵石小道上把手像跳绳一样一下一下高高的甩起来,或者在草地上并排躺着,望着天空越来越高的风筝,或者相对地紧紧拥在一起,像一座一动不动的雕塑。
罗朋又掉转头走回去。他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只是很随便地走走,又好像掉了什么东西,在那里寻寻觅觅。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他身体里发芽、生长,他感觉身体似乎在膨胀,那种疯长的东西随时欲破皮而出,把他整个儿弄得千孔百疮。他心神不定,焦灼不安亢奋异常。
罗朋找了一个不上工地的借口,就在春光灿烂的这天下午,在江堤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江堤的另一边,一排房子的某一间走出一个女人。女人上堤,径直走到罗朋跟前,女人笑吟吟地和罗朋说话了:“大哥,看你在河堤上走了半天,走,到下面喝口茶,休息休息。”
“不,不,不。”罗朋好像走着去办一件事情,径直朝前走。
女人就笑着牵着了他的手。
“不,不,不。”罗朋飞快地看了看左边,又看了看右边,却被那女人轻轻地牵进了房间里。
“不,不,不。”罗朋的心突突狂跳。
“大哥。”女人甜甜地叫他,好像两人上辈子就认得了似的。女人的眼光勾勾的。女人开始解自己的衣扣。
“我老婆不在家,打工去了。”罗朋低声咕噜着,好像有人在问他似的。
“你老婆也打工去了?”女人脱去外衣。
“我老婆打工去了,我老婆不在家。”罗朋好像说给女人听,又好像说给自己听。
“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呢?”
“不、不不。”罗朋坚决又急急地说。
“我们回家了,也和老公说在外面打工。”
罗朋脸上有汗,但他却把脱下的西装又穿上了。女人不解地看着他。罗朋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早已搓成条的五十元钞票塞进女人手里。女人不做声,小心翼翼地把钱展开,反正看了看,插进了罗朋西装口袋里。然后转一个身,背对了罗朋,把脱下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穿好。罗朋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他默默地、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间。那女人也不看他,把头向在一边。
罗朋出了门,贼一样看了看左边,又看了看右边,然后狂奔着上了河堤,再冲到江堤下的公园里。公园草地的缓坡斜进水里。罗朋没有停,径直冲入江水中。水齐了他的膝盖,他站住了。望了对面屋宇巍峨的城市一眼,突然,罗朋弯下腰,像传说中的鸵鸟把头埋进沙子一样把头埋进水里。
华灯初上,公园里情侣们在缠绵、在疯狂地接吻。樱花像雪片一样落下来,把他们包裹......
没有人注意江水里的男人。没有人会注意江水里一个叫罗朋的三十岁的、来自乡下的男人。
两岸城市赤橙黄绿的光映在江水里,光怪陆离。
城市市在狂欢。
城市在狂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