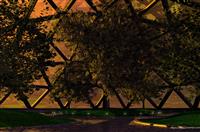不大的舞厅上空回荡着《难诉相思》的舞曲,我静静地独自坐在舞厅的一角。已经习惯了独自等待。很多时候都是我在独自等待着。舞厅老板给我送来茶具,我开始独自冲着从家里带来的铁观音茶。他又给我送来玫瑰干花,并说女人喝了玫瑰冲的茶,脸蛋会漂亮,慢慢地身体还会散发出玫瑰的香味。他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已结婚,有一个女儿。夫妻感情很不好。舞友曾经告诉我说他半夜三更被老婆赶出家门,衣服也被扔到街上。但他舞跳得很好,有时他会跟我夸口说他曾经到广州参加比赛。后来在我略懂跳舞的皮毛之后,我相信他的话,我看得出他跳得专业。他藉此不俗舞技经常陪四五十岁的女人跳舞。其中用意不言而喻。我也曾经跟他跳过,感觉很轻快、舒服。刚刚来到这里他时不时会教我跳舞。大约除了想从我这里收学费之外,还可以吸引我长久留在那里跳舞。毕竟我在那些消费低廉的舞厅也算年轻,并且长着一张讨好的脸。身材不错。经他塑造,作为他的活招牌,当是一个稳当的算盘。我因倾慕他的舞技,且离家不远,每天早上我都会不期而至。我一直生活在这个海滨小城,海风总会吹来咸咸的腥味。晚上倚着海滨长廊上的栏杆,眺望对岸起伏的山影,灯火阑珊,海面上偶尔捕捞的船只,总让人有说不出来的惆怅。远处两排弧形灯光下面是建好不久的大桥。老公大约就是乘车沿着这条新建的大桥往深圳的吧。
陈一直是这里的常客,在我来这里之前,我不知他究竟在舞厅厮混了多久。只知道大家都叫他陈,今年四十九岁,经常穿一件陀色的大衣。长着一张平庸的脸,不高的个子。每次来到舞厅,不算是出手大方,但他还会帮跟他一起跳舞的女人买单。我知道他目前没有舞伴,他的舞伴刚刚离他而去。听说他的老婆在别的舞厅跟别人跳舞,是那种固定舞伴的。(我在混了一段时间后,我知道这里的游戏规则是固定舞伴是可以上床,但也有例外少数没上床,算得上情操高尚)我在跟他交往的一年里我没有看到他去过那个舞厅。我也懒得去一探究竟。我想这样很好,来到这里,有人陪你跳舞,可以不用尴尬没人请跳舞,大家跳完走人,这是我所希望的,我讨厌被标上我是谁的舞伴的标签,这有辱我的人格,一贯我就自视清高。这里没有谁有资格可以当得上我的舞伴,就算不要上床的那种,我不想被人家在背后猜疑,毕竟上不上床别人也看不到。起码我还身家清白。虽然我的内心很空虚,很寂寞。在这里可以消磨掉我很多的时间,从白天到黑夜。这里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只有幽暗,舞台灯光幻灭闪烁。女人显得年轻,看不到皱纹。男人则跃跃欲试。眼睛既离不开暗涌的舞池,却时不时总在眺望着门口,希望从那里能够魔幻般走出个陌生的新鲜面孔,毕竟这里的女人熟悉得如同舞台的布景、灯光。乏善可陈。
婆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乡下来到这里,一来到,嘴巴便会骂骂咧咧,那种农村妇女的坏习气统统暴露,什么脏话她都可以骂得出来,长久以来我早已习以为常,也练就一身的钢筋铁骨,刀枪不入。紧闭嘴巴,任由她骂个天翻地覆,只当一阵恶风吹过。然而那次因为暂时未能出租的铺面有几颗老鼠屎没有清理干净的事情,竟然对我大动干戈,我忍无可忍,婆媳当着孩子的面扭打在一起,因此我与老公之间的关系迅速掉进冰窟。苦闷之下朋友带我走进舞厅。
在这里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等,心情随着舞曲的旋转而飞翔,一种另类的欢快占据内心,偶尔隐隐会飘过他的影子。他仍然是谁也无法比拟的,一张俊朗的面孔,高大的身材,这是令我着迷的地方。一直以来我不乏裙下之臣,父亲是当地富商,这都使我骨子里有着无限的高傲。
老板贪恋我的到来,有时也会教我一招半式,并且教我如何练基本功。很多时候我不屑于跟那些碌碌之辈跳舞。且绝大多数是想在这里浑水摸鱼,毫无技巧,更无舞德可言。我很多时候便会独自在镜前苦练。陈没有经常陪我。况且他的舞技已不能让我满意。我为了让老板可以继续教我,每次我都没叫他一起来。他也忙于奉陪他的朋友、税务局的一个朋友带他的一个三十多岁的情人,和那个情人的几个好姐妹到处游山玩水。陈有时也会带我来到一家地处偏僻的舞厅。说是舞厅,更多的像是专供情人幽会的地方,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里面有很多卡座,舞厅上空点缀着塑料花,偶尔一串绿叶、葡萄悬挂在空中晃荡,低沉悠扬的旋律盘旋,这里没有其他舞厅的哄哄闹闹,一对对低头私语,舞曲照例旋转,不时会有人起身跳舞。
我也一边忙于我的“外交”。在另一个舞厅我认识了一位舞友,高高瘦瘦的个子。善于调皮捣蛋,很会逗人。他的自我介绍是“女人的开心果。”跟他在一起总会欢欣雀跃。从此我游走在陈跟他之间。然而不久我便发觉他行踪不定,于是我开始盯梢他到另一个偏僻的舞厅,而我竟没有勇气直接到上面查看,空落落地在下面等了两个钟头,一无所获。后来我终于叫上一个朋友乔跟我一起上去,这一次被我逮个正着,但我找不到任何借口过去盘问他。眼睁睁看着他在那里谈笑风生,对我视而不见。我只能落荒而逃。好几天后,他低着头到大观园找我。我对他已不再心存幻想,却又有所不甘,怏怏不乐。有时还会心神不定,落寞地独坐在大观园的一角,偶尔也独自练舞,舞友都看出我对他的不舍。在跟他保持了一段若即若离的状态不久,我遇到了一个高大帅气且年轻的阳,这是我来的这里第一个让我心潮澎湃的人。但他有着高傲的性格。寒对我毫无防备,带我到他的小工厂参观,那时阳还要一个固定舞伴,听说因为生意的事跟老婆偶有争执。在舞厅好几次遇到他,我放下清高的架子对他频频示意,他视若无睹。就在我即将放弃的一个晚上,他终于来到我经常聚脚的大观园找我。这是第二天早上大观园老板告诉我的。我内心一阵窃喜,大有一种报复的爽快——终究让他也尝尝得不到的滋味。没过几天,我还是按捺不住到他经常流连的舞厅找他跳舞。他对之前冷淡于我解释是:“我以为你跟寒跳,所以我不能跟你跳。”我一阵愕然,继而郑重其事的说:“我可是至今为止没跟谁是舞伴哦!”他似信非疑的望着我。
接下来的遭遇让我明白什么叫人言可畏。
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找到我,劝说我离开她的舞伴。她自己在市中心开了一家童装店,听说生意不错,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她跟一个哈尔滨来的三十来岁的小白脸混在一起,最近我偶尔在舞厅碰到他,也跟他跳了几条舞,小白脸很会说话,每句话都恰到好处,听来十分受用,大约这便是他捕获她的手段吧,我觉得那女人可怜,有点像大婆被小三枪了老公的感觉。小白脸的舞技我根本看不上眼,只是小白脸粘人的手段了得,或者他跟她吵架,小白脸拿我来气她吧,虽然之后我不再跟他跳舞,然而在舞厅隐约流传着我抢了别人的舞伴。我感到很无奈。然而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很少人会去相信你的清白的。
我一直奔波于寻找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舞伴,但是我终不能,我感到疲惫不堪。我失去了很多信心。然而没有一个合适的舞伴我将更加疲惫,很多时候我只能静静坐在百乐的角落,老板有空会过来请我跳一条,这里的很多常客都知道他们请不动我,他们对我望而却步。白天我在大观园跟陈继续凑合着跳,我仍然希望能够找到合拍的舞伴,但我知道很难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