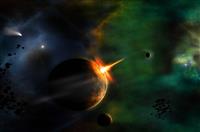美国舆论研究的知名学者劳伦斯·雅各布斯(Lawrence R. Jacobs)指出:“在民主国家,政策制定者被视为响应民意的执行者,公共舆论是塑造决策议程和确定政府决策的自然动力。舆论作为影响政治生活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变量之一,始终是参与式民主理论与公共决策理论的重要范畴。”这一看法充分揭示了舆论对国家决策不容小觑的影响力,而舆论尤其是印度舆论在中印关系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力证明了雅各布斯的论断。
本文以印度国内舆论主体——英语主流媒体与智库为研究对象,重点对洞朗对峙、武汉-金奈会晤和 2020年中印边界西段对峙这些重大事件发生后,印度主流英文媒体和智库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报道和评论进行阐述,分析其主要观点的形成原因及其对中印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而探讨中国的应对之策。
“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是印度国内舆论的关注重点。当中印关系发展顺利时,印度舆论在涉华边界问题上多聚焦于常规的边界磋商和谈判、两国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当中印在边境地区发生对峙、两国关系因此陷入紧张时,印度国内舆论往往会渲染“中国威胁”,夸大甚至刻意扭曲中方在边境地区的正常建设,鼓励或煽动印度民众的反华情绪,为印度政府在边境地区和两国关系的其他领域采取进攻性行动制造借口。大体而言,印度主流英文媒体和智库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道内容主要集中在领土争端、边界谈判、边防会晤、边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一)洞朗对峙发生后印度国内的代表性言论
2017年6-8月间,中印边防部队在两国边界锡金段爆发了长达70余天的“洞朗对峙。”对峙期间,印度国内涌现出了许多诸如“对华开战”“与中国决一死战”等过激言论。时任印度国防部长阿伦·贾特利(Arun Jaitley)在《印度时报》上公开宣称:“有些人意图挑战我们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我坚信,我们勇敢的士兵有能力保卫国家安全,无论挑战来自东部边界还是西部边界。印度军队已经足够强大,有能力应对任何对国家安全的挑战。印度军队已经从1962年的战争中吸取了教训。”
印度陆军参谋长比平·拉瓦特(Bipin Rawat) 也渲染发生第二次印中战争的可能性,并表示“印度军队已经做好了进行两线半战争的准备”。军方人士的“战争宣言”不同,印度的专家学者群体多强调“中方行为的不合理性”,以此为本国进行“辩护”。
印度前驻华大使阿肖克·康特(Ashok Kantha) 在对峙期间就诬指中国“改变现状”,“威胁”印度安全,声称“中国意图扩大在洞朗地区的军事存在,尤其是洞朗地区的道路建设明显改变了中印不三国在此地的军事现状,这将对印度的战略安全产生威胁”。
洞朗对峙结束后,时任印度全球问题研究所主席阿肖克·萨杰哈尔(Ashok Sajjanhar) 发表文章称:“此次在洞朗地区逼退了中国军队,是印度取得的重大外交胜利。印度边防部队接下来要加快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军备升级。”印度国内战略家和各大媒体的消极言论加深了洞朗对峙以来印度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两国间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的基础。
印度国内主流英文媒体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追踪报道此次对峙产生的影响,印度的专家学者更是多番发文讨论后续如何在中印边境地区再次发生冲突时占据主动性。对峙结束半年后,印度国内舆论稍有所缓和,但边境地区的紧张局面仍在持续。真正给对峙后印度国内舆论和中印关系带来专机的事件,是2018年在武汉举行的两国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晤。
(二)武汉-金奈会晤后舆论风向的转变
2018年4月27-28日,武汉非正式会晤举行。这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印领导人举行的第一次非正式会晤。翌年, 两国领导人又于10月11—12日在印度金奈举行了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在首脑会晤的引领下, 印度国内对于中印关系、中印边境地区的有效管控出现了一些乐观的声音和看法。
武汉会晤结束后的第二天, 《印度教徒报》 就大篇幅报道了“武汉会晤”对中印两国边境管理的引领性作用。报道称,“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竞争, 中印两国仍能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武汉非正式首脑会晤不仅为中印共创亚洲世纪创造了条件,也为此后两国减少双边摩擦和矛盾提供预防机制”。
曾任印度驻美国和中国大使的尼鲁帕玛·拉奥(Nirupama Rao) 于 2018年5月3日发表的《当印度与中国相遇》一文中谈到, “ 尽管中印两国仍然存在地缘政治竞争、边界战争的历史包袱、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反对等一系列问题,但近年来随着中印两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不断上升,‘中印共创亚洲世纪’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呼声。中印两国领导人可定期举行非正式会晤,以不同形式继续保持战略沟通,共同创造属于亚洲的时代”。
印度分析人士阿图尔·阿内加(Atul Aneja) 在武汉非正式会晤后,提出了“印中两国携手复兴东方文明,共创亚洲世纪”的观点。他指出,“中印关系的回暖不仅有利于两国自身的发展,也是全球化时代下重振东方文明的关键之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武汉会晤是亚洲文明将重新引领世界的重要体现”。
2019年的金奈会晤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印度媒体称此次会晤再次“为不确定的中印关系带来了稳定积极的因素”。《印度斯坦报》大幅报道了此次会晤取得的多项成果,称“两国领导人在会上讨论了贸易、国防、人文交流以及恐怖主义等领域的问题,达成了10项收获”。
曾任印度驻缅甸大使的高·帕塔萨拉蒂(G Parthasarathy)也赞同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为缓和两国间矛盾起到积极作用,他表示:“此次会晤期间,中国领导人将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中印双边合作,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两国领导人在武汉和金奈举行的非正式会晤有力地促进了印度国内涉华舆论的转变,此前的对华负面声浪有所减弱和扭转,舆论转而更多地关注双边合作中的积极因素, 这反过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回暖和正常化。
(三)加勒万河谷对峙刺激印度反华舆论
2020年4月以来,印度边防部队单方面在中印边境西段地区抵边修建基础设施,5月6日凌晨更是越线进入中国领土构工设障,阻拦中方边防部队正常巡逻,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措施,加强现场应对。随着新一轮边境对峙而来的是印度国内各界对中国的攻讦和诬蔑。
早在5月22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努拉格·斯里瓦斯塔瓦 (Anurag Srivastava) 就表示:“任何关于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进行活动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是中方最近采取的行动妨碍了印度正常的巡逻模式。”相对于政府的表态,印度军方的发言和实际行动则更为强硬。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陆军总司令纳拉瓦内( Naravane)几乎每天都向国防部长通报拉达克东部局势的变化,并建议对中国在中印实控线沿线的‘违法行为’作出强硬反击。”
自对峙开始以来,中印两国边防部队陆续进行旅长级、军长级等多层级谈判,但6月15日发生的加勒万河谷流血事件却使两国关系陷入剑拔弩张的状态。尽管随后公布的细节已经表明,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直接起因于印度陆军上校桑托什·巴布(Santosh Babu) 冒进和鲁莽的“亲略”行为,但印度国内舆论却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大肆攻讦中国,为自身的错误行径辩护。《印度斯坦时报》、《德干纪事报》 和《印度教徒报》等多家主流媒体,都相继发表了宣扬“中国率先‘亲略’印度”的相关报道。
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军队还在8月底、9月初发起了占领班公湖南岸部分高地的行动,甚至违背中印相关协定在一线对峙中多次鸣枪,而这些“亲站”和非法行径却被印度国内舆论美化为边防官兵保卫己方“领土”的“英勇”行动而大肆宣传报道。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项目研究员哈什·潘特 (Harsh V. Pant) 在随后发表的《中印边境实控线的“新常态”》的评论文章中大肆赞扬了8月底印军抢占高地的行动。文章称“在此次冲突中,印度军队成功占据了有利地位,挫败了中国军队的计划。......印度国防机构需要在中印边境部署大量兵力,做好准备迎接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
2021年2月10日,中印两国国防部先后宣布两军位于班公湖南、北岸一线部队开始同步有计划组织脱离接触。但从脱离接触开始至今,印度国内舆论总体上反应消极,一方面相关的报道和智库评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无视中国的和平诚意, 视脱离接触的实现为印度实力使然, 且对缓和局势缺乏积极性。 如印度陆军退役中将赛义德(Syed Ata Hasnain) 公然表示: “ 就北部边界而言, 所有的脱离接触及局势缓和都只是暂时性现象, 在保持积极立场的同时, 印度必须拥有比其对手更强大的军事实力。”
舆论一旦形成就具有无比的潜力,它代表公众的意愿和利益,会对决策者产生现实的压力, 进而影响未来的决策方向。鉴于“边界问题”在印度国内的敏感性与热度,莫迪政府上台以后,印度的智库和主流英文媒体关于此类议题的报道与评论层出不穷,并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其一,在印度的书写语境中,倾向于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在边界问题上“虎视眈眈”的具有“亲略”性的邻国。莫迪上台以来,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多次发生对峙。边境一线的紧张和中印两国整体实力有较大差距的现实与上世纪60年代印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的惨败记忆相结合,使印度国内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正常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充满了警惕和怀疑。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甚至诬蔑中国进行“亲略”,已经成为印度长久以来的习惯性舆论。加勒万河谷对峙以来,面对几十年来少有的边境严峻形势和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和姿态,印度舆论更是反应激烈,刻意诋毁和抹黑中国,塑造中国的“亲略”和“威胁”形象。前国家安全问题组成员马诺伊·乔西 (Manoj Joshi) 也在边境对峙期间强调“中印边界西段的局势让印军相信,印度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北部邻国,而不是西部邻国”。“中国威胁论”不仅延伸为“边境入侵威胁论”“中巴两线威胁论”等,还逐渐成为了印度版的政治正确。凡论及印度的周边安全隐患, 其舆论往往“ 言必称中国”。
其二,印度舆论重视追踪报道、 评论印度本国边境的基础建设和军事部署, 强调以此对抗中国的重要性。莫迪刚接任印度总理之际, 国内安全分析人士尼廷·戈卡莱(Nitin A. Gokhale) 就直言道: “尽管在2013年印中两国签订了首份边防合作协定, 以期建立双方在边境军事领域的政治互信。但实际上,印度从未放松对于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建设。印度军方抽调了更多兵力部署在锡金、‘伪阿邦’ (我国藏南地区) 和拉达克等地区。”即便是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 中印关系回暖、升温之时,印度国内舆论也从未放松对本国边境地区尤其是中印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关注。2019年4月,即武汉会晤结束一周年之际, 《印度时报》大篇幅报道了印度军方主办的由比平·拉瓦特将军主持、为期一周的军事指挥官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就是强调印度政府目前迫切需要加强从拉达克东部到“伪阿邦” (我国藏南地区)与中国边境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勒万河谷对峙以来,印度舆论在大肆攻讦中国的同时, 也不乏强调加强中印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对抗中国创造更有力有利条件的报道和评论。《印度斯坦时报》就曾对印度军队在边境增兵进行大篇幅报道: “陆军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印度军队已经向印中边境西段派遣三个师与几个中队的坦克部队、火炮与机械化步兵,加强军队部署以应对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军事存在的强化。”
其三,印度国内舆论带有明显自我美化的色彩———突出表现为对峙期间鼓吹对华强硬, 对峙结束后宣扬 “ 印方胜利”。印度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阿肖克·赛詹(Ashok Sajjanhar)在洞朗对峙后第三天就在国内大张旗鼓地宣称印度在此次对峙中取得了 “ 胜利”, 他认为 “ 洞朗对峙是印度在政治、 外交和道义上的巨大胜利。印度政府在极端挑衅面前坚定不移, 这一事件将极大地提升印度作为全球舞台上负责任、 果断和可靠大国的形象”。2021年2月,印度陆军北部战区司令乔希(Joshi)在接受印度New18电视台专访,就中印边境对峙以来的情况进行全景梳理时,除表示当前脱离接触过程进展顺利外,还不断鼓吹“印度的成功”,宣称“中国丢脸”。此类论调的盛行不仅暴露了印度精英群体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印度失败的事实,也折射出印度大部分民众对中印边界争端形成演变的无知。
作为中印关系中最敏感的部分, 边界问题被称为悬在两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一旦发生边境对峙,印度国内舆论就习惯性地放大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因素,并由此强化了这柄利剑的危害性。印度国内围绕中印边界争端的前述舆论及其特点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的影响,又受当下印度决策层外交战略的规范, 还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盛行和印度媒体自身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第一,印度对中印边境战争的记忆为其国内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上特定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底色。罗伯特·杰维斯指出: “一般来说,对人们影响最大的不是从前的战争,而是最近一次重大战争。因为重大战争在一代人身上也就发生一次,大部分人亲身经历的也是最近的一次重大战争。”这一判断显然适用于印度。印度国内主流英文媒体和智库学者之所以对中印边界问题如此敏感和态度消极,很大程度上与上世纪60年代中印边境战争的历史记忆有关。
印度在美苏冷战已经拉开帷幕的背景下实现了独立,并因积极倡导“不结盟运动”而拥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受到美苏两国的争相拉拢。同一时期的中国则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包围中。中印建交后,双边友好关系迅速发展,印度不但大力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积极支持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印度因此自认为对中国颇多“恩惠”,中国应该“知恩图报”,在边界问题上对印度“投桃报李”。
然而,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仅打破了两国的“蜜月”, 也摧毁了印度在边界和领土争端问题上一厢情愿的对华幻想,战争的结果尤其加剧了印度对中国的怨愤之情。战争结束后,中印关系跌至冰点,印度开始将中国视为其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在媒体上大肆炮制和渲染中国对印度的“‘亲略’行为”。讽刺的是,这种虚假的宣传报道客观上成为印度政府凝聚民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佳素材,时至今日,仍屡试不爽。印度的政治精英和主流媒体在特定时期对这场战争的“印度式”反思宣传,使这种被刻意歪曲的战争记忆得以不断加深,并最终演变为“中国背叛并‘亲略’了印度”的荒谬文本而得以传承。印度始终认为中国“背叛”了印度,中国对印度的“‘亲略’战争”是其挥之不去的历史耻辱。尽管中印边境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但印度民众对边界争端的历史和边境战争的错误认知一直影响着其国内的对华舆论,制约着印度民众客观理性地看待当前的中印边界争端。
第二,大变局下印度政府的战略转向为印度国内有关中印边界问题舆论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上的对印优势越来越大,直至现在中国的GDP是印度的5倍之多,这造成了印度国内政客和中上层群体巨大的心理落差。印度战略层甚至认为“中国已经超越巴基斯坦,成为本国的头号威胁”。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让印度看到了遏制中国、扩大印度战略空间和战略利益的另一种途径,即交好美国,借美国之势来压制中国,对冲中国在中印双边关系和地区事务中不断扩大的优势和影响力。印度向美西方国家的不断靠拢从两个方面助长了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反华舆论的形成。一方面,印度国内对华舆论的强硬顽固能够凸显印度这个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中美竞争中的战略价值,从而有效抬升印美关系;另一方面,在边界问题上渲染“中国威胁”既能为美西方国家抹黑、诋毁和打压中国提供素材和借口,又有助于争取美西方国家对印度的同情和支持。加勒万河谷对峙以来,美国部分官员就曾公开表态支持印度。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犹他州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在中印边界明显的‘亲略’行为表明,其正在试图通过武力夺取实控线的控制权”。2020年10月27日,印美两国召开“2+2”外长防长会议,签署了有关地理空间合作的《基本交流合作协议》,这份军事合作文件可以说是美国与其防务伙伴的“ 标准配置”,文件的签署事实上表明印美“准盟友”关系的建立,这反过来壮大了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奉行错误认知和实践的底气。
第三,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的盛行为印度国内有关中印边界问题舆论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宗教民族主义,是指民族宗教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 使本民族神圣化, 使宗教为本民族或本国家的一切利益服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社会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印度人民党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国内政治中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人民党采取了一种比以往历届政府都更强硬、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步成为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强势外交理念与莫迪时期的“大国梦”正相契合,印度外交的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头不断上升。
2015年2月,莫迪声称要带领印度发展成为 “全球领导大国”(a leading power),而不只是一支制衡力量 (a balancing power)。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印度与莫迪: 仍旧处于蜜月之中》指出, “ 就党派而言,具有印人党背景的人士比具有国大党背景的人士更多地认为中国是威胁”。2019年,莫迪政府取得压倒性胜利,再次获得连任。斩获印度人民院的绝大多数席位后,新一届莫迪政府在外交战略上变得更加雄心勃勃, 在对华交往中也更多奉行强硬政策。 在数次中印边境对峙中,印度不仅坚称“印度军队没有越境行为”,其军队高层还多次在国内采访中指责中国的正常边界巡逻行为,宣称印军行为的“合理性”与 “正义性”。洞朗对峙中印军的非法越境行为在事后更是被视为印军的“果断”和“坚决”而大加赞赏和鼓励。正所谓“上行下效”,印度政府和军方的一系列举动刺激和催生了印度国内在边界问题上对华负面舆论的盛行。
第四,印度媒体刻意歪曲和掩盖中印边界问题真相为印度国内相关舆论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土壤。“中印边界问题”之所以能成为席卷印度上下的热门议题,与印度国内媒体的刻意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在全球范围传统大众媒体萎缩的态势下,印度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读者群体。印度全国有超过10万种报刊和出版物, 其中150种主要报纸每天发行量超过1亿份。据印度媒体使用者委员会(MRUC)的调研,印度报纸的读者群体已超过4.25亿人。
印度的报纸主要分为英文媒体和印度语言媒体,英文媒体的数量和受众量虽然有限,但熟识英文的多为印度中上阶层,他们对印度的外交决策具有重要的舆论影响力。度媒体多为私营企业,在市场化和商业化环境下,读者、订阅量和广告数量的多寡决定着一份报纸的“生死存亡”。博得大众眼、满足国内民族主义的需要,往往是一份报纸获得高销量和理想排名的重要法宝,,而中印边界问题就是博眼球的天然话题,在该问题上迎合印度的“政治正确”自然是占据较高市场份额的“秘诀”。大众传媒娱乐化的现在,加之民族主义情感的盛行,印度媒体涉华报道的标题越是耸人听闻,内容越是对中方强硬,越能赢得读者关注并获得各类企业投放广告的青睐。换言之,印度主流媒体在争夺观众和利润追求的双重压力下,在涉华边界问题报道中常常会主动背离客观与公正,炮制错误信息,误导舆论。
除了以上四种因素外,公民交往与文化合作因素也对印度国内涉华边界舆论的形成造成了影响。中印文化交流不理想,民间往来不充分,阻碍了两国广大民众和知识精英培育彼此间的文化亲和与友谊互信, 这自然也会影响到印度媒体、学者的心态立场及具体的报道手法和行文方式。
政治学家维·欧·基(V. O. Key) 曾提出著名的“堤坝论”。他认为:“公众舆论好比一座堤坝,它预示了公众行为的方向,而政府层次的辩论和行动都必须在这个堤坝下谨慎地进行”。印度主流英文媒体和智库每年的涉华报道、评论多不胜数,为广大读者群体们感知他们心中的“中国形象”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对华舆论充满了对中国的防备、警惕甚至敌意,这也使得双边关系和两国在全球层面的合作屡生波折。
首先,印度涉华边界问题舆论压缩了政府的决策空间。随着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速度和渠道不断加快、拓宽,媒体报道和随之诱发的公众舆论对一国外交决策和两国双边关系的影响愈发凸出。当“ 边界问题”这样的高敏感问题出现时,国内专家学者多对此畅抒己意,发表相关评论文章。媒体报社也会争先报道, 唯恐落于人后。两相联动之下, 极易引发覆盖社会上下的公众舆论。
莫迪上台以来,印度涉华边界问题的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政府的决策空间,也不可避免的给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投下了阴霾。一方面,印度国内热衷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发声的群体多为印度的精英阶层,许多还和政府部门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们所发表的对华评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智囊团的声音。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印度版的“ 旋转门”机制,使得主流媒体和智库的舆论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印度的精英阶层是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一般是指政府 ( 退休) 官员、智库研究人员、大学学者、军方和情报界人士、商业精英、著名记者等。在印度国内对华边界问题的评论中,最活跃和吸引眼球的报道和言论就是出自他们之手,前政府官员、智库人员和学者们热衷于在报纸以及网络上开设专栏,对印度内政外交进行评论,涉及议题面广,传播力强,民意引导效果明显。2020年中印边界西段发生对峙 以 来,以 拉 贾·莫 汉(Raja Mohan)、 科瑞帕拉尼(Manjeet Kripalani)、哈什·潘特等为代表的学者集体和以前外秘萨仁山(Shyam Saran)、 高·帕塔萨拉蒂、前内阁副秘书贾亚德瓦·拉纳德(Jayadeva Ranade) 等为代表的退休官员,都在报纸、电视和网络媒体上发表过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和主张既引导着大众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规范着政府的决策。
另一方面,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消极舆论冲击了莫迪上台以来两国领导人高层引领的效果。莫迪上台以来,中印两国关系在高层频频会晤的引领下呈现出积极向好的态势。但不断发生的边界对峙及其前后印度国内的消极舆论使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引领效果大打折扣。高·帕塔萨拉蒂曾在金奈会晤后公开表示,“中印领导人的会晤并不能完全解决给两国关系带来消极影响的问题”。加勒万河谷对峙以来,印度舆论再次质疑两国间高层对话的作用。马诺伊·乔西在2020年6月曾发文称, “过去一个多月的对峙表明,中印高层为维持实控线沿线和平而建立的信任措施已经失效”。印度民众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关注和负面情绪加大了传播学角度中的“观众成本”,而媒体为了博流量的大肆炒作,进一步影响了印度政府决策层理智、客观地看待边界问题和印中关系, 并作出正确的应对。
其次,制约中印双边关系的深层次发展。近年来印度主流英文媒体和专家学界在边界问题上的对华报道和评论呈现出了鲜明的负面色彩,颇有“言必称中国威胁”之势,这不仅会使中印关系中的消极因素进一步扩散,也会给印度政府在涉华问题上的决策造成负面影响。
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中印关系逐渐回暖过程中,双方达成了“边界问题不构成两国发展关系障碍”的共识。2014 年,中国领导人首访印度时, 也与莫迪总理商定“不使边界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发展”。但在实践中, 印度国内不仅炒作中印边界争端, 刻意歪曲中方在边境地区正常的基建活动,煽动印度强化在中印边境地区的管控力量,在边境对峙发生时,印度政府还任由其国内负面舆论向低敏感的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蔓延。
加勒万河谷对峙以来,无论是印度官方封禁中国企业研发的APP,教育部门叫停与中国高校间的合作协议,还是民间还发起的“抵制中国商品”的行动等,背后都有媒体记者和智库专家的鼓吹、煽动与应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副主席Gautam Chikermane 直言,封禁中国APP “是一项有效预防‘数字入侵’的方式,印度政府的此项政策与目前的中印边境西段局势息息相关”。印度梵门阁智库董事会成员布莱斯·费尔南德斯(Blaise Fernandes) 则将中国的 5G 技术形容为“糖衣炮弹”,认为“中国将尽一切可能促成与印度的5G 谈判,到那时中国便可以挑起直接或间接的边界冲突、用无人机袭击印度西海岸的石油设施和发动网络攻击等”。印度国内涉华边界负面舆论的持续传播, 不仅增大了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难度,还使得边界问题再次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主导性议题。就中国而言,印度在涉华边界问题上的消极舆论不仅引起普通民众群情激愤的反弹,也影响了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的对印认知,客观上阻滞了中印间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入合作。
再次,中印在国际层面的合作波折丛生。中印同为亚洲发展中大国,彼此在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国际组织机构改革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或相近的主张。但印度国内盛行的“中国威胁论”和两国边界对峙频仍的情况,不断瓦解着中印两国本就极其脆弱的政治互信,也促使印度更加坚信“中国是遏制印度成为大国的强劲对手”这一错误理念。由边界问题加剧的对华警惕、防范心理使印度难以正确看待在一些国际合作议题上的中国参与,从而削弱了中印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国际合作。
其中,反恐与区域经济合作是极具代表性的两个事例。一是在反恐问题上认为中国偏袒巴基斯坦而影响中印两国反恐合作。如2019年3月,当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否决了印度提出“将马苏德·阿兹哈尔列入联合国恐怖分子名单”后,印方在国际场合大肆传播“中方否决此提案是为了维护中巴之间的友谊和在印度周边制造动荡不安的恶劣环境”,不仅否定了中国开展反恐合作的决心和诚意,也有损于两国友好合作的氛围。
二是在区域经济合作议题上以中国在侵犯印度权益为由进行消极抵制,拒绝签署合作协议。印度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和国家利益的考量先后拒绝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却多次将拒入原因归咎于中国。印度数度拒绝“一带一路”倡议,理由就是“巴经济走廊”侵犯其宣称的“领土与主权完整”。2019年11月,印度几经犹豫,最终决定拒绝加入RCEP。为了应对来自日本和东盟国家的质疑,印度国内舆论将责任推卸到中国头上。《印度时报》称,“中国长期对印度拥有着大额的贸易顺差。如果没有关税的保护,印度工业无法与大多数RCEP伙伴的工业产品竞争,尤其是中国。……此时签署RCEP协议将会永远使印度成为中国的战略分支,这是印度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除此之外,印度还以防范中国为由,逐渐背离其“不结盟”政策。加勒万河谷对峙为印度政府进一步向美国和西方国家靠拢并联手制华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和藉口。印度国防分析与研究所研究员卡利亚拉曼(S. Kalyanaraman) 称,“中国在印度周边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与实力威胁着印度的安全与利益。印度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及其亚洲盟国进行安全合作,以此更好地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自4月份以来,中国悍然且无端地“亲站”了印度的领土, 这可能会加速印度与美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并推动印度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脱钩。” 2021年5月,印度战略家拉贾·莫汉在外长苏杰生首访拜登政府之际,提出了“印度在多边问题上对西方的习惯性反对已经成为历史。在拜登的总统任期内,(我们)要让多边主义成为印美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舆论尤其是一些颇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大肆鼓噪联美制华,不仅在实践上冲击了中印两国开展国际合作的友好氛围和积极性,也加剧了两国普通民众之间的猜疑。
四、结语
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人口大国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新兴国家,也是拥有千年友好交往史和短暂边境冲突、且同步崛起的邻国,中印双边关系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都具有重要影响。但与之不对称的是两国之间相互的认知,尤其是印度涉华边界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失衡和偏差。这使得莫迪上台以来,两国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互信不仅难以有实质性提升,还因加勒万河谷对峙的发生而遭到重创。当前,两国仍处于中印边界西段对峙“脱离接触”的进程之中,在此时间点上,推动印度国内舆论摆正心态,正视边界问题,提倡中印友好和支持两国在全球层面的合作则显得尤为重要。
舆论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推动外交目标的实现,也有可能压缩外交的空间,使危机处置从外交手段滑向冲突甚至战争。边界和领土问题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最容易引发广大人民的关注,激发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
对此,一方面,中印要加强媒体与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莫迪上台以来,中印两国已举办三届“中印媒体高峰论坛”,每届论坛都有来自两国数十家媒体负责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高级别政府官员参加。未来在两国主要媒体和智库的推动下,中印两国可以开辟多轨道对话平台,以促进两国间的全面交流。
另一方面,在边界问题上我们对印度舆论的回应要特别注意“因时因事”,特别要避免无益于良性沟通的煽动性措辞。中国国内主流媒体要把握对印度报道的主流和方向,在经济、文化、社会等低敏感性议题上,更强调中印之间的合作面,积极推动“合作”与“共赢”成为两国之间的基本盘。在政治、安全、军事等敏感问题上阐明中方态度与立场的同时,要在报道中坚持“有理、有利、有据、有节”,避免陷入”论战“的陷阱,为真正维护好中印关系的发展大局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