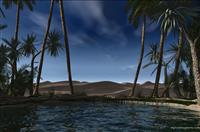从网上看到最近有不少关于智库的论坛和研究,很高兴看到我国的智库发展正在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机会。
什么样的智库产品符合决策需要?
什么样的智库产品符合决策需要?这是中国学者经常困惑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做周边工作,当时世界刚刚走出冷战。从外交决策的角度,面临许多新课题,例如:周边外交怎么走?如何从理论上讲清楚?这样一些问题。那时开始看一些中国学者的文章和书,例如从阎学通老师的研究中就得到许多理论上的启发和支持。我印象最深的是阎老师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外溢,延伸到了边境之外”的论述。围绕“周边外交要为改革开放构建好的周边环境”的思路,我们形成了在周边增信释疑、参与多边对话、推进“合作的安全”等一系列政策和外交宣示,最终建立起中国东盟自贸区。亚洲地区比较顺利地渡过了后冷战时期的思想混乱,较快地进入一个良性的合作轨道。这期间我们与国内学者一直保持密切的沟通,他们对国家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的外交政策和思想延伸有很重要的贡献。
再举两个例子,记得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等亚太区域合作时,无法回避预防性外交的概念,对此怎么看、怎么做,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地区多边机制中的作用。国研所、社科院、北京大学,特别是王逸舟、刘学成等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而且有系统的著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现在预防性外交这个词已经在经常使用。
智库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和相关表述最典型的例子,是郑必坚和他领导的改革开放论坛,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在他的研究基础上阐释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后来还发表了政府白皮书,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的体会是,在外交方面,好的智库产品应该紧跟当时国家发展需要,能服务于相应的对外政策的需要。应该是现实的和具体的,说白了就是能“解渴”。怎么看当今世界的特点?
任何时期的外交决策都需要一个比较客观的三维世界政治地图。在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变化中,如何找到一个描绘国际形势的切入点?
看今天的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一个“变”字,似乎一切都在动态中。能不能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而且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多重转型。
首先是国际格局的转换,对这一点国际上基本是有共识的,包括美国的一些重量级学者都承认,国际权力不再集中于传统的西方大国。但是在向什么方向转换的问题上,看法不同。前一段时间国际上讲得比较多的是国际权力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引起西方世界的紧张和对中国的警觉。最近又出现美国实力恢复并且将延续霸权的论断。
从辨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当今世界国际权力的转换反映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形态。冷战后出现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再受到任何政治制约,技术、资本、人才乃至市场等等,都开始在全球范围更自由、更快地流动,从传统的西方中心向外扩散。固然有的国家和地区吸纳的多一些,例如中国和亚洲,但是只要没有发生动荡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得益于这个扩散,取得很大发展,许多数据都说明了这个效果。
中国如何更多更好提供国际信息的问题,需要增强自身形象塑造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智库确实可以多做多说在此基础上,国际权力也在向更广泛的领域和方向扩散,推动新兴大国力量的上升,一些非传统力量也在上升。这与历史上大国更替过程中出现的权力转换完全不同,现在是权力的扩散和分散,国际事务的处理需要更多国家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讲世界进入转型阶段,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来。例如,生活方式在转型,新技术,尤其是网络,带来人的交往方式以及资讯传播方式的改变。再比如,在绿色理念和新技术的推动下,生产和制造方式和消费方式也在转型,等等。
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但是同时,世界仍然处于和平发展的时代,这个判断不应该动摇。在20世纪,前50年是以战争为主线,后50年没有再发生大国之间的热战,冷战使得各个区域隔绝,但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虽然很不均衡。这为20世纪后期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时代奠定了基础。和平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大方向必须坚持。
所以,可以说当今世界时代主题没有变,只是在这个主题下,世界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和转型,而中国,则处在变化的中心。21世纪中国智库的责任那么,应该怎么看待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
中国在智库建设上是后来者,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就有重谋士、利智囊的传统,但是古代的幕僚只是单向服务,没有社会公共属性。在现代智库发展上,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与传统的西方国家差距是比较大的,像英国的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oHouse)是1920年成立的,有90多年的历史了,美国布鲁金斯的前身——政府研究所是1916年成立的。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在全球智库分布中,中国排第二名,有429个智库,而美国拥有1823个智库,是中国的4倍。在前50个顶级智库中,中国只有3家。在报告中提到的最具创新性政策建议、最佳利用互联网和社会媒体、最佳利用多媒体技术、最佳对外关系与公众参与等项目的全球排名中,没有中国智库。
当然,这份报告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情况,中国智库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思潮的引领上已经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国际评估难免受到语言和渠道的限制。但是在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上,我们确实有提高的空间。
应该说,现在是中国智库成长的难得机会。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政策需求大,需要研究的课题丰富。同时我们是在一个成熟的国际环境中成长,可以学习和汲取的知识和经验非常丰富。
关于如何加强智库与决策的关系,我想到这么几点:
一是,智库要与决策机构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课题需要贴近外交现实和需求。
宾州大学的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JamesMcGann)博士(他牵头做了《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来北京时,我向他请教智库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做出的东西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策所用,这个智库思想产品就不是成功的。
中国智库建设还在成熟的过程中,如何能更好地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撑和培养优秀人才,这都是需要不断摸索和提高的。有人问,智库如何才能知道有什么决策需求?确实,这是一种供求关系,牵动供应的是需求,决策部门可以提供需求提示和相关的信息资料。例如外交部就与许多智库保持着比较密切的沟通关系。党的18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发挥思想库的作用,中国智库的发展对于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
智库需要有政策服务意识。智库的独立思考要具有建设性,包括批评,目的是为了使决策更加准确,智库要看到问题才能提出改进的建议。但是目的性很重要,因此智库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更多的冷静思考和平衡观点。这次的学术共同体论坛的题目非常丰富,也都是当前决策的关注焦点问题。
二是,智库要聚焦中国在国际问题上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初登世界舞台的国家来说,需要解决的理论和操作问题非常多。
例如,如何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时代方位?中国的自我认识是地区大国并且将发展成世界级大国,谈世界排位的时候中国更多考虑人均收入和面临的发展挑战。而国际上普遍以世界大国看待和期待中国。我们的智库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国内外都能接受的观点,至少要推动在国内形成社会共识,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大国战略和大国外交理论。
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加州会晤中,明确提出中国对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将重点落实两国领导人会晤共识。“新型大国关系”指的是中国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与美国这个传统的霸权国家之间如何确保以和平方式、对话方式为关系主导面,即便竞争也是非对抗性的。能否成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涉及到未来中国国际战略的方向。
这将是个长期和艰难的磨合过程,美国有霸权的惯性,调整会有难度,中国缺乏做有国际影响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学习需要时间。在这方面智库可以先行一步。
三是智库要坚持自己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增强向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和能力。
我最近出国访问和与来访的外国人士交谈,感觉到外界一方面对中国有信息饥渴,期待听到更多中国的声音,另外一方面关于中国的偏见和误导性资讯很多。这当然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因素,也有中国如何更多更好提供国际信息的问题,需要增强自身形象塑造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智库确实可以多做多说。
例如在中国国际责任问题上,外界有很多议论和期待。但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有自己的外交理念和原则,不赞成干涉内政。而传统的大国对此往往缺乏了解,也不认同,甚至认为中国不愿承担责任。中国智库可以多向外界介绍中国的行为模式和原则。增进国际了解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发挥国际责任,而促进国际了解的过程也有利于中国智库树立自己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形象。目前中国智库在世界上的声音还是比较稚嫩的,实力和人才都在成长的过程中。社会对智库要多几分宽容,对智库的思想产品要给予尊重和价值上的认可。
做智库是寂寞的,若无心静如水,恐怕很难深做学问。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何以中国自身历史文化和政治思想为基础,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独树一帜,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建立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需要相当的耐心、耐性和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