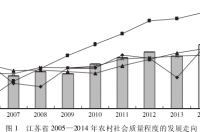仅仅在几年前,“欧洲的德国”或者“德国的欧洲”这类说法还只是存在于象牙塔内的理论探讨,学术界也多从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待德国与欧洲的关系。但是,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德国地位的上升成为不争的事实,德国与欧洲的关系再次受到瞩目。回顾欧债危机演变的过程可以发现,德国在危机救助政策实施的内容、步骤和时机等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德国的这种主导作用以什么样的渠道来具体影响欧盟的发展?这种主导作用是会长期存在,抑或只是欧债危机背景下短暂的幻象?如长期存在,其根基和影响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本文主要讨论的内容。
一、主导欧盟制定应对债务危机的战略
2013年7月20日,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发表的署名文章《我们不要德国的欧洲》同时在德国、英国、法国、波兰、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主流日报上刊发,否认德国在欧洲谋求领导地位。此文的发表显然是想打消其他欧盟成员国对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担心和忧虑,但另一方面,这一高调的政策宣示凸显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欧洲政治经济格局已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重组,德国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主导作用,并在此次债务危机中更加显性化。
不同于历史上传统霸权国采取的单向强制行动,德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隐藏在欧洲的集体行动中,以“欧洲”的名义和渠道投放自身影响力。这种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主导”主要通过“理念引领”来实现。
德国的理念引领作用突出体现在对欧债危机根源的解释上。国际社会对此次危机有多种解释:因欧美经济金融关系密切,欧债危机是受美国金融危机传染而致;因欧洲在货币统一后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导致成员国在国际收支失衡情况下缺乏财政支持恢复平衡,最终爆发危机;欧元的引入让欧元区不同国家间利率趋同,希腊、西班牙等竞争力弱的南欧国家融资成本大为降低,导致大量廉价资本流入造成了经济泡沫。
从学术角度来看,上述观点为理解欧债危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并无高下之分。但从政治上,对欧债危机的解释权则涉及处理危机所需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德国在这方面当仁不让,其对危机的解释成为正统:相关国家之所以陷入债务泥潭不能自拔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经济竞争力,长期处于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失衡的状态;二是政府缺乏财政道德自律,过度举债。既然找到了“病根”,则“对症下药”的方子也就非常明确了,就是以恢复竞争力为核心目标的结构性改革:紧缩财政,严控政府债务,削减福利,降低经济成本,恢复竞争力。
虽然德国开出应对危机的“药方”引起重债国的不满与批评,但从欧盟整体而言却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除了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德国的传统支持者外,北欧国家也认同德国对危机的解释,中东欧国家则更是紧跟德国。最终人们看到,德国倡导的“以紧缩提高竞争力”成为目前欧洲经济治理的主旋律。陷入危机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顶住国内政治压力,坚持推进结构性改革。向来以欧洲政治领袖自居的法国也主动配合,2012年8月9日,法国宪法法院判决将“国债刹车”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列入宪法;奥朗德虽打着“反对紧缩,促进增长”的口号赢得了选举,但上台后依然继承萨科奇路线,实施了一系列削减开支、增加税收的紧缩政策。就连没有太受债务危机影响的荷兰和比利时,也主动推出了自己的紧缩方案。
后危机时代的欧盟面临三个主要任务:一是恢复经济增长。当前欧盟经济的复苏仍然具有不确定,逆转的风险是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企稳回升缺乏有力支撑。消费物价指数(CPI)是衡量一国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欧元区的CPI已经长时间处于1%以下。第二,虽然欧盟经济整体实现正增长,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这种“无就业增长”如果长期持续,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完善银行业联盟的建设。银行危机与政府财政危机之间相互传染是此次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建立银行业联盟,切断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是将来预防类似危机再度爆发的重要举措。三是财政一体化。这是从根本上消除欧元制度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分离这一内在缺陷的解决途径,在基本制度层面避免危机重演。对于这三大任务,德国正凭借其主导地位进一步发挥直接影响,将自己的理念渗透到宏观层面的欧洲一体化制度建设和微观层面的经济运行之中。
二、发挥主导作用的根基
德国在欧洲形成的主导地位,绝非只是此次欧债危机催生的短暂的欧盟成员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并非德国雄厚财力在危机中凸显的“崛起幻象”。其主导地位的形成由以下因素支撑,有着较为坚实的基础。
(一)非中性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欧盟层面的许多制度安排都是非中性的,欧元体制即是一例,[1]德国从这一制度中获取的优势远大于其他成员国。这种非中性制度安排,为德国提供了向整个欧盟投放力量的支点和网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负责欧元发行的欧洲中央银行制度。
欧元诞生以前,德国马克是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马克的国际地位给德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利益,法国人甚至将马克称为德国的“核武器”。所以,德国人不仅要求把欧洲中央银行设在德国法兰克福,更竭尽全力主导对欧洲中央银行的制度设计。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应该支持欧盟总体的经济政策,其首要目标就是维持物价稳定。欧洲中央银行具有政治独立性是确保物价稳定的必要条件,[2]如果缺乏政治独立性,中央银行会被迫以印钞方式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必将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欧洲中央银行或成员国中央银行不得对欧盟及其各机构、各国中央政府、地方当局和公共部门提供赤字融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信贷便利,欧洲中央银行或各国中央银行亦不得直接购买上述机构发行的债务工具。在政治独立性与防止央行为各国政府直接融资方面,欧洲央行所获得的法律保障要超过德国联邦中央银行,因为德国议会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修改法律,改变甚至取消德国中央银行的政治独立性,而欧洲中央银行的相关法律则很难改变,需要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欧盟条约。
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和制度设计这两方面来讲,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以德国联邦中央银行为蓝本建立的。[3]这种制度设计切断了所有成员国政府从中央银行获取资金的内部融资渠道,看似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实际上对各成员国的制度约束并不相同。因为德国在外部融资渠道方面优势明显:一是凭借强大工业竞争力以大量贸易顺差的形式获取资本,二是凭借良好的信用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在经济平稳发展时期,这种制度的“非中性”作用不会显现,但在遭遇危机时,许多成员国因外部融资成本提高而无法继续对外融资,导致财政枯竭,只有德国的外部融资渠道畅通;欧洲中央银行以德国联邦中央银行为蓝本建立,德国对欧洲央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此次欧债危机中,欧洲央行与德国政府的合作非常默契,甚至有观察家认为,欧洲出现了柏林——法兰克福轴心,取代了原先的柏林——巴黎轴心。
在为应对债务危机启动的财政一体化方案中,核心条款就是要求欧盟成员国政府未来财政预算和经济政策要得到欧盟机构的批准。这一规则从表面上看对所有成员国的约束相同,也精准地指向引发债务危机的制度缺陷,但其在制度设计上对各成员国施加的压力有别。相比其他成员国,德国财政一直奉行“稳健”理念,在财政纪律、财政平衡和财政实力面状况良好,一体化方案中的“财政监督”对德国不是问题。但对其他财政纪律相对松弛、财政能力相对薄弱的成员国而言,这一政策无疑是“紧箍咒”。在这一方案设计中,德国可轻易占据财政平衡问题上的道德制高点,还可借欧盟名义以整顿财政纪律的方式向其他成员国施加影响力。正因看到这一点,尽管德国提出的财政一体化方案将大大加强欧盟委员会的权力,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仍非常谨慎地回应德国这一倡议,强调财政一体化要“一步步来”。
(二)强大的融资能力
国家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国际资本的竞争,哪个国家能够最大程度、源源不断地以低成本汲取到充足的新鲜资本,也就是说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哪个国家就会获取到竞争优势,各国融资能力的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
欧元作为一种共同货币制度,其引入后的直接后果就是重塑了欧洲的经济格局,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变革就是欧洲内部的资本流由之前围绕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中心的多边循环流动,逐渐变成了主要以德国一个中心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一对多”的双边循环流动。德国站在了整个欧洲内部资金流动链条的顶端,扮演着 “欧洲银行家”的角色。这让德国具有了其他欧盟国家无可比拟的“融资能力”。
德国这种“融资能力”的基础就是在欧元制度下被不断强化的工业竞争力。虽然战后德国在工业制造业领域的出口一直保持增长的态势,但在欧元诞生之前“德国制造”在欧洲大市场并没有获得“压倒性”的优势,更不是像近年来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其他欧盟国家出口普遍疲弱,而德国出口反而逆势增长,巨额贸易顺差频频创造纪录[4]。当时“法国制造”、“意大利制造”甚至“西班牙制造”在现代工业的不少领域都有实力与“德国制造”一争高下。20世纪90年代,德国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被称作“欧洲病夫”,远没有当今“一枝独秀”的光环。进入21世纪之后德国经济很快重新焕发活力,许多研究将德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归结为1998年施罗德上台后对德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改革,认为继任的默克尔政府之所以能够保持德国经济平稳增长并且经受住了此次欧债危机的考验,实际上是坐享了施罗德的“改革红利”。这一解释虽有道理,但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出口是德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如果以贸易顺差来衡量,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德国经济的转折点在于欧元的引入。德国贸易顺差是在2001年左右开始迅猛增长的,之后几乎是直线上扬。而施罗德担任总理时所启动的以恢复劳动力市场弹性为核心的改革是在2003年。所以很明显,德国出口的强劲增长与欧元的相关性要远大于施罗德改革。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欧元让德国享受到“双重优势”。一方面,欧元的汇率是依据各成员国的经济权重来确定的,德国与比其弱小的成员国权重相互加权对冲之后,实际享受到了比马克时代更为“便宜”的汇率,欧元的使用相当于马克“自动贬值”,这自然有利于德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其他成员国无法再通过本币贬值的方式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对“德国制造”的优势,这让原本就非常强大的德国工业很快在欧洲大市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原本能够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或者对德国有顺差的国家在欧元启动之后很多都变成了对德逆差,德国贸易顺差的一半以上都来自欧盟内部,并且这一份额在欧元引入之后一直增长迅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达到顶峰。从2001年到2012年德国积累了约1.7万亿欧元的顺差,这些巨额顺差中的很大部分又以直接投资或者金融资产投资的方式回流到其他欧盟成员国。[5]强劲的出口让德国经济很快走出20世纪90年代的颓势,赢得了国际资本市场的信任和青睐,德国国债受到追捧,收益率下降,这意味着德国能以非常低的成本来融资。
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成为了资本的避风港,进一步拉低了德国的利率水平,其融资能力在危机中被大大增强了,10年期国债利率基本都处于2%以下,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相当于德国基本可以“免费”从全球借钱。2012年5月,德国更是首次以零利率发行了价值45.6亿欧元的两年期国债,如果将通货膨胀考虑在内,这意味着有太多的投资者为了竞争到借钱给德国的机会,不仅放弃利息收益,还要“倒贴”给德国人钱。根据德国财政部的计算,因为借款成本下降,2010-2014年德国仅利息支出就节省近410亿欧元。国家层面的这种融资能力体现在微观经济层面就是企业对资本的掌控力,德国企业的融资能力远超其他成员国企业,比如一笔5年期以内的100万欧元的贷款,西班牙企业需要支付6.5%的利息,意大利企业是6.24%,而德国企业仅需4.04%。[6]德国企业融资能力让其他欧盟成员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境地。
德国通过强大的工业竞争力以贸易顺差的方式让欧洲实体经济中的资本流向德国,同时德国又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大规模、低成本地吸纳金融资本,再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将巨额资金“二次分配”到其他欧盟国家,如此循环往复。在欧盟内部的这一资本循环中,德国始终掌控着欧洲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流向,实际上扮演者“欧洲银行家”的角色。正是这一机制让德国在欧盟影响力的根基更为坚实。
(三)发挥主导作用的意愿
有观点认为,德国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欧洲债务危机应对机制最重要的支撑者,但德国并没有必要将其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欧盟层面的制度安排对德国也是一种限制,德国的权力未来将会逐渐减弱;因为与重债国关系紧张,德国的影响力在欧债危机中实际是受损的。[7]但从现实考虑,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领导权是符合德国国家利益的唯一选择。欧元区是德国经济的依托,一旦欧元区解体,将给德国带来致命打击。为了保存欧元区完整,恢复欧元竞争力,需要一个切实的经济改革方案以及保障这一方案获得实施的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监督者,目前只有德国能胜任这一角色。
默克尔曾在欧债危机期间说过一句名言:欧元的失败意味着欧洲的失败。[8]其背后无法公开表达的潜台词则是,欧元的失败更意味着德国的失败。如果欧元崩溃,德国经济将丧失巨大的战略空间,其国际地位将大打折扣。所以德国的政治精英存在一个共识:欧元现在不允许失败,将来也不能失败。[9]
有人将德国称为“不情愿的霸权”,认为正像二战后美国肩负起领导职责支撑起脆弱的西德,现在轮到德国来领导那些深陷危机的盟友,这既是为了盟国,也是为了德国自己的利益。[10]言外之意是德国并不情愿成为欧盟的领袖,其领导地位是形势所迫。但实际上,今天的德国领导人不再刻意保持政治上的低调和克制,也不再讳言德国对欧盟领导权的追求。[11]2013年总统高克在德国统一日的演讲中指出,德国要在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在现实政治中,“责任”实际上是“权力”的另一种委婉的表达。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在组成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也专门讲到“德国的欧洲责任”:欧洲的统一事业仍是德国最为重要的任务,在过去几年中,欧洲伙伴对德国的期望改变了。[12]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欧洲伙伴希望德国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德国的领导是有“民意”基础的。“协议”还写道,“欧洲正处在一个历史时刻,在这变革时期,德国作为经济强大的成员国和欧洲的稳定之锚,责任在增长,也被伙伴国寄予了特别的期望。”[13]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欧债危机中德国的领导地位确实得到加强,而其他成员国也期望德国担负起领导责任,所以德国领导地位的加强与欧盟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是大势所趋。
三、推动欧盟内部改革与对外战略调整
德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与欧盟的发展高度融合在一起,所以随着自身在欧盟地位的上升,德国积极推动欧盟内部改革与对外战略调整,以巩固和加强欧盟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优势。德国的这一努力已初见成效,并且将影响深远。
第一,提升欧盟经济竞争力。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第二季度欧元区GDP环比增长了0.3%,标志着欧元区结束了连续18个月的衰退,经济转向复苏;2014年第一季度欧元区GDP增长0.2%,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环比增长。虽然增长微弱,但仍继续了复苏的势头。2013年12月15日,爱尔兰政府在宣布正式退出由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援助计划,成为首个退出这一纾困机制的欧元区国家。这说明德国开出的“紧缩”药方虽然痛苦,但效果已现。
在欧盟的宏观经济治理上,德国所倡导的“紧缩”理念和政策最终指向并非仅仅是应对债务危机,而是结构性改革。许多欧洲国家因不合理的高福利导致本国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经济逐渐丧失了竞争力。但在选举政治下,政治领导人难以下定决心削减过分的福利。此次债务危机的爆发为欧洲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德国带领下及其作为外部监督者所施加的压力下,以整顿公共财政和恢复劳动力市场弹性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成为欧洲“政治正确”的选择。随着改革的深入,欧盟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会更为稳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也将进一步增强。
第二,启动欧盟财政一体化。此次欧债危机提供了推动财政一体化的契机。当年欧元设计者们非常清楚共同货币制度所存在的缺陷:货币统一而财政不统一。在丧失货币主权的情况下,成员国政府容易倾向于利用发债解决财政问题。如果债务负担超过了偿还能力,又没有统一的欧元区财政部在债务国与财政充裕的成员国之间进行转移支付,就会导致债务国陷入财政危机。在共同货币制度设计之初,由于成员国难以接受本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和支出最终由欧盟批准,更不愿用本国财政收入补贴其他成员国债务,因而在政治上难以一次性地让成员国全部同时交出货币主权和财政主权。欧元设计者退而求其次,率先实现欧元统一,日后择机实现财政统一。[14]欧元设计者的逻辑是:统一货币需要共同预算,而共同预算又需要共同的议会,这样就把欧洲引上了联邦之路。[15]此次欧债危机激活了欧元设计者的最初设想,财政一体化被提上日程。
德国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设“政治联盟”的欧洲愿景,其核心即实现某种形式的欧盟财政一体化。德国对财政一体化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允许欧洲央行逐渐担负起“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可以向成员国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流动性,可以购买成员国国债。该政策的实际效果相当于形成一个“隐形”的共同财政,把富裕成员国的资金转移支付给危机国家;二是以财政契约的方式约束成员国的预算和支出,同时寻求修改欧盟条约,将成员国更多的财政权上交给欧盟。这意味着欧洲财政一体化的进程已经正式启动,欧盟的制度建设进入新阶段。这不仅将大大加强欧盟抵御外部金融风险的能力,也将有力地提升欧盟的国际地位。
第三,推进欧盟“大西方”战略。当今世界格局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根据IMF的最新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首次超过50%。[16]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劳伦斯·萨默斯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变化背后的重大意义。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30多年,这种变化发生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涉及到数以亿计的民众,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甚至可能超过后两者。因此,当今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管理大国的崛起。[17]
所谓“管理大国的崛起”就是发达国家需要一个“再平衡”,平衡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崛起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格局的冲击。美国的“再平衡”就是要“重返亚太”,而欧洲的“再平衡”则是积极推动发达国家间更紧密合作,努力组建一个制度化、机制化的发达国家间政治、经济以及金融集团,也就是布热津斯基笔下的“大西方”。这就是欧洲人力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与日本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区(FTA)谈判的原因。
德国是欧盟“大西方”战略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默克尔在2005年上台后就把加强欧美关系放在优先位置,2006年提出建立欧美自贸区设想,2007年初在访美时正式向小布什提出这一倡议。2013年10月,欧盟和加拿大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这是八国集团成员之间首个自贸区协定,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这背后与默克尔的努力密不可分,2012年8月,默克尔访问加拿大专门就欧加自贸区细节问题与加总理进行商谈。默克尔再次当选总理后,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和北约框架内的合作仍然是德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础。[18]
四、结语
德国在欧盟的重要地位并非始于欧债危机,但是此次危机确实提供了一个让德国从幕后走到前台的契机。欧盟当前的内部改革和对外战略调整中,德国无论是在理念的提出还是政策的实施方面,都起到了关键的引领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欧盟的发展将会带上相当程度的“德国色彩”。近年来中德关系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2013年中欧光伏产业贸易争端中,欧盟之所以最终改变强硬态度,放弃单方面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贸易争端,德国起到了很大作用。德国在欧盟的主导作用会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中国与欧盟打交道的协调成本,但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德国的政治精英更多地是把中国定位成一个挑战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19]德国政府在2013年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明确提出“要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深化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支持美国的亚太政策,这显然是出于平衡中国的考虑。虽然德国政府认为,由于存在多样化的“共同利益”,中国是德国和欧盟的战略伙伴,但是德国仍然要“致力于使中国在宪法中所承诺的权利以及对普遍人权的保障能够得到尊重”。[20]也就是说,德国要“监督”中国的人权建设,这明显有悖于双方“战略伙伴”的定位。德国的这种“中国观”将会是中德关系未来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这种“中国观”不变,那么长期来看,德国在欧盟的主导地位无疑会增加中国处理对欧关系的难度。
注:
[1]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所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有的人多,有的人少;甚至在很多时候同一制度能够为一部分人带来利益,却给另一部分人带来损害。这一现象被称为“制度非中性”。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第98页。
[2]欧洲中央银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以及任何决策执行机构的人员,在执行或实施《马约》赋予的权力与义务时,均不得寻求或接受来自欧盟或者欧盟各机构、任何成员国政府、以及任何其他机构的指示。
[3]关于欧洲中央银行以德国联邦中央银行为蓝本的相关论述,本文主要参考:[比]保罗·德·格劳威著:《货币联盟经济学》,汪洋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129-130页。
[4]德国对外贸易顺差在欧债危机期间经历2008、2009两年的短暂下降后,从2010年开始持续反弹,2012年德国对外贸易顺差为1881亿欧元,创下战后以来的第二高顺差额的记录,最高的顺差额是欧债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的1953亿欧元。2013年前三个季度德国的顺差就达到了1478亿欧元,其中2013年9月的顺差额为204亿欧元,创下战后单月最高顺差额记录,之前单月最高顺差额是2008年6月的198亿欧元。2013年德国的外贸顺差为1989亿欧元,是德国有外贸统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数据源自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库,https://www.destatis.de。
[5]根据德国联邦银行的统计,德国的贸易盈余一半左右来自欧盟内部,而这些盈余中的大部分又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输出到欧盟成员国。根据德国联邦银行的统计,德国对外直接投资(FDI)的一半以上流向了欧盟成员国。
[6]Niedrige Zinsen,“Deutsche Firmen Profitieren von Euro-Krise,”September 4,2012,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ezb-zinsen-fuer-unternehmen-in-der-euro-zone-driften-auseinander-a-853728.html.(上网时间:2014年5月30日)
[7]Daniela Schwazer and Kai-Olaf Lang,“The Myth of German Hegemony,”October 2,2012,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8162/daniela-schwarzer-and-kai-olaf-lang/the-myth-of-german-hegemony.(上网时间:2014年6月5日)
[8]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会的演讲,2011年9月7日,http://www.bundeskanzlerin.de/ContentArchiv/DE/Archiv17/Reden/2011/09/2011-09-07-merkel-bt-haushalt.html。(上网时间:2014年6月5日)
[9]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会的演讲,2011年9月7日,http://www.bundeskanzlerin.de/ContentArchiv/DE/Archiv17/Reden/2011/09/2011-09-07-merkel-bt-haushalt.html。(上网时间:2014年6月5日)
[10]“The Reluctant Hegemon?”The Economist,June 15,2013,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579456-if-europes-economies-are-recover-germany-must-start-lead-reluctant-hegemon.(上网时间:2014年6月3日)
[11]“New Power New Responsibility:Elements of a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 a Changing World,”SWP and GMF,October 2013,p.2,p.20.
[12]“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18 Legislatur periode,p.156.
[13]Ibid.
[14]张宇燕:“债务危机与世界经济”,《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31-32页。
[15]丁一凡:《欧洲时代》,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16]“World Economic Outlook:Recovery Strengthens,Remains Uneven,”IMF,April 14,2014,p.159.
[17]劳伦斯·萨默斯:“中国崛起及中美两国的金融监管”,《研究参考》,第21号(总106号),2011年7月8日,第1页。
[18]“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18 Legislaturperiode,pp.168-169.
[19]“New Power New Responsibility:Elements of a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 a Changing World,”pp.33-36.
[20]“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18 Legislaturperiode,p.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