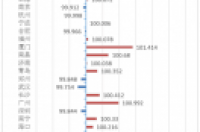大衰退的结束重燃了对美国制造业未来的乐观态度。2010年第二季度,美国制造业雇佣工人数量呈现了正增长,这是自2006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并且在接下去的10个季度里就业均有增加,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扩张。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工业转型的潜力,他们对于之前美国制造业的困境给出了正面的解读:虽然21世纪前十年的就业有所下降,但工业增加值保持了与整体经济持平的增速。工业部门占美国GDP比重保持在稳定的水平,这是同一时期其他高收入经济体罕见的成就。商业媒体使用“回岸”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美国公司将此前离岸给一些低工资地区的就业岗位回归到本土的现象,尽管这种现象并未被证实。
在宣布美国制造业复兴之前,有必要再次评估该部门此前衰退的规模,并思考导致就业减少的因素。就业水平缩减的规模着实令人震惊。从图1可以看到,2000年时,美国有1730万工人受雇于制造业,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期性涨落中的正常水平。到2010年,就业数量下降到1150万人,相比2000年下降了33%。出人意料的是,大部分下跌发生于大衰退正式开始之前。2007年年中,雷曼兄弟崩盘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瘫痪的前夕,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水平就已经降为1390万人,即从2000年到2010年间全部岗位损失的五分之三都发生在美国经济总体收缩之前。图1还展现出近期工业复苏杯水车薪的影响。就2014年年中情况而言,制造业就业人数只有1210万人,比起衰退之前的水平还相差甚远。
我们考察了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原因,我们的出发点是21世纪前十年里美国制造业的黯淡正好对应着来自中国进口竞争的显著加剧。从1990年到2011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总出口的比重从2%增至16%。这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采取深入的经济改革措施的结果,并由2001年该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得到了进一步扩展。与在全球范围的表现一致,中国占美国制造业进口的比重也从1991年的5%上涨到了2001年的11%,在2011年更是跃至23%。中国的崛起是否是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原因呢?
首先,我们估计了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美国制造业的直接冲击。设想一下,中国的经济开放使得该国能够实现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而这种优势在毛(泽东)时代中央计划的体制下因为重重贸易障碍而无法施展。改革使得中国劳动力和资本从农场转向工厂,从无效率的国有企业转向更有效率的私人商业,比较优势最强的部门产出将得到扩张。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足,可耕地和自然资源相对稀缺,因此制造业成为了改革所倡导的工业重组的主要受益部门。中国向制造业的转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又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而大大强化。中国占据了自1990年以来低收入与中等收入经济体工业增加值所有增长的四分之三。
对于许多美国制造企业而言,来自中国进口竞争的加强意味着对他们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他们雇佣工人的数量也会随之缩减。通过考察美国制造业内与中国进口商品有竞争的部门,我们估计,如果没有1999年之后来自中国的进口渗透,到2011年时制造业岗位的损失将减少56万。实际上,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水平从1999年到2011年减少了580万,我们所估计的中国进口渗透对就业损失的直接影响占据了实际制造业就业缩减的10%。
这些直接影响并没有捕捉到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对美国就业水平的全部冲击。对某一行业的负面冲击将通过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传导到其他行业。联系的纽带之一就是“买方-供给方”关系。在服装和家具部门日益加剧的进口竞争(这两个部门正是中国的优势),将使得下游行业减少向提供织物、木材、纺织品和伐木器械等的上游部门的采购量。由于买方和供给方的位置通常彼此毗邻,下游行业贸易开放度上升所带来的冲击很可能传导至同一地区或市场的供货商。我们使用美国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了制造业与非制造业行业的下游贸易冲击。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复苏对下游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将直接影响与利用投入-产出所估计出来的影响加在一起,我们对于1999年到2011年由于贸易所导致的制造业就业损失的估计上升到了98.5万人次,而整体经济的就业损失则是200万人次。行业间的联系强化了贸易冲击的就业效应,将制造业内的冲击规模扩大了近乎一倍,对制造业之外的就业也产生了规模相当的作用。
其他两种联系不同部门的因素是总需求的变动和劳动力的再分配。当制造业萎缩时,失业工人或收入降低的工人将缩减他们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通过标准凯恩斯的传导机制,即抑制总消费和总投资,需求缩减对于整体经济的作用是翻倍的。从制造业脱离的工人可能在服务业或经济的其他部门就业,弥补了部分在贸易开放行业的收入损失,从而抵消了一些负面总需求效应。因为总需求效应和就业重新配置效应的方向是相反的,我们只能识别它们对总体就业的净效果。更深一步的问题在于,这些效应在总体经济的层面上发挥作用,而不像贸易冲击的直接影响和投入-产出效应那样在行业层面上起作用,这意味着我们所能拥有的数据点与自中国的贸易冲击开始的年份相同。因为中国的出口浪潮直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才全力涌现,美国国家层面可得的时间序列就非常短。
为了应对这一数据问题,我们使用地区经济的数据来完善对于美国产业的分析。我们将包含着清晰的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有商业联系的郡县加总,定义为“通勤区域”。因为通勤区域内各自的行业分工模式迥异,它们所面对的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增长的情况也不相同。北卡罗来纳州的阿希维尔是一个家具制造中心,是中国进口竞争的直接受影响地区。与之对照,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迪士尼和哈利波特主题公园所在地),聚焦于旅游业,受制造业产品进口增长的影响较轻。如果再分配机制起作用的话,中国竞争的结果使得某地本土产业萎缩,那么在同一个通勤区域的其他产业就应该扩张。总需求效应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也有作用,如果某地因为贸易开放而减少了总就业,缩减的收入将降低对非贸易的本地商品与服务的支出,在整个本地经济中扩大冲击。
我们对于总需求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净冲击的估计表明,1999年到2011年来自中国进口的增长导致了就业下降240万。这一数字比之前我们仅捕捉直接和投入-产出效应对全国产业估计得到的200万稍大一些,但仍可能低估了中国冲击美国就业的全部后果。不论是关于通勤区域的分析,还是关于全国产业的分析,各自都没有完全包括另一种分析的调整渠道。基于全国产业的估计排除了再分配和总需求效应,而通勤区域的分析则排除了这两种效应的全国性因素,以及投入-产出联系效应的非本地因素。因为通勤区域的估计表明总体的力量扩大而非抵消了进口竞争的影响,我们将基于产业水平的估计视作就业损失的保守下限。
我们的发现对于美国制造业复苏的潜力有何启示呢?近年来美国制造业进口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劳动力密集产品中拥有强大比较优势。美国在服装、家具、鞋类和其他工资敏感性产品上损失给中国的岗位不大可能回来。即使中国的劳动成本上升,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更有可能转向孟加拉、越南或其他崛起的国家,而不是重新出现于美国本土。而且,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远没有结束。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迅猛地进军手提电脑和手机的组装行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出现,比如联想和华为。虽然前景看起来相当惨淡,但美国的制造业仍有希望。或许最振奋人心的迹象就是许多面对贸易冲击的企业开始增加对创新的投资。技术的进步最终可能为美国的生产商创造新的市场。然而,如果制造业常规岗位自动化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这些新技术的运用可能更多地推动增加值的增长,而非增加进入工厂就业的工人数量。
本文作者:
Daron Acemoglu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David Autor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David Dorn为瑞士苏黎世大学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主席,Gordon H. Hanson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经济关系主席、新兴与太平洋经济中心主任,Brendan Price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候选人。
注:
本文原题名为“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US manufacturing”。
本文于2014年9月28日刊于VOX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