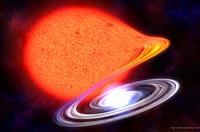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和环境上访数呈现增长趋势(童志峰,2008;张玉林,2010)。无论是城市里的“邻避运动”,还是乡村的“生存抗争”,此类群体事件多由环境污染、危害健康及相关的赔偿等问题引发。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对环境风险的惧怕无疑是环境群体事件出现和增长的直接动因。近年来,环境风险在人群中是否公正分配的争论,正日渐成为推动环境集群行动发展的一股新动力 。国际研究表明,社会发展进程中,历史烙印对环境风险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如种族区隔、贫富分化,导致有限环境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人群在环境污染中的不合理暴露 ,而这些都是推动环境集群行动和环境运动发展的动力(Mohai,et al.,2009;Mohai & Pellow,2009; Schoolman & Ma,2012;Faber & Krieg,2002)。当下我国正处社会转型期,环境污染和保护问题逐步得到重视,但环境风险公正分配问题尚未引起社会管理者的足够重视。我们需要弄清楚,当下中国“谁在承受何种程度的风险”,即环境风险在人群中的分配状况和依据,这亦是本文主旨。
本文选择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风险为例,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我国城市垃圾产量剧增,垃圾处理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 ,亟待解决;其二,垃圾处置是涉及城市规划布局、环境治理、技术革新和政策安排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社会问题,程序公正和社会公正在垃圾处置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其三,垃圾处理产生的风险具有多重性和积累性,在地理空间上与垃圾处理单位的接近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暴露在多重风险(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噪声、有毒物质吸纳、心理压力等)中的概率。这种复合性风险在社会空间中如何分配,哪些人承担更高环境风险,为什么出现这种分配格局等话题是本研究所关心的。
二、文献评述与研究设计
1978年的“爱河事件” 和1982年的“瓦伦郡运动”开启了美国甚至西方社会反有害废弃物歧视性选址处置和反环境种族主义的历程。自此以后,国外研究者对风险分配的依据和后果进行了大量研究。
理性选择论者认为市场是环境风险分配的风向标,工业选址和居民选择居住地都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转引自洪大用,龚文娟,2008)。具有地价低、较低的污染损失赔偿等特征的地区,往往能吸引污染单位来此选址,同时也吸引穷人和低收入的外来流动人口来此就业和居住,而社会中上层人群则逃离这些地区,由此造就了人群不成比例地承担环境风险的局面。与此相左的观点认为,环境风险的分配并非单纯市场自主选择的后果,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主要依据。数十年来,种族和社会阶层差异被西方学术界视为有害工业歧视性选址、废物商业化以及人群在环境风险中不合理暴露的关键影响因素(Bullard,1990; Mohai & Bryant,1992; Gary & Elyse,2002;Pearce & Kingham,2008;Mohai,Pellow and Roberts,2009)。在美国,种族和收入甚至成为预测反环境的工业企业和有害废物处置设施在何处选址的重要人口学指标(Faber&Krieg,2002)。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个体和社区的社会资本和政治力量也是影响环境资源和风险在人群中不合理分配的重要因素(Saha & Mohai,2005)。甚至有研究者指出不同人群不成比例承担环境负担与政治边缘化有关,且二者交互作用,相互强化(Schoolman & Ma,2012)。
来自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美国、瑞典等国的大量研究表明低收入社区的人口面临的物理环境和居住条件比高收入社区人口的更差(Bullard,1983;Jerrett,et al.,2001; Brainard,et al.,2002;Brulle & Pellow,2006;Chaix,et al.,2006;Pearce & Kingham,2008)。种族、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和可动员的社会资本、所属社区总体资本存量等要素,都可能对个体是否遭受环境风险及遭受何种程度的风险造成影响。
西方环境公正研究三十年,其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改进。从早期经典的“空间单位分析法”(Unit-based method),到Mohai等人提出的“距离分析法” (Distance-based method),再到风险/暴露分析法 (Risk/Exposure-based method),每一种方法都希望克服已有方法的缺陷,为环境风险分配研究提供多视角、系统的方法支持。综合它们得出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少数种族和穷人居住在比白人和富人距离环境污染源更近的地方,并且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转引自Ma & Schoolman,2010)。
在我国,环境风险分配和环境公正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环境风险公平正义分配的讨论更多来自于政治学、伦理学和法学,而基于环境社会学视角的实地一手数据的量化研究鲜见,且由于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不一致,导致研究缺乏系统性。当然,西方社会的研究方法和发现对中国的现状是否具有普遍解释力,值得商榷。以种族为例,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并不存在种族和种族歧视问题,“民族”与“种族”不管在学理上,还是政治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的环境公正是否能够单纯依靠收入(income)来解释,还有哪些社会经济因素可以解释中国的环境风险分配问题。事实上,我国的社会结构具有特殊性:第一,创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现代户籍制度,被视为“中国特色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性守卫者。它对居民的收入、教育、福利待遇、个人生活方式,甚至人生历程产生深刻影响;第二,单位制(Units)作为曾经最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管理制度,走过了发展、扩张到弱化的道路,那么在社会转型期,它是否对环境风险在人群中的分配具有影响,有待考量;第三,城镇化和市场化打破了户籍制曾经对人口流动固若金汤的限制,使得大量低学历乡-城移民流入城市,成为工作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城市融入性,收入、社会保障与维权,子女受教育等问题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李培林,1996;王春光,2011;李强,2001;叶静怡,2010;陈云松,2012;戴国立,2008;赵蔚蔚等,2011),但就他们的环境风险承担问题,却较少讨论。因此,有必要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尝试借鉴西方社会对环境风险分配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分析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环境风险在人群中的分配问题。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初步判断,经济收入、户籍身份、住房地位等社会经济因素比种族对中国的环境风险分配问题更具有解释力。本文的基本假设是: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居住地接近大型垃圾处理单位的可能性越高,暴露在环境风险中的可能性越高。数据处理方法是,通过控制性别、年龄、城市等变量,使用Logistic回归估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与其是否居住在距离大型垃圾处理单位3公里范围内之间的关系;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与其风险暴露状况的关系。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公众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及行为研究”,项目组于2011年至2012年在北京、重庆和厦门三地 进行了有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环境影响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本研究实际调查单位见图1。
我们采用了多阶段混合抽样方法获取样本:第一阶段,采用立意抽样方法,依据三个城市的垃圾处理单位分布状况和城市人口分布状况,抽中北京市海淀区、朝阳区、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重庆市渝中区、沙坪坝区、渝北区、南岸区、江北区、北碚区,厦门市湖里区、思明区、海沧区和翔安区为初级抽样单位;第二阶段,按“概率与元素的规模大小成比例”原则,抽取街道、乡镇;第三阶段,在街道、乡镇中随机抽取社区居民委员会/村委会,并以此为三级抽样单位;最后在居委会/村委会中随机抽取家庭,并在每户中确定1人为最终调查单位。我们采用专业调查员与受访者一对一,由调查员依据问卷逐题询问并填答的方式进行了调查。三地共发放2050份问卷,有效回收1953份,有效回收率为95.3%。所有调查对象均为18-70岁的居民,其中,29岁及以下占27.8%,30-39岁占28.7%,40-49岁占19.3%,50岁及以上占24.2%;男性占49.6%,女性占50.4%。针对典型案例,我们进行了深度访谈。
图1 (略)
(二)变量及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包括两项:居住地与大型垃圾处理单位“距离”和居民风险暴露状况。前者为二分变量——居住地距离大型垃圾处理单位3公里以内,3公里以外。在一些使用“距离分析法”估计风险在人群中分配状况的国际研究中,研究者们通常以1英里或2英里 作为选样范围的半径(Chakraborty & Armstrong,1997;Mohai&Bryant,1992;Pastor,etal.,2005;Dolk,etal.,1998;Geschwind,et al.,1992),本研究借鉴于此。此外,我们感兴趣的是大型垃圾处理单位在人群中的一般分布模式,在此并没有区分不同类型垃圾处理单位(例如垃圾焚烧厂和垃圾填埋场)。本研究以3公里为辐射范围的半径,分析范围内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构成。这一变量的赋分方式为:居住地在3公里及以内赋值1,3公里以外赋值0。
另一因变量“环境风险暴露”,通过询问被访者“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下列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您的生活?”来测量 。通过臭味、污染水源、噪声、土壤污染、病菌、心理压力、健康问题等7项指标度量居民所经历的风险,每一指标被划分为五个等级:严重影响、有些影响、不清楚、没什么影响、完全没影响,并分别赋分5-1分,得分越高表明遭受的风险越高。统计检验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信度,Cronbach’s Alpha为0.924。
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十项指标: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单位类型、行政级别、家庭年总收入、家庭月消费水平、房产价值、户籍、居住地类型和是否农民工身份。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是衡量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指标(胡荣,2003;冯仕政,2007;Gary & Elyse,2002;Mohai,2009);户籍和农民工身份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安排和产物;考虑到社区的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分布不均衡可能导致环境风险不公正分配,以及“住房地位群体”在我国日渐兴起(李强,2009),我们亦将居住地类型和房产价值纳入分析框架。
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五个层次;职业地位采用李春玲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单位类型为三分变量,国有单位、非国有单位和无单位;行政级别划分为局级及以上、处级、科级、科级以下、无级别五个层次;家庭年总收入,指“全家所有成员的全部工资、各种奖金、补贴、分红、股息、保险金、退休金、经营性纯收入、租金、利息、馈赠等”;家庭月消费水平主要以受访者全家每月生活费用来衡量;房产价值指受访者拥有的所有具有部分或全部产权的房屋的价值;同时,将“户籍”“农民工身份”和“居住地类型”作虚拟变量纳入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体系,居住地类型指居住社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
3、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和城市作为控制变量。
表1(略)
四、分析与发现
首先,我们对居住地距大型垃圾处理单位3公里以内和以上的居民人口构成进行了分析(见表2)。初步分析发现:除性别和年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均通过检验。说明在居住地距离垃圾处理单位远近的问题上,男性和女性没有显著差异,不同年龄层的人群也没有显著差异。居住地距离垃圾场3公里内外的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呈现出差异,3公里范围内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71.6%,大专及以上占28.4%,3公里以外高中及以下占49.9%,大专及以上占50.1%。不同年收入的家庭在垃圾场外围的分布也存在差异(X2=103.987,p≤0.001),3公里范围内有60.7%的家庭,其年总收入在5万元以下,年总收入10万以上的家庭占11.8%;3公里以外,5万元以下家庭占31.3%,10万元以上家庭占35.8%;另外,年收入1万元及以下的组内比较显示,76.6%的低收入家庭居住在距垃圾场3公里范围内,23.4%低收入家庭居住在3公里以外。同样,家庭月消费水平和房产价值在两组不同人群中也呈现出差异:消费水平较低和房产价值较低的人群居住在3公里范围内的比例更高。就职业地位而言,距垃圾场3公里以内人群中,非国有单位的受访者比例最高,无行政级别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再来看户籍身份特征,3公里范围内,农业户口者比例略高于非农户口者比例,身处农村社区的居民比例高于城市社区居民比例。而农民工与非农民工在垃圾场外围的分布,无论3公里以内还是3公里以外的农民工比例均低于非农民工比例,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农民工样本较少的缘故(农民工占总样本的14.4%)。这些发现部分与国外研究一致,如Mohai等人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地影响人口居住距离污染企业的远近。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较更高年收入家庭更可能居住在距离污染企业1英里的区域内;高中以下学历的人口明显比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居住地更接近污染企业。相反的是,他们认为居住在城市及郊区的人口比居住农村地区的人口距离污染工业单位更近(Mohai,et al.,2009)。
表2(略)
然后,我们对居住地距离大型垃圾处理单位3公里以内和以上人口的风险暴露状况进行了分析(见表3)。通过均值比较发现,除噪声污染在两个群体中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外,其他六项垃圾处理带来的风险,对居住在3公里以内的居民的影响均高于对3公里以外居民的影响(t检验,p≤0.001)。垃圾处理对3公里以内居民最突出的影响是臭味,其次是滋生病菌,再者是危害身体健康,这三项得分均值都在4分及以上。垃圾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气体、粉尘、二噁英等有害物质使附近居民的呼吸道类、皮肤类疾病的患病率较高,居民的非正常死亡率间接指向垃圾处理给周边人口带来的健康风险。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什么3公里内居民的心理压力高于3公里以外的居民。如果以大型垃圾处理单位为圆心,3公里为半径画圆,环境风险在地理上是从内向外逐步推出去的,而居住地因距离圆心的远近不同,承受的环境风险自然不同。
表3(略)
为了进一步考察居民身份构成与环境风险社会空间分配状况的关系,我们使用了Logistic回归分析和OLS回归,分别对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与污染源接近性,及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暴露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表4报告的是用居民社会经济地位预测污染源接近性的结果。第一层模型为基准模型,控制基本人口特征与城市类型对污染源接近性的影响,模型Ⅰ增加了职业地位变量,模型Ⅱ增加了家庭经济状况变量,模型Ⅲ增加了户籍身份变量。
表4(略)
在四个模型中,性别和年龄对因变量的影响都没有统计显著性,而城市间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有意思的是,在模型Ⅱ和模型Ⅲ加入经济收入指标和户籍后,北京的统计显著性消失。说明城市间的差异,特别是北京市与其他两市的差异,是通过经济收入指标和户籍呈现出来的,换句话说,收入与户籍在北京市是影响污染源接近性的重要因素。
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城市后,受教育程度展现了稳健的影响作用。模型Ⅰ,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居住在距垃圾处理单位3公里范围内的可能性是本科及以上人口的5.22倍(e1.653)。尽管加入经济变量和户籍变量,发生比有所降低,但仍能证明:受教育程度越低,居住地接近垃圾处理场的可能性越高。职业地位对垃圾场接近性的影响力由模型Ⅰ的微弱,到模型Ⅱ和Ⅲ消失,说明职业地位对垃圾场接近性的影响作用不大。单位类型在模型Ⅰ中,国有单位就职者居住在距垃圾场3公里范围内的可能性是无单位者的24.6%(=e-1.403),非国有单位者是无单位者的22.1%,但随着经济和户籍指标的加入,这种影响力在降低。这一点在行政级别上体现得更明显,行政级别中仅“处级”对污染源接近性有显著影响,其他几个级别的影响均不显著。拥有处级身份的居民居住在垃圾场3公里范围内的可能性是无级别居民的31.4%(e-1.158),加入户籍变量后,这一发生比增加到35.7%(e-1.029)。说明单位类型和行政级别对居住地距离垃圾场接近性的影响是通过户籍制实现的。单位类型和行政级别在我国曾作为衡量个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指标,但随着市场化和住房商品化的推进,它对人们居住地和住房选择的影响在逐步降低。
模型Ⅱ引入了家庭年收入、月消费水平和房产价值等家庭经济状况变量。发现,家庭年收入和房产价值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家庭月消费水平影响不显著。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及以下的家庭,居住在距垃圾场3公里范围内的可能性是年收入10万以上家庭的3.858倍(e1.350),即便加入户籍身份变量后,这一比也为2.957倍(e1.084),其他两组收入的家庭也显示出了类似差异。同样,房产价值也成为预测居住地与垃圾场接近性的一个稳定指标,房产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家庭,居住在距垃圾场3公里范围内的可能性是房产价值500万以上家庭的31.11倍(e3.438),即便加入户籍身份变量后,这一比也为24.50倍(e3.199),而房产价值在200-500万之间的家庭与500万以上家庭的这种发生比就大为降低,前者为后者的2.214倍(e.795)。随房产价值的提高,居住在距垃圾场3公里范围内的可能性逐步降低。模型Ⅲ引入户籍、居住地类型和农民工身份变量。拥有农业户口居民居住在距垃圾场3公里范围内的可能性是非农居民的2.016倍(e.701);居住地为农村社区,其接近垃圾场的可能性是城市社区的7.519倍(e2.017);而农民工居住在垃圾场3公里范围内的可能性为非农民工的29.2%(e-1.230),换句话说,并未发现农民工比非农民工更多地居住在接近垃圾场的地方,这与前文初步分析的结果一致。尽管由于本研究农民工样本较少,并没有证明农民工比非农民工更多聚居住在接近污染源的范围内,但两次检验都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农民工身份可以预测人口与污染源的接近性。
表5报告了用居民社会经济地位预测环境风险暴露的结果。第一层模型为基准模型,控制基本人口特征与城市类型对风险暴露的影响,模型Ⅰ增加了职业地位变量,模型Ⅱ增加了家庭经济状况变量,模型Ⅲ增加了户籍身份变量。四个模型都通过了F检验,具有统计显著性,并且随着变量的加入,模型解释力逐渐增强。
表5(略)
在基准模型中,人口特征和城市能解释风险暴露2.7%的方差。具体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暴露在风险中,女性的生理特性(如月经周期、怀孕、哺乳等)和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如照顾家庭),要求她们与环境之间保持紧密联系,从而使女性对环境具有较高依存度,使得女性在面对环境风险时比男性更加脆弱和敏感;重庆居民暴露在垃圾处理风险中的可能性高于厦门居民,而北京的不显著,说明垃圾处理产生的风险及人群在风险中暴露状况存在地区性差异,这与各地居民生活、消费方式,城市垃圾处理模式,垃圾处理设施和人口分布等因素都有关;年龄对风险暴露状况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Ⅰ引入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地位变量,模型解释力提高了3.7%。受教育年限越长,遭受的环境风险就越低。单位类型和行政级别对风险暴露的影响不显著,并且这种不显著随着经济变量和户籍变量的加入,并没发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位制”对国人生活的影响面和影响力在逐步缩小和下降,倚重职业的行政级别对风险分配的影响力也不及二十年前那么强烈了 。模型Ⅱ引入家庭经济状况变量,模型解释力提高到10.5%,家庭年收入、月消费水平和房产价值与风险分配间呈负相关。说明家庭经济状况越好遭受的垃圾处理风险越低。良好的经济条件一则可以通过选择居住空间,规避垃圾处理风险,二则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条件(如购买净水器,空气净化机等),最大程度降低风险。模型Ⅲ引入了户籍身份变量,模型解释力提高到17.6%。农业户口居民比非农户口居民遭受更高的垃圾处理风险,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居民比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居民遭受更高垃圾处理风险。农民工身份与风险暴露的关系不显著,并未发现农民工遭受的垃圾处理风险高于非农民工。
上述分析表明,第一,城市间的垃圾处理风险在人群中的分配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受经济收入和户籍身份的影响明显;第二,低受教育水平者、低收入家庭、农业户籍者、居住在农村社区的人遭受的垃圾处理风险高于高受教育水平者、高收入家庭、非农户籍和居住在城市社区的人口。从风险制造者角度分析,他们不希望在方案执行过程中遭遇强烈抵抗,或者至少希望能与当地居民讨价还价,所以通常会遵循“最小抵抗原则”。显然,与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相比,只有缺乏良好教育、低收入的弱势人群才具备“最小抵抗力”。从风险承受者角度分析,处于社会阶梯上端的人群在风险发生前,可能通过动员多种社会资源规避风险(如通过多种途径抵制大型污染设施不公正选址),即便环境风险降临,他们也有能力“用脚投票”;而同为风险承受者的低学历、低收入群体,既不具备风险转移能力,也不具备风险规避能力。一些社会底层人群,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和工作,甚至出现“自愿的”风险暴露人群。户籍制度是我国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制度安排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分,不仅使风险转移到农村地区,还通过对城市空间安排和布局,使那些流入城市却带着农业户籍身份的人群,在城市仍然面临风险。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环境风险在人群中的社会空间分配状况分析发现,我国存在基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不公正环境风险分配问题。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城市变量后,低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房产价值、农业户口和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居民明显地比高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房产价值、非农户口和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居民,更可能居住在接近大型垃圾处理单位的地方,并承受更高环境风险。而单位类型、行政职务和农民工身份,不能对污染源接近性和风险暴露情况产生稳定的预测作用,但也并非完全不相关,只是随着经济收入和户籍等变量的加入,统计显著性减弱或消失。
研究发现给了我们三点启示:第一,户籍对污染源接近性和风险暴露具有明显影响作用。尽管户籍制有了松动的迹象,但其影响力仍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延续。户籍制对中国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犹如种族在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体现在城市内部,通过城际比较,还发现其影响在城市间差异明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购房(包括各类保障房、经济适用房)、教育、就业、保险、医疗资源等民生问题直接与户口挂钩,而这些与健康相关的资源不同程度地导致了低收入群体的脆弱性再生产。这一点也回应了环境公正中有关资源分配问题的讨论,特别是由制度安排导致的资源和风险分配不公,导致的弱者越弱。跟户籍制相关的另一话题是农民工群体的风险暴露问题。虽然在本文中,农民工身份与污染源接近性和风险暴露的关系没有得到确切证实,但根据显著性检验和实地走访判断,这种拥有农业户口的乡城移民身份会影响他们的居住区位分布,这也间接证明了户籍制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影响力。第二,社会经济地位影响风险在人群中的分配,进而,风险分配状况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 。那些处于不利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更可能遭受不利物理环境给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O’Neill et al.,2003),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社区,其居民的健康状况比居住在条件良好社区的居民的健康状况差(Thomas et al.,2010),从而,居民健康状况呈现地理区位差异化和空间区隔化。由制度安排造成的健康地理区位差异化,可能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社会经济地位、风险分配和健康之间的恶性循环——社会经济地位形塑风险地位,风险分配影响健康,健康状况反过来影响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变化(如因病致贫);二是人们对不公正风险分配带来的疾病的惧怕和对后代健康的担忧,可能激起他们的风险应对行为,包括极端的暴力抗争。这些都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构建。第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因素和一些非个人的制度、市场因素(如工业发展的历史模式、产业重组与经济调整、劳动力流动、城镇化和居住区隔等),使得社会下层人群——无论是美国的少数种族,还是中国的低收入者或农民工(Ma & Schoolman,2010;Schoolman & Ma,2012)等——正不成比例地承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环境后果,这背后揭示的是社会制度安排、政治过程对弱势群体的多重剥夺——生存空间选择权、环境权、公共事务参与权。反之,作为一辆往复循环的“苦役踏车”,削权行为一方面导致弱势群体脆弱性再生产,另一方面又积累了被剥夺人群的抵触和抗争情绪。社会和政治发展要求对社会空间和制度安排进行合理调整,这是必然,但不必然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为代价。
基于上述结论和讨论,我们得出一些政策启示:
第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有序地“统一户籍、普惠权利”,通过完善跨区域的城乡统一社会保障体制,逐步减少环境资源和风险分配不公。改革的关键是户籍内含的各种权利和福利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户籍制度影响环境不公正的途径是通过身份歧视,形成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等,进而导致不同群体面临环境风险时应对能力和承受能力差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均等化公共服务,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特别是公民享有非歧视的环境权。当然,考虑城际间的发展差异(经济、文化等方面),需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
第二,完善环境立法和政策,特别是针对具有环境负外部性的大型公共设施和工程(如垃圾处理单位,重化工项目,核电站等),并形成对弱势群体的环境风险补偿和保护机制。环境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其宗旨是环境资源和风险在人群中公正分配,通过完善环境立法和政策,保证弱势群体(如城市低收入者,农民工等)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并通过国家统筹安排,对已遭受环境损害的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和法律援助,更大程度地保护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
第三,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具有环境负外部性的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属于公共事务,应广开言路,听取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张。由此,呼吁逐步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并规范公众参与行为,让松散的公众参与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在环境风险应对和环境管理问题上,让公众听证、多方协商互动、民意调查、公众监督等利器有效运转起来,不仅有利于环境公正的构建,更有利于可持续和谐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陈云松:《农民工收入与村庄网络》,载《社会》2012年第4期。
戴国立:《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产生原因探索》,载《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6期。
冯仕政:《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洪大用,龚文娟:《环境公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胡荣:《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李培林:《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李强:《转型时期城市“住房地位群体”》,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卢淑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童志锋,《历程与特点:社会转型期下的环境抗争研究》,载《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6期。
王春光:《中国社会政策调整与农民工城市融入》,载《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5期。
叶静怡,周晔馨:《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民工收入》,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10期。
张玉林:《环境抗争的中国经验》,载《学海》,2010年第2期。
赵蔚蔚,刘轶俊:《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统计考察》,载《统计与决策》,2011年第23期。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
Brainard,J.S.,Jones,A.P.,Bateman,I.J.,& Lovett,A.A.2002.Modelling environmental equity:accuss to air quality in Birmingham,England.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34(4),695-716.
Brulle,R.J.,&Pellow,D.N.2006.Environmental justice: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inequalities.Annual Reviwe of Public Health.27:103-124.
Bullard R.D.1983.Solid waste sites and the Houston Black Community.Sociological Inquiry.53(Spring):273-288.
Bullard R.D.1990.Dumping in Dixie: race,class,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Boulder,CO: Westview.
Chaix,B.,Gustafsson,S.,Jerrett,M.,Krestersson,H.,Lithman,T.,Boalt,A.,et al.2006.Children’s exposure to nitrogen dioxide in Sweden:investigating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 an egalitarian country.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60(3):234-241.
Chakraborty J,Armstrong MP.1997.Exploring the use of buffer analysi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impacted areas in environmental equity assessment.Cartogr Geogr Inf Sys.(24):145–157.
Chunbo Ma,Ethan D.Schoolman.2010.Who bears the environmental burden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sources.Ecological Economy.(69):1869-1876.
Daniel R.Faber,Eric J.Krieg.2002.Unequal exposure to ecological hazards: environmental injustice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Vol.110:277-288.
Dolk H,Vrijheid M,Armstrong B,et al.1998.Risk of congenital anomalies near hazardous-waste landfill sites in Europe: the EUROHAZCON study.Lancet.352:423–427.
Ethan D.Schoolman,Chunbo Ma.2012.Migration,class and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Exposure to pollution in China’s Jiangsu Province.Ecological Economics.140-151.
Gary W.Evans,Elyse Kantrowitz.2002.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the potential role of environmental risk exposure.Annual Review Public Health.23:303-31.
Geschwind SA,Stolwijk JAJ,Bracken M,et al.1992.Risk of 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associated with proximity to hazardous waste sites.Am J Epidemiol.135:1197–1206.
Jamie R.Pearce,Kingham,S.2008.Environmental inequalities in New Zealand: a national study of air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Geoforum.39(2):980-993.
Mohai P.,Bryant B.1992.Environmental racism: reviewing the evidence.In: Bryant B,Mohai B,eds.Race and the Incidence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A Time for Discourse.Boulder,CO: Westview Press.p163–176.
Mohai P.,Paula M.Lantz,Morenoff J.,House J.S.,2009.Racial and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residential proximity to polluting industrial facilities.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Vol 99.No.S3:649-56.
Mohai P.,Pellow D.,Roberts J.T.,2009.Environmental Justice.The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34:405-30.
O’Neill M S,Jerrett M,Kawachi L,Levy J L,Cohen A J,Gouveia N,Wilkinson P,Fletcher T,Cifuentes L and Schwartz J.2003.Health,wealth,and air pollution: advancing theory and methods.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111:1861-1870.
Pastor M,Morello-Frosch R,Sadd JL.2005.The air is always cleaner on the other side: race,space,and air toxics exposures in California.J Urban Aff.(27):127–148.
Robin Saha,Paul Mohai.2005.Historical Context and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Siting: Understanding Temporal Patterns in Michigan.Social Problems.52:618-648.
Thomas,B.,Dorling,D.,& Smith,G.D.2010.Inequalities in premature mortality in Britain: observational study from 1921 to 2007.British Medical Journal.
注释:
2013年江门反核、2011年大连PX事件、2009年番禺反建垃圾焚烧发电厂、2005年浙江东阳画水镇农民集体抗议化工企业污染、2007年广西岑溪波塘镇村民抗议造纸公司污染事件等,均涉及污染单位选址与环境风险在人群中不公正分配问题,并发生群体抗争事件。
在西方社会主要表现为环境种族歧视和以收入为基础的阶层空间区隔,换言之,少数族群和低收入人群暴露在环境风险中的比率远超过白人和高收入人群。
据统计,2011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已达1.639亿吨,城市生活垃圾存量达70亿吨以上,截止2012年5月,全国31个省/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地区)垃圾焚烧厂在运行共有122座,除贵州、青海、宁夏、西藏、内蒙古、江西、新疆、甘肃、陕西9省外,其余22个省市均有已运行焚烧厂分布(国家统计局,2012)。
尽管在爱河事件中,虎克公司的有害化学废弃物掩埋在先,社区建成在后,但市政府在明知此地掩埋化学废弃物的情况下,决定将此地改造为低收入家庭和单身家庭的住宅区,这一举措已构成对环境风险的歧视性分配。
这种方法简便易行,在环境公正研究的起步阶段得到了广泛运用。其操作方法是:选择一个事先确定的地理单位(如县、地区代码、人口普查区域),再辨别其中哪些单位隐匿了环境风险而哪些单位对风险作出了处置,确定一组恰当的比较单位(特别是那些不包括危险的单位),然后比较这两组单位中的人口学特征。这种方法的缺陷是,既不考虑研究单位内风险的准确位置,也不考虑风险对邻近单位的接近性。
这种方法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收集数据,并描绘出环境风险的精确位置,列出这些风险位置距附近居民点的距离。这个方法能将特定距离内的所有单位(不仅仅是主要研究单位)的人口学特征与更远距离的单位的人口学特征进行对比,以发现是否存在环境风险不公正分布问题。
这种方法直接检验一个给定地理单位内的人口特征和在这个单位内使用复杂大气扩散模型预测的有害污染物浓度之间的假设关系。
之所以选择北京、重庆和厦门三座城市,是考虑到城市类型、地理位置、综合发展水平、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公众生活消费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导致各城市采取不同的垃圾处理模式,由此带来不同的环境风险。此外,我们计划在后期研究中对比不同城市间人群风险暴露、应对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所以选择这三座城市。
1英里等于1.6093公里。
就目前的垃圾处理技术而言,不管何种垃圾处理方式,或多或少对近距离居民的生活质量都会产生一定影响,例如有毒气体的排放、粉尘沉降、水源污染等,以及由此造成的生理疾病、心理压抑、焦虑、社会污名化等等。
之所以采用主观风险评价法,是因为,一方面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测度污染、解决环境修复等专业技术性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科学视阈中的风险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自反性,主观评价更能反映研究对象对风险的判断,并依据思考行动。
参照卢淑华教授对本溪环境污染与居民区位分布关系的研究。
尽管健康状况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营养供给,医疗保障等,但不能否认居住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基金项目: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211“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公众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及行为研究”(11CSH01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环境公正视野下的城市垃圾处理风险分配研究”(201022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