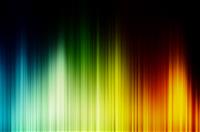
在经济理论中,平等与效率的权衡占据着崇高地位。美国经济学家亚瑟·奥肯(Arthur Okun)著有经典名著《平等与效率:大权衡》(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他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围绕管理这两种价值的冲突而生的。2007年,纽约大学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在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发表毕业演说时总结了12条简短的经济学原理智慧,权衡也在其中。
增进平等需要牺牲经济效率的观念建立在经济学最重要思想之一上:激励(incentives)。企业和个人需要有更高的收入前景才会储蓄、投资、努力工作和创新。如果盈利企业和富裕家庭的税收影响到这一前景,结果就是偷懒和经济增长下降。共产主义国家的平等主义实验往往导致经济灾难,一直是反再分配政策的“呈堂证供”。
但是,最近几年来,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经验都倾向于这一假定的权衡。经济学家提出了新论据证明为何经济表现不仅相容于分配公平,甚至还有求于它。
比如,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穷人家庭被剥夺经济和教育机会,经济增长也受到抑制。另一面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里的公平主义政策显然没有妨碍经济繁荣。
今年早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得出了一个似乎足以颠覆这一旧共识的实证结果。他们发现,更大的不平等性伴随着随后更快的中期增长,不管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家间都是如此。
此外,分配政策并未表现出任何对经济表现的危害。看起来我们可以鱼与熊掌兼得。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考虑到这一结果来自极少出现异端或极端思想的IMF就更加值得惊讶了。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可以说没有揭示过任何普遍真理。与社会生活中的几乎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平等和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偶然的而不是固定的,取决于不平等的更深层次原因和诸多中介因素。因此,关于不平等的有害影响的新共识可能与旧共识一样具有误导性。
比如,考虑工业化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在大部分劳动力受雇于传统农业的穷国,城市工业机会的出现也许能拉低不平等,至少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是如此。随着农民走向城市、获得更高收入,收入差距也被打开。但同一过程产生了经济增长;所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一经历。
比如,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快速经济增长伴随着不平等程度的显著增加。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大约一半来自城乡收入差距,而这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或者,考虑对富人和中产阶级征税以提高穷人家庭收入的转移支付政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和玻利维亚)以财政审慎的方式采取了这类政策,以确保政府赤字不会导致债务高企和宏观经济动荡。
另一方面,查韦斯及其后继者马杜罗在委内瑞拉所采取的激进再分配转移支付由暂时性石油收入作为资金源,转移支付和公关经济稳定性都受到了威胁。尽管委内瑞拉(目前的)不平等程度被抑制,但其经济增长前景也被严重削弱。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地区。社会政策的改善和教育投资的增加都是重要因素。但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薪酬差距——经济学家称之为“技能溢价”——的下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经济增长来说,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答案取决于技能溢价下降的原因。
如果薪酬差异是因为高技能工人相对供给增加而收窄,那么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拉丁美洲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不会干扰增长加速(甚至可能是增长加速的早期信号)。但如果基础原因是高技能工人需求下降,那么薪酬差异缩小意味着作为未来增长基石的现代技能密集型产业扩张不足。
在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原因仍在争论中。自动化和其他技术变革、全球化、工会式微、最低工资的侵蚀、金融化和企业内部可接受薪酬差距范式的变化都起到了作用,只不过在美国的权重与在欧洲不同。
所有这些驱动因素对增长都有不同的效应。技术进步显然有利于促进增长,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崛起可能具有消极效应——通过金融危机和债务积累突显。
经济学家不再把平等-效率权衡看做铁律,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不应该颠倒错误,认为更大的不平等和更好的经济表现永远会同时出现。毕竟,经济学只有一个普遍真理:视情况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