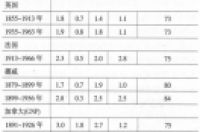——以雾霾治理政策制定为例的一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格局,公民结社权利及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不断扩大,在各个领域中与政府的互动形态也发生了急剧、深刻的变化。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公众以及民间环保组织,针对一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和政府已经或即将出台的政策中存在的环境侵害或隐含的环境风险,公开向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进行呼吁、申诉、抗议,以此参与到相关环境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本文以我国雾霾治理政策的制定过程为例,对公众与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的特征和影响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雾霾问题:一种空气,两种声音
最近几年来,全国多次出现大范围雾霾过程。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13年中国气候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中东部地区平均雾日数16天,较常年偏少8天,为1961年以来最少;平均霾日数36天,较常年偏多27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1]。
严格来说,“雾霾”并不是一个科学概念。目前国内科学界更常采用的是“霾”或“灰霾”的说法,而“雾霾”主要指由雾和霾共同造成的水平能见度降低的空气普遍混浊现象,被公众统称为“雾霾天气”,是空气污染严重的表现之一。由此,雾霾治理仍然属于大气污染防治范畴。
1973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暂定了13类有害物质的排放标准,标志着大气污染防治被提上中国政府日程。40多年来,中国政府主要通过加强法制建设与科技攻关并进的方式开展大气污染防治[2]。在法制建设方面,除了《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1973年)以外,中央政府及环保部门还陆续颁布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1982年)、《关于防治煤烟污染技术政策的规定》(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年)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为我国空气污染防治提供了法制保障,初步形成了煤烟型大气污染管理的法律体系。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系统、国务院各部门系统和环境保护管理系统四大环境科学研究体系也逐渐形成[3]。环境科研中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一些重大课题被列入国家科学发展“七五”、“八五”、“九五”、“十五”计划之中。这些环境科研的开展不仅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了切实的技术保障,而且推动了相应的政策制定、法规完善和标准出台。
在制度保障及技术支撑下,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近十年以来,全国环境空气质量大幅改善,并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根据环保部网站《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2年,在每年中国地级行政区划单位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等级监测中,空气质量达到或优于二级(达标)的比例从最低的38.6%(2004年)上升到的91.4%(2012年);三级空气质量比例从最高的41.2%(2004年)下降到7.1%(2012年);劣三级(超标)空气质量比例从最高的26.8%(2003年)下降到1.2%(2011年)。这些数据表明,从整体上看,我国空气质量级别变化趋势呈现良性发展。
然而,随着雾霾天气的频繁出现,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渐入佳境”的趋势纷纷表示质疑。2010年11月,美国驻华使馆通过其Twitter账号“BeijingAir”发布了北京市空气质量指数超过500的结果,并配文“Crazy bad”(糟糕透顶),一些中国网民戏称这一结果为“爆表”。但由于当时Twitter的中国用户不多,其发布的信息影响还有限。到2011年10月22日晚,中国地产企业家潘石屹在其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内容为“妈呀!有毒害!”的微博,配图为数据来源于美国使馆的北京空气质量定时播报软件截图。截图显示:当日北京PM2.5细颗粒物浓度为408,空气质量指数为439,评级为“有毒害”。彼时微博已有广泛使用,潘石屹发布的信息当日就获得了数千人的转发,由此PM2.5这个词在网上迅速流传。后来传统媒体跟进,形成了线上、线下同步传播的局面,通过媒体传播,PM2.5以及雾霾迅速成为公众热议的社会议题。
从内容分析上看,公众关注点主要有五类:一是“北京空气质量数据差距争议”;二是关于雾霾天气的报道;三是关于雾霾危害的报道;四是政府发布治理雾霾的信息;五是普及雾霾防护知识。其中“北京空气质量数据差距争议”引起网友的激烈讨论,除了美国驻华使馆公布的北京空气质量“爆表”数据外,大部分市民在感官上也觉得空气质量很糟糕,然而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空气质量报告却显示北京空气仅是轻度污染。政府监测数据与公众感知的空气质量相悖,使得环保部门的大气污染治理成效受到了公众的质疑。
综上所述,在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新阶段中出现了“同一种空气,两种声音”的现象。这种现象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方面,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北京环保局对北京空气质量监测存在的差距,引发了社会各方的解读,建构了雾霾问题。根据政府监测数据,北京的空气质量在近十年里逐渐转好,尤其是2011年和2012年,然而雾霾问题也就是在这两年里“爆发”。也就是说,雾霾问题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并未成为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受到公众的关注,直到最近三、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讨论,大众媒体的报道,科学家、政府官员的“发声”、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雾霾问题才真正成为了一个紧迫的环境问题。作为环境议题的雾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共识、共建的过程和结果。另一方面,空气质量的客观监测与主观感受之间不一致,表明了政府与公众之间在空气质量判定上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这里除了反映了政府监测指标、监测方式与治理重点滞后于环境问题的演变,同时也凸显了公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更高环境质量的强烈需求,而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大众传媒的发展则直接加速了公众直接表达和参与治理的进程。
二、雾霾治理:推力与拉力的结合
就雾霾治理而言,表面上看,公众参与直接影响了雾霾治理的政策进程。但是,深入分析表明,雾霾治理政策的制定是公众参与和政府主导双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推力与拉力的结合。
1.公众参与对于雾霾议题演进的推动力
首先,公众参与促进雾霾议题从科学议题转向公众议题。如同其他环境问题一样,雾霾问题也经历了科学研究、公众关注和政策反应的社会过程,相应的也就存在学术议题、公众议题和政策议题三种型态。雾霾进入科学界视野,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学术议题,大概始于20世纪80年代,彼时中国已陆续开展了富有开拓性的大气气溶胶研究。2003-2007年,政府开始设计建设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辽宁中部城市群大气成分观测站网[4]。但一直以来,雾霾作为一个科学议题,很少为公众所了解。在2011年PM2.5数值引发争议之后,雾霾议题迅速地从科学议题转化成公众议题,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根据百度搜索引擎提供的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百度用户对“PM2.5”一词的每周搜索频率可以了解到,在2011年10月之前,PM2.5的平均每周搜索次数非常少(接近于0);但在同年10月的“PM2.5风波”之后,相关搜索次数迅速增长,在2013年秋出现明显峰值。
其次,雾霾议题成为公众议题之后强化了公众对于雾霾现象的认知和了解。根据我们2013年3月在北京市进行的一项电话调查2数据显示,在在对雾霾的关注和认知方面,有76.6%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地区雾霾现象严重(其中认为很严重的人占54.6%),只有10.4%的受访者认为不严重或不太严重,其余13.0%的受访者表示说不上严不严重;在公众应对雾霾的行为倾向方面,有63.0%的受访者赞成在雾霾治理方面公众个人也应该承担责任(其中明确表示很赞成的比例为27.6%),表示不赞成和不太赞成的受访者占23.7%,其余13.3%的受访者表示说不上赞不赞成;在公众对雾霾治理政策的期待和支持方面,有29.9%的受访者对政府在雾霾监测预报和防治方面的信息公开工作给予了积极评价,但其中认为做得很好的受访者只有4.6%,认为做得很不好和不太好的受访者占35.1%,其余35.0%的受访者表示说不上好不好。整体而言,大多数公众对雾霾严重性的判断都有接近一致的意见,意识到了自己应当承担相关责任,同时对政府的政策应对满意度不高。
再次,公众对雾霾问题的关注逐步有了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向。这种政策指向表现两个方面:一是向政府举报,期待政府解决。2014年上半年,环保部受理的群众举报案件中涉及大气污染问题的占到受理案件总数的80.2%,较之2013年上半年的71.8%有大幅上升3;二是采取各种探索性的自力救济措施,为公共政策做出示范。例如,一些普通市民、企业自发给交警、清洁工、工地农民工等暴露于雾霾环境中的群体送口罩;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招募志愿者进行室内空气PM2.5检测,开展“我为祖国测空气”行动[5];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发布新增PM2.5浓度值指标的《2012年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AQTI)报告》;而绿行齐鲁、天津绿领、磐石能源与环境研究所、中国空气观察河北志愿者小组、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自然大学基金五家环保组织则从2013年8月份起,采用数据分析、实地走访、信息公开申请等方式,对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的12个城市控煤情况进行了调研,共同发起了“好空气保卫侠”行动,形成了强大的“公众监管”民间行动网络[6]。另外,石家庄市民李贵欣以石家庄PM2.5年均值超标3.4倍,侵犯公民生命权与健康权为由,于2014年2月20日起诉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局并要求赔偿,该事件成为全国首例公民因空气污染向政府部门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环境诉讼案[7]。
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舆论和公众参与的压力,促使政府反省空气质量监测指标和监测方式,开始推出更加积极的雾霾治理政策。2011年11月16日至12月5日,环保部第二次就《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向公众征求意见。2012年2月,环保部正式发布新增PM2.5空气质量检测指标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提前实施,北京、广州、上海等多个地区陆续开始公开发布PM2.5的监测数据。从2013年1月1日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门户网站开始统一发布74个城市496个监测点的PM2.5实时监测数据。
2.政府改进环境治理对于雾霾治理政策出台的拉动力
客观地说,大气污染防治一直是中国政府环保工作的重点之一。中国政府在1987年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在1995年对其作了修改,并在2000年再次做出修订,不断完善其内容。2000年修订后的法律条文从1987年的四十一条增加到六十六条,包括了总则、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防治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防治机动车船排放污染和防治废气、尘和恶臭污染,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内容。
从大气污染防治法律的执行效果看,虽然由于能源消耗和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工业SO2排放量总体仍然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是在区域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较大差异,工业SO2的整体排放强度持续降低[8]。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就雾霾问题严重的北京地区而言,从2000年到2007年,大气环境中主要污染物SO2、NO2、PM10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其中SO2下降最明显。如果不考虑新的监测指标,北京的大气环境质量实际上呈现出明显的好转趋势[9]。
就雾霾防治而言,北京、上海和广州等特大城市在大型赛事的推动下,也已经较早开展PM2.5的监测和治理工作。2007年,为确保北京奥运会期间空气质量良好,北京市周边省区市通力合作,针对空气质量呈现大范围区域相互影响的特点,共同制定了《第29届奥运会北京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并于同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这实际上已经是具有区域联动性质的大气污染治理行动。2008年开始,中国环保部建设了3个大气背景站,在广东、江苏两省和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南京6个大城市进行“灰霾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试点方案”建设,建成了16个灰霾监测站[4]。2010年11月,环保部已经开始就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向全社会第一次征求意见,并首次给出了PM2.5参考限值。2011年6月,《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办法(试行)》试点监测工作在全国26个城市低调开展,试点城市要求按照监测能力尽可能监测,其中包含PM2.5;同年9月,环保部发布了《环境空气PM10和PM2.5的测定重量法》,对环境空气中PM2.5的测量方法进行了正式规定。正如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在回应雾霾问题时所说:“从PM10到PM2.5,原来政府就想干,现在公众想知道,只是公众参与的特点不是按照你的时间表进行,所以你得顺势而为”[10]。
在雾霾问题从科学议题转成公众议题之后,政府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较快地做出了回应,加快了政策设计和发布实施的进程。例如,2012年5月,环保部印发《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施方案》;2012年9月,国务院批复《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应急方案(试行)》;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十条”);2013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试行)》。截至2014年1月7日,环保部与全国31个省(区、市)都签署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2014年1月22日,北京市人大还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标志着雾霾治理已有专项地方性法律保障。
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公众参与的推力之所以能够形成、显现并得以发挥作用,也受到了中国政府改进环境治理方式、鼓励公众参与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安排日趋完善,特别是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强制性规定,使得公众获得和传播环境信息具有了合法性,由此保障了公众议题的形成。例如,《环境影响评价法》从2003年9月1日施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从2006年3月18日施行,《环境信访办法》从2006年7月1日施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也从2008年5月1日就开始施行。民间组织“自然之友”采取向北京市环保局申请公开北京市雾霾空气形成的原因、污染源比例,通过媒体平台向环保部递交雾霾治理建议书等行动[11],可以说都是受益于已有的制度资源和社会空间。
综上所述,在中国雾霾治理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互动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政府自身一直在积极推进环境治理的改善,探索新的环境政策;另一方面,公众的积极参与也对政府决策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加快了政策制定和颁布实施的进程。如果采用时间轴的记录方式,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雾霾治理政策发展过程中公众和政府互动的脉络。
三、雾霾治理政策的应急性与风险
上文分析表明,在雾霾治理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公众参与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一是改变了政策制定过程的特性,使得政策制定从相对封闭的政府内部过程转变为相对开放的社会参与过程;二是增加了政策制定的主体,使得政策制定从专家、官员的互动发展为专家、官员、民间组织和公众等多主体之间的互动;三是加快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进程,缩短了政策出台周期,提高了政策制定效率。政府原计划在2016年全面实施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明显提前执行就是一个好的例证。
但是,在公众参与影响下加快出台的雾霾治理政策具有应急性特征,政策的专业技术支持还不充分,对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困难考虑还有不足,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着一些显在或者潜在的风险:
一是现行政策对雾霾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预计还不够充分。就国外的经验来看,雾霾治理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洛杉矶雾霾在1943年大规模爆发时,该市市长承诺在四个月内对雾霾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治[12],但事实上,数十年的时间过去后,洛杉矶的空气质量才有实质性的好转。我国现有政策偏向于取得短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确实有可能加快雾霾治理的进程,甚至在短期内能够取得一定效果,但是这种效果的长期可持续性值得忧虑。毕竟,雾霾治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二是区域联防联治的落实存在现实困难。大气污染在相邻地域之间的联动影响方面表现显著,在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等区域,部分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受外来源的贡献率达到16%至26%4,因此,要取得较好的雾霾治理效果,区域内各地区的相互协调、联防联治很关键。但是如何协调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打破各地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无论是政策设计还是政策执行,都将面临巨大挑战。中国长期存在的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刺激了竞争性的经济增长和利益冲突,妨碍环境保护共识和一致行动的达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痼疾[13]。
三是环境保护理念转变中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难度很大。如果不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无论采取如何严厉的污染治理措施,都不太可能遏制住经济总量扩张和大量消费带来的污染总量的增加。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机会和空间明显受到压缩,面临着更大的产业结构升级困难,西方的成功经验难以简单复制。另外,中国城镇化进程仍在快速推进。2013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达到53.73%。《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5。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城市规模仍将持续扩大,城镇人口仍将大幅增加。快速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影响是多方面的[14],例如,施工扬尘、建材生产、城镇化生活消费习惯等都意味着节能减排的任务相当艰巨。在此基础上,雾霾治理无疑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四是开展广泛的社会动员任重道远。雾霾防治实际上需要“群防群治”,治理雾霾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和公民的责任。从目前情况看,普通公众对雾霾问题的抱怨很多,对政府治理不力的批评很多,对雾霾治理的预期很高,但若治理雾霾真的涉及自身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调整时,公众又有很强的抗拒心理。在我们针对北京公众的电话调查中,明确表示了解《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受访者仅占12.0%(其中明确表示很了解的受访者只占1.0%),而近八成(77.0%)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这一针对雾霾防治的新政策,此外还有11.0%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说不上了不了解。在被问及是否赞成政府为了解决雾霾问题而增加税收或者提高消费品价格时,仅有20.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其中表示很赞成的受访者占10.7%),而明确表示不赞成和不太赞成的受访者高达60.7%,此外还有18.8%的受访者表示说不上赞不赞成。由此可见,公众对于政府政策的了解并不充分,通过增加个人经济负担来促进雾霾治理的意愿也不足。考虑到目前中国在整体上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广大公众对于继续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还很迫切,自觉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心理准备、知识准备和物质准备都还不足,要实现有效的群防群治确实面临困难。
四、结论与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就雾霾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看,公众参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环境政策制定的重要力量,中国环境政策的制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在共同应对环境问题时,政府已经更加明确地注意到了对公众要求的回应,公众参与和政府决策之间正在形成有效的互动关系。
但是,在现阶段的公众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互动双方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公众自身对于环境问题的专业知识了解比较有限,容易忽视环境问题本身及其背后长期累积的复杂因素,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表现出了简单化、情绪化的倾向,过于急躁,理性思考不足,而且过多地指责政府的同时又依赖政府,自我行动的意愿与能力还有很大不足,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公众情绪的宣泄会制造出强大的舆论场,给政府施加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政府对于原有决策模式和沟通渠道还存在着路径依赖,因应公众参与扩大的新形势还很不足。特别是,政府还不能熟练地使用与公众沟通的新方法、新技巧,往往对公众的诉求回应迟缓、方式不当、内容不足。而当公众参与形成强大舆论压力时,一些官员又容易在政治正确和保持稳定的压力下仓促出台政策回应或者做出简单化的承诺。需要指出的是,公众与政府的局限性,既有各自自身的原因,也有体制性观念性的原因,而且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环境政策发展的特定阶段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客观必然性,迈向成熟的公众与政府互动需要一定的实践和时间。
由于在实践中政府与公众互动还存在着局限性,由此加剧了环境政策制定过程的复杂性,并容易导致出台设计不完备、实施有风险的环境政策。如前所述,当前雾霾治理政策虽然已经渐成体系,但是其对雾霾治理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着有效社会动员、转变产业结构和实现区域联防联治等风险。因此,未来应该注重更加合理的体制机制建设,更加有效地整合公众和政府两个方面的力量,使得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更加常规化、制度化、理性化,以便更加有效率地发挥公众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合力,促进嵌入社会经济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具有长期效用的复合型环境政策,从而促进更好的环境治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参考文献:
[1]徐文彬,庄白羽.中国气象局发布2013年《中国气候公报》[EB/OL].[2015-01-16].http://www.cma.gov.cn/2011xwzx/2011xqxxw/2011xqxyw/201401/t20140114_236245.html.
[2]郝吉明.穿越风雨 任重道远:大气污染防治40年回顾与展望[J].环境保护,2013[14]:28-31.
[3]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30年编委会.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30年[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35.
[4]吴兑.近十年中国灰霾天气研究综述[J].环境科学学报,2012(2):257-269.
[5]焦玉洁.“我为祖国测空气”——访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人冯永锋[J].世界环境,2012(1):29.
[6]朱艳.环保组织联手发布《华北煤问题首轮调研报告》治理雾霾遭遇“数字游戏”[J],环境与生活,2014(7):105.
[7]张淑宁.告政府是我有一个善良的愿望[N].京华时报,2014-02-27(第023版).
[8]李名升,于洋,李铭煊,等.中国工业SO2排放量动态变化分析[J].生态环境学报,2010(4):957-961.
[9]韩昀峰,马明涛,宋凌艳.北京市近年来大气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分析[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9(6):4-6.
[10]汪韬.那些关于北京空气的“大实话”:对话北京环保局前副局长杜少中[N].南方周末,2012-07-19.
[11]汪韬.南方周末联合六家NGO的七大建议[N].南方周末,2012-03-19.
[12]奇普·雅各布斯,威廉?凯莉.洛杉矶雾霾启示录[M].曹军骥,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4.
[13]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2(9):82-99.
[14]洪大用.绿色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研究[J].环境保护,2014(7):19-23.hansi-font-family:Calibri"">):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