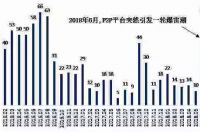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
在中国学术界,费孝通是一位有着自己鲜明学术特色的学者。费孝通治学的鲜明特色是“学以致用”。早在从事社会学初期,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为研究而研究”的倾向,他说:“‘学术尊严’我是不从的。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是功能),亦可以做食粮的。”在后来的多次著述中,他都指出学者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这种做法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是要不得的,因为从方法论上讲,“为研究而研究”是一种受兴趣驱动的活动,为研究而研究的人,一旦兴趣不同,就可以为不研究而不研究了。
20世纪80年代,他又以类似的语言批评了那种流行于西方人类学界的以人类学来消磨时间或表现才能的研究取向。在他看来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用得到的知识来推动中国的进步”,否则它无异于游戏和玩麻将。“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内在动力。
1983年,在江苏省组织小城镇问题研究时,他对课题组的同志说:“一定要坚持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在他看来,学者就是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
从实求知
1979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费孝通领衔在中国恢复社会学。社会学恢复初期,费孝通就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路径:“我们建设社会学的方针,正如乔木(指胡乔木,笔者注)同志所讲的,有三条: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我们的理论基础和方向;二是结合中国实际,这就是说要有我们自己的内容;三是为现代化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社会学的宗旨。”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领头人,费孝通把为现代化服务作为社会学建设的宗旨。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社会学在过去的36年有了巨大的发展,与时俱进,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研究,发展出若干新的学科分支,拓展出若干研究领域,孕育出若干重大理论和思想,培养出若干在发展领域具有很大影响的学者。实践证明,社会学只有贴近中国的社会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才有前途。
20世纪末,回顾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路程,费孝通认为自己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用实证方法、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中吸取研究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取得理解,进而按照自己的认识想方设法去提高各民族人民对于自己发展道路的理解。这包括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思想。他在2002年写道:“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的出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费孝通找到了探索这条出路的方法,那就是实地调研。
博采众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有幸在费孝通指导下攻读社会学。那时,在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小圈子里有一个惯例就是,费孝通每写一篇文章都要拿到北京大学,在有关研究人员和学生中传阅、学习、研讨,大家可以提出意见。有时,费孝通不顾年迈,亲自到北大与研究人员和学生一起座谈、讨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写的《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一文,是对他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同学利奇(Sir Edmund Leach)博士写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 1982)的回应。在《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中,针对不同环境下文化的差异,针对当时世界文化在现实和学术领域的冲突,费孝通提出,“我们不仅能容忍而且能够相互欣赏”,“我们不妨各美其美,还可以美人之美”。我们应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文化。这是他给我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思想之一。这个思想是费孝通从人类学角度考虑人类不同文化的和平相处、文化之间的平等问题。
学而思、思而学
1992年春,我随费孝通到山东曲阜,访问了三孔——孔林、孔庙和孔府。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在孔庙坐了很久。我看得出,他当时是思绪万千。回到北京后,他在北京大学社会学1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谈了访问孔林时的思考和感想,后来形成了著名的《孔林片思》。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认识到,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经注意到战争造成了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地球上是否能够还能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球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提出来研究,看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觉醒。这时,费孝通已经从对文化的思考进入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思考,从社会发展这个更广泛的视角透视中国乃至全球发展,考虑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
紧紧追赶时代的步伐
作为一个成功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费孝通从不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考虑问题,而是紧紧追赶时代步伐,与时俱进,不断探索。
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人民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在这样的大社会背景下,费孝通在《孔林片思》中把他的文化思想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小康之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而涉及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的问题。他把这种相处称为人的心态关系。他说:“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共荣。”
1993年7月他在印度新德里参加“英迪拉· 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他发表了《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的演讲,将其以往文化平等、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思想升华,形成美好社会的思想:“20世纪最后10多年所发生的这些新事物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理解,其中是否得出一种看法,人类大小各种群体是可以各自保持其价值体系而和其他群体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只要大家不采取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而容忍不同价值信念的并存不悖。”政治平等、经济公平、社会公平、文化公平和环境公平等思想在这里得到更进一步升华,成为他的美好社会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