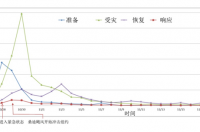一、问题的提出:从“一般的生产”到“纯粹的规范”
众所周知,马克思将“生产劳动”视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生产活动在人类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体现在: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生产;每一个社会都需要生产;每一个人都需要生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个人从事着不同的生产。那么,面对上述超级复杂的生产活动,理论上如何抽象?马克思认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这可以称为“生产一般”①。这个“生产一般”是一个可以包容很多差别的抽象,“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抽象,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这个抽象却不能取代现实的生产,因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②。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两种“生产”的形式:一种是作为现实的人在现实的社会中进行的具体的生产活动,而另外一种是经过理论抽象的“生产一般”,是一个包含了多种规定性与可能性的“简单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通过提炼出“生产一般”的概念,首先将“商品”规定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然后区分了“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再集中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并为之构造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态③。
但是,正如后来很多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对于社会生活的另一个维度,即“规范”活动的结构与特征,却没有正面论及,意大利学者科莱蒂就直言不讳地声称,马克思缺乏自己的政治哲学④。著名法哲学家凯尔森则认为,马克思对社会现实所做的经济解释,具有一种反“规范”的趋势,具体表现为:“硬是把那些在伦理学上及法理学上认为是道德规范或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义务、责任与权利的人的关系,归结为政治权力或者经济权力的事实关系;把正当及不正当、公平及不公平等价值判断认为是可用个人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观察得到的事实的命题,而不是把它们解释为符合或不符合一个事先假定有效的规范的判断”⑤。因此,企图在马克思的经济解释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法律理论的尝试是必然失败的。由此可见,凯尔森是将“生产”与“规范”视为两个没有交集的领域。作为纯粹法理论的首创者,凯尔森是以“纯粹规范”的提出与论证而著称于世的。正是从这个意义说,考察凯尔森对“规范”的内涵及其特征的规定,进而考察他基于此对马克思的批评视角,对于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应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二、在“事实”与“道德”之间:纯粹规范的自主性论证
凯尔森“纯粹法理论”之所谓的“纯粹”,首先在于其认知对象的纯粹性。在他看来。19世纪、20世纪所形成的法律科学,与他所谓的纯粹法理论相距甚远,因为前者“全然不加批判地同心理学、生理学或伦理学、神学混为一谈”⑥。而这种渗透造成的后果恰恰是令法律科学迷失自我。因此,只有“循名责实”,才能将法律科学从其他异质性因素中解放出来,真正确立纯粹法理论的对象的自主性。
在凯尔森看来,作为对象的法律行为,既非自然事实,亦非道德价值,而是某种“社会行为”。虽然任何行为都是具体的行为,“属存于时空且可为感官所感到之事实”,因此要受自然因果律的支配,但是,作为纯粹法理论之认知对象的社会行为,却与此自然性无关,而是具有超出这种具体行为的“法律意义”:“此意义并非可自行为之外在物质事实而耳闻目睹,亦不能测度其黑白、软硬、轻重等所谓自然属性或机能”⑦。这种意义就是来自于人为创制而成的规范,“此规范之内容涉及上述事实,并对其赋予法律意义;则此行为便可依规范而解释”⑧。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的难题正在于确立法律意义上的规范活动的自主性。
在凯尔森看来,从理论的表征形式来看,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因果律是在“实然”的层次展开的,那么,法律科学则是在“应然”的层次展开的。“一言以蔽之,法律无他,唯应然而已。纯粹法理论即以应然描述法律”⑨。如果说自然规律的含义是“若有甲,则必有乙”,那么纯粹法理论所表达的则是“若有甲,则应有乙”。如此说来,规范层次的“归属律”与事实层次的“因果律”便是不同层次的逻辑,两者之间绝不会存在因果律意义的逻辑矛盾。若将因果律推进到规范层次,以因果律来判定规范层次的命题,显然是缘木求鱼,错失了规范层次的特殊逻辑。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行为的法律活动也不同于道德行为,因此,对规范的自主性论证,还需要进一步排除“法律乃道德之一部”的成见。在凯尔森看来,这种成见将一切法律视为合乎道德的,而认为法律不过是道德的一个分支,在历史上,这就是自然法学说所持的观点:自然法学说要么预设价值内在于事实而且具有绝对性,要么预设上帝之意志内在于自然。但“这不过是想将道德所信奉的绝对价值强加于法律而已”⑩。原因在于,正义之绝对效力要求我们只能想象一个异于且高于实在法的秩序,但是这本身就超越了一切的经验,非人类认知所能及。
如果说在早期的自然法学说中,这种价值与事实的统一性表现为对自然所做的“泛神论”解释,即认为“自然乃是某种超人的人格存在,是人必须服从之权威”(11),而当社会进化到较高的阶段,这种泛神论便为“一神教”代替:“自然便被想象为上帝之造物以及上帝全能与公正意志之象征”(12);那么,19世纪兴起的社会进化论与历史哲学,尽管从根本上反对自然法学说,“但却运用了相同的方法因而犯了与其试图取代之自然法学说相同的错误——从‘实然’推出‘应然’”(13)。具体来说,19世纪社会学代表人物孔德与斯宾塞便是假设人类的社会生活如自然现象一样受某种因果律的控制,后来他们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假设社会也存在社会进化规律,两人都主张社会进化的基本规律显示了人类从低级到高级最终达到最高形态的过程。在凯尔森看来,“对社会进化的过程性假设,即文明从低到高之发展,意味着社会价值内在于社会事实——这正是自然法学说之典型假设”。其实质是混淆了“对社会实际生活之描述与解释”和“对社会事实与政治价值判断之规范性宣言”(14)。
作为历史哲学“研究大家”的黑格尔,将“世界精神”作为统治世界与历史的力量,将世界历史视为世界精神的理性化过程。在凯尔森看来,“黑格尔所谓的历史哲学不过是世界精神之神话;其并非哲学,而系历史神学”。在此神学之下,上帝作为一种绝对价值,不仅超越而且内在于世界。于是,“世界历史便是体现绝对逻辑与伦理价值之理性的实现。若此价值为真,则一切历史事件就只能被认为是世界精神之行动,因而只能被认为是合理的与善的”(15)。这样的后果便导致现实中根本无法区分善恶。
在凯尔森看来,黑格尔不仅混淆了思维与存在,也混淆了事实与价值。这种观点在自然法中曾经导致了错置“实然”与“应然”的错误,也是黑格尔辩证法致命错误的根源。与此相对,凯尔森坚持认为,“现象只能、也必须通过符合旧逻辑的无矛盾陈述来描述”(16)。他自己的纯粹法理论乃是“描述法律之本来面目,而不因其公正与否妄加褒贬;其所研究者乃是现实与可能之法,而非正确之法”(17)。只有从这个立场出发,作为纯粹法理论之研究对象的规范的自主性才得以保证,纯粹法理论才得以自命为真正的法律科学。
《纯粹法理论》的英译者鲍尔森根据法与道德、事实之间的关联构造了一个“矩阵”:自然法学说认为法与道德不可分,但与事实可分;实证主义理论认为法与道德可分,但法与事实不可分;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则是认为法与道德、事实皆可分(18)。鲍尔森认为,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之间虽然各自能够自圆其说,但其共同之处都是将法律与道德或事实混为一谈,两者相互纠结,使得法学陷入了类似康德所揭示的二律背反之中。而凯尔森独辟蹊径,“藉证明两传统理论并未穷尽此领域中之一切可能,使其标新立异之纯粹法理论找到了立足之地”(19)。从这个意义上说,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对规范之纯粹性的论证所选择的乃是一条康德或新康德主义的“中间道路”。
基于纯粹规范的自主性,凯尔森从两个方面批评马克思,一方面认为马克思混淆了“法律现实”与“意识形态”,将法律、政治、道德等视为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忽略了法律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则指认马克思混淆了“意识形态”与“现实”,误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视为“现实的科学”,实则是一种“坏的意识形态”。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凯尔森认为,“立法者所创造的和法院所援用的法律,不是思想家的产品,不是哲学家意识形态的、思辨的学说,作为人类在空间和时间中所作出的行为的特殊意义,它是一个社会的现实”(20)。即规范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法律关系是一种现实关系,国家与法律作为实际存在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是意识形态。只有一种特殊的法律理论,才是意识形态;而法律本身,亦即理论的对象,则不是意识形态。因此,“认为法律是意识形态的见解,实际上是混淆了法律与法律理论”(21)。
如果基于规范的现实性与自主性来考察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的话,凯尔森认为,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唯心主义,主张“人类思想中对自然现实的观念只是这个现实的反映而不是相反地由现实反映观念”时,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当马克思将这个公式应用于法律等规范的具体行为时,“马克思毫无疑问地错了”(22)。因为作为一种观念,法律不像一面镜子反映独立于镜子之外的实际事物那样去“反映”一个与之相应的现实,而是通过创制一种行为的规范来调整人类的具体行为。与反映论的镜子式比喻相比较,“法律规范必须首先制定,然后才有与它相应的实际行为的判定,就是说,才有与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或允许的行为相似的实际行为”(23)。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凯尔森认为,马克思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乃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但“马克思恩格斯却把它说成是一种科学,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他们因为已经把社会主义从‘空想提升到科学’而骄傲,因此称他们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主义’”(24)。如果说确立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特殊功能,那么,在凯尔森看来,人类社会行为中根据一个价值判断,“确立一个本身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的目的,却不是科学的功能”(25)。如果将这个价值判断先行投入到现实中,然后从所谓的现实中再引申并论证这种价值的正当性,这显然不能称为“科学”。凯尔森据此认为,当马克思把他的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提出来的时候,恰恰“制造了一个与他们所指责为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相同的虚假的意识形态”(26)。如果说资产阶级以宗教为手段,授予资产阶级国家与法律以神圣的权威,事实上却并没有这些权威,那么,马克思在批判意识形态时虽然摧毁了宗教的权威,却借助了“科学”的权威:“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冒充为与道德标准无关的客观科学,正是为了掩盖作为它的基础的价值判断的非常主观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展的社会科学,就其本性而言是一个意识形态”(27)。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批评,凯尔森还试图进一步揭示马克思双重混淆的理论根由。他认为,马克思在处理“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时,区分了“意识形态的意识”与“科学的意识”,因此相应地存在着两层“现实”:一个是外部的、可见的,然而是虚假的现实,即“意识形态的现实”;一个是内部的、看不见的,然而是“真正的、实在的现实”。如果“意识形态”的特有作用是歪曲“现实”,“像一面不平的镜子那样,使现实的反映变了样”(28),那么,“科学”则是要暴露这个“意识形态”和它所歪曲反映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但问题是如何区分两种不同的“现实”呢?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之所以“社会现实”中产生了“意识形态”这种歪曲了现实的意识,是由于“社会现实”本身是歪曲了的。那么,“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就变为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而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的目的就在于完全变革这个现实,在于社会革命”(29)。但这样一来,便在“革命”的名义下将“科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混淆在一起了。如果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这种混淆是荒谬的因而是不允许的,但是,在凯尔森看来,“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科学,它的唯一的独占的目的不在于思考和叙述社会现实的实际情况而不加评价,恰恰相反,它是要依照科学社会主义事先假定的而又被欺骗性地投射入社会现实之中的价值来衡量社会现实,并且明白地承认要使社会现实符合这个事先假定的价值”(30)。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对矛盾的处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逻辑规律,而是一种特殊的逻辑,凯尔森认为这正是与黑格尔一脉相承的“辩证逻辑”。
这种“辩证逻辑”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取消了“(不)矛盾律”。因为按照矛盾律,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不可能同时为真。但如上所述,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恰恰承认矛盾不仅不是思想的一个缺点,而且还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凯尔森认为,黑格尔之所以敢于作出如此断言,是因为“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中,思维与存在是被认为同一的,作为这个同一化的一个结果,认为逻辑上的矛盾是现实中所固有的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31)。虽然凯尔森也承认,马克思并没有如黑格尔那样将“思维”与“存在”等同起来,但他还是认为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运用造成了类似黑格尔的后果。因为按照这种逻辑,马克思所主张的从现实中牵引出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正义,便像自然法学说所主张的那样,只是将从原先投射到自然中的东西再度演绎出来而已:“马克思硬说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来的社会真理,也只是他自己的、早已投射到社会现实中去的社会主义思想”。究其根源,乃是由于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将“社会现实”与“意识”的双重含义缠绕在一起,“好像魔术家的帽子一样,有双层夹底,你可以从中用手法得到任何你所需要的东西”(32)。
更重要的是,当马克思将社会中对抗的力量或者利害的冲突归结为“辩证逻辑”的时候,便导致了一系列“矛盾”的后果:“这个逻辑允许他们说,国家按其本性而言是一个维持剥削的工具,同时又说,国家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是废除剥削的特殊工具;说无产阶级既可以实行专政,同时又说它要实行民主;说共产主义是个人自由的实现,同时又是一个集体权威的组织,主张社会主义理论是超道德的科学,同时又以科学的名义,宣布自由与平等这个真正的正义;断言不可能有客观的科学这样的东西存在,同时又自夸已经把社会主义从空想的希望提升成为客观的科学”(33)。
综上所述,凯尔森批评了马克思混淆“意识形态”与“现实”的两个表现,进而剖析了这种混淆的理论根源,即对于“辩证逻辑”的运用。在凯尔森看来,这种“辩证逻辑”的解释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这种哲学忽略了现实与价值之间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不可回避的二元论,而仅仅是基于主观价值判断的一个政治假设,说成是受客观规律决定的进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并且认为它必然会从低级的文化发展到高级的文化”(34)。
四、在“特殊对象”与“特殊逻辑”之间:对凯尔森批评的回应
综上可见,凯尔森立足于其纯粹规范的独立性,对马克思的批评集中在以下两点:(1)马克思忽略了“法律规范”的现实性,而将其视为“意识形态”,错失了法律科学的“特殊对象”;(2)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运用,混淆了“理论”与“实践”、“意识形态”与“历史科学”,其实质是一种自然法学说。凯尔森对马克思的两个批评确实具有针对性,但他对于马克思所研究的“特殊对象”以及表述对象的“特殊逻辑”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却失之肤浅,有待深入。我们认为,马克思在探讨“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时,恰恰没有忽略“思维”与“现实”、“实然”与“应然”之间的二元性,且对“现实的具体”与“思想的整体”之间的差异有着自觉而深刻的揭示。下面我们将以凯尔森的上述批评为契机,重新检视马克思所研究的“特殊对象”与其表述这个对象的“特殊逻辑”之间的关系,以回应凯尔森的批评。
首先,与凯尔森不同,马克思视“物质生产”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他的研究对象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35)。如上所论,只有基于“生产一般”的抽象,马克思才能进入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个别”。因为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以太”与“普照的光”。
其次,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的对象”与“对象的逻辑”、“思维的具体”与“现实的具体”之间,一般来说是“非对称”的。因为“思维”不是“现实”,它只是思维着的头脑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思维的具体”能够表现为“思想的总体”,但是这个“总体”事实上只是思维的产物、理解的产物;而在作为整体的思维中,存在着很多范畴,既有简单的范畴,也有比较具体的范畴,但这些范畴之间的运动并不就是现实的运动,世界也并不是这些范畴运动的结果。马克思认为:“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或自然的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36)他列举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的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进程,但条件是必须以一个比较具体的现实基础作为前提。另一种是不存在这种递进的对应关系,恰恰相反,“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由此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37)。
再次,马克思没有否认“思维的具体”与“现实的具体”在特殊情况下存在着“同一性”的可能。也正是基于这种同一性的特殊条件,马克思才得以将“资产阶级社会”作为研究的对象,在思维中构造出“资本的逻辑”来。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38)这句话有两重意思:一方面,从“思维的具体”的意义来说,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典型”,因而是更加“具体”的样态,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9),即基于“具体”的范畴可以反向追溯比较“简单”的范畴;另一方面,在这个“思维的具体”中,“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40)。即在马克思所考察的“思维的具体”中,所有的范畴归根结底都是为揭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服务的。从“生产一般”的抽象到“资本”的具体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以“资本逻辑”所把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过程,反映的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因此,在这个思维的整体中,所有范畴的排列都必须以“资本”作为“定向标”与“拱顶石”。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范畴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41)。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现实的对象”与“对象的逻辑”、“思维的具体”与“现实的具体”的二元区分中,构造了“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的逻辑。但是,如何表述“资本”,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确如凯尔森所言,马克思是借助于黑格尔辩证法来表述“资本逻辑”的。马克思在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这样提到:“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42)。
而“资本的逻辑”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逻辑”之间确实也具有某种亲缘关系,正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具有组织世界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观念性的力量,并非经济基础,也不是什么上层建筑。……不管是以怎样颠倒的形态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运动中依然具有‘能动性的一面’。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记述的那样,认识到这一点的并非那些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而是黑格尔”(43)。那么,为什么黑格尔具有这样的“援用”价值呢?用内田弘的话来说:“黑格尔的逻辑方法,一贯地延续着从外在化到内在化的逻辑,一个事物发展并分为两个,从两个又分为多个,在分化和独立的最后,所有对立事物之间一方面是互相对立,同时又在这种对立中把自身不具备而对方具有的内容引向自身,从而与对立面结合起来,最终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看到近代市民社会把人的生活和生产的诸要素进行分化,规定为私有权,却又把它们结合起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人的生活这一特征。货币独占了分离与结合的双重作用,而以货币或商品的形态不断增加的是资本。黑格尔敏锐地发现了现实的市民社会的分离—结合运动,把它在思维领域用哲学一般的、抽象的方法描写为理念的活动。”(44)
但是,这种“援用”是有限度的,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表征资本运行的理论形式,这种表征形式具有某种类似于旁观者的、超乎个体人格与个人意志的特征,而现实中的个人却既是旁观者,也是行动者。从马克思的观点来说,由于他是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所以,他“并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而《资本论》中所“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45)。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借用黑格尔辩证法来表述“资本的逻辑”,还具有某种“实践”的意蕴。正如阿隆所言,马克思通过“辩证法”实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他给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上科学课,同时也为革命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的科学成为了革命的科学,在这里,仍然是在这个词语的双重意义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引发了科学的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所以这种批判本身宣布了革命的必然性。如果资产阶级只能靠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又有唯一的一种没有剥削的制度出现在前景中,人们怎能不成为革命者?”(46)
综上所述,马克思是集中对物质生产实践作了一个理论上的抽象,即从“生产一般”的抽象开始去表征“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而马克思是借用了黑格尔辩证法来表征“资本逻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就是一个类似于黑格尔的自然法学说的继承者,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关注政治活动这个维度。而只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的逻辑”是主导的逻辑,不仅是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也必须服从这个逻辑。科莱蒂与凯尔森只是抓住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外在形式,而忽略了马克思表述“资本逻辑”时的理论坐标与特殊形式。从这个意义说,如何理解“现实的对象”与表征对象的“理论逻辑”之间的关系,才是凯尔森与马克思之间的分歧之处。
五、从“纯粹的规范”到“规范的逻辑”: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的缺失
如果说马克思是借助于黑格尔辩证法来表述“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那么,我们发现,凯尔森虽然论证了“纯粹规范”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但在如何表述规范的逻辑形式上却陷入了困境。从回应凯尔森对马克思的批评中继续考察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的去向与得失,对我们将是有启发意义的。
凯尔森对纯粹规范之“归属逻辑”的阐释,散见于其各个时期的著作中,而未能一以贯之。如他在《纯粹法理论》第二版中提及从“基础规范”、“宪法”直到“立法”、“司法行政”的链条,且“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存在着不确定,以此为规范的逻辑留下空间。但他只是在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与自然法的各种变种之间探讨,批判“实然的逻辑”推广到“应然的逻辑”时必然发生的谬误,并没有展开“归属逻辑”的一般形式。同时,他还在《因果、报应与归属》中论及自然科学与法律科学之间的差异,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归属律的前身“报应律”的历史渊源,认为两者决非势不两立,甚至在晚年与逻辑学家克鲁格通信讨论规范的特殊逻辑及其表现形式问题,最后还通过《规范的一般理论》这部未竟之作展示其最终的成果。但是,凯尔森最终放弃了“规范的逻辑”这一想法,甚至对当时的一些逻辑学家试图建立“规范逻辑”的努力,还进行了一一批驳,并将矛头主要指向了一些他比较熟悉的逻辑学者(47)。有人因此把凯尔森规范理论的最后形式称为“规范非理性主义”(normative irrationalism)(48)。这就意味着,虽然凯尔森反对将“实然的逻辑”推广到“应然的逻辑”,但是关于“应然的逻辑”,即“归属律”的具体内容,却无法深入。这似乎意味着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的最终失败。
那么,凯尔森为何无法确立规范的逻辑形式?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坚持纯粹法理论的实证主义特征,而错失了自然法学说的成果,并将自然法学说中所论及的价值的客观性、法律的整体性等理论成果当作“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如果以康德道德哲学及其阐释的不同路向作为坐标,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凯尔森曾经认为,纯粹法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康德哲学。他说:“我是试图将康德哲学的先验方法运用于实证法的理论中——而不是如施塔姆勒那样陷入自然法的泥淖之中,当然这种实证法是在康德的先验哲学的意义上的实证法。正如康德哲学坚定地反对形而上学,那么,纯粹法理论的目标就是反对自然法学说。”(49)另一个新康德主义者施塔姬勒则认为,康德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为一种普遍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而其缺陷就在于没有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法律领域中去。他本人的任务就是要将康德所提出的方法一以贯之地运用到法哲学中。如果说施塔姆勒继续坚持了康德的自然法立场,那么,凯尔森关于“实然”和“应然”的二元论区分则更多的是休谟式的:在实然领域,他虽然接受了康德对于休谟的批判,即承认在实然领域存在客观性,然而在应然领域,他却接受了休谟的论断,认为在这里没有客观性可言,价值所依据的最终根据是人的偏好。因此,自然法是站不住脚的(休谟的立场),同时经验性的实证主义也是站不住脚的(康德的立场)(50)。
由此可见,虽然凯尔森与施塔姆勒两者都试图从康德的先验方法中找到一条超越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的道路,其进路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但是他们最终面临同样致命的困境:当他们抛弃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之后,仅仅是将康德的先验方法运用到法学领域去论证法的自主性、正当性或者纯粹性,实则是抛弃了康德道德哲学而重新诉诸某种理论哲学来建立一种法律理论。这里的问题在于,一旦将先验方法裁剪下来诉诸实在法的领域,应该如何说明这种先验知识的来源,进而如何自足地表述这种法律的逻辑?这些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也说明,确立认识的对象是一回事,如何恰当地表述这个对象的逻辑则是另一回事。即使能够借助某种形式将此对象表达出来,还需要从多方面限定这种表达的边界,特别是在“对象”的厘定与表述对象的“逻辑”之间、在表达形式的“构成意义”与“范导意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否则,又有可能错置“具体性”,从而陷入新的混淆当中。
在法律思想史上,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引起的争论也很多。如施密特便将规范性观念斥为“对实在性同义反复的夹生饭”(51)。在我们看来,他对“纯粹规范”的自主性论证与马克思对“生产一般”的提炼与抽象有异曲同工之妙。更重要的是,他基于纯粹法理论的立场对马克思具有针对性与说服力的批评,使得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检视马克思从“生产一般”进入到“资本具体”的思维进程。本文仅以“特殊的对象”与“特殊的逻辑”之间的匹配关系为线索,试图在马克思与凯尔森之间做一个“互文式”的考察,即在考察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辩证法表达“资本逻辑”的特殊形式时,反过来考察凯尔森展开“规范逻辑”时的困难及其内在根由。借助于这种考察,笔者力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寻求一个更为宽广的坐标,进而在此坐标下寻找其与现当代思想家之间的可能交流,从中伸展出政治哲学的可能生长点与出发点,以期真正推动当前国内哲学研究的纵深进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
③王时中:《从精神科学到历史科学——重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对立》,《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④Lucio Colletti,From Rousseau to Leni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2,p.185.
⑤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作者序”,王名扬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⑦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第39页。
⑧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第41页。
⑨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第54页。
⑩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第46页。
(11)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第230页。
(12)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第231页。
(13)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第257页。
(14)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第257页。
(15)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第266页。
(16)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第269页。
(17)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第49页。
(18)凯尔森:《纯粹法理论》“英译者导言”,第14页。
(19)凯尔森:《纯粹法理论》“英译者导言”,第9页。
(20)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17页。
(21)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17页。
(22)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21页。
(23)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20页。
(24)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54页。
(25)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54页。
(26)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55页。
(27)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55页。
(28)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16页。
(29)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56页。
(30)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58页。
(31)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61页。
(32)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27页。
(33)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第61~62页。
(34)凯尔森:《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理论》,吴恩裕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页。
(4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1页。
(43)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44)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1~102页。
(46)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47)陈锐:《规范逻辑是否可能——对凯尔森纯粹法哲学基础的反思》.《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2期。
(48)Hans Kelsen,General Theory of Norms,Oxford:Clarendon Pres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
(49)Stanley L.Paulson,Normativity and Norm,Clarendon Press,1998,pp.171-172.
(50)吴彦:《新康德主义法学的两种路向:施塔姆勒与凯尔森》,《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51)转引自凯尔森《纯粹法理论》“英译者导言”,第4页注释2。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研究”(项目号:08JZD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逻辑研究”(项目号:10CZX0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