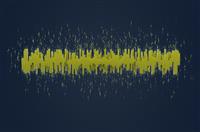
导论
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高难度但又具有根本意义的重要问题。目前国内外对这个问题有各种说法。本文认为,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对1945年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机构的历史、现在中国与全球治理机构之间的关系、中国在全球治理的领导机构(诸如联合国安理会和G20等)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对未来全球治理的贡献(作用)等四个方面来定义和说明。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复杂,却是可以说清楚的。
中国仍然在继续努力参加现存的国际制度(国际机构或者国际组织)。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申请和参加这些组织了。这些组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国际产物。从形式上看,中国似乎已经参加了所有的这类组织,但从内容看,中国距离全面成为这类组织的成员,尤其是在这里机构中占据和发挥与中国的国家地位(世界大国)一致的作用还有相当的距离。也就是说,中国与现存国际制度(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是在进行着一个双重的进程:继续申请加入那些尚未加入和融合的内容和项目,如IMF数据标准和SDR;要求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成为现存国际制度的改革者(改革现存国际制度的力量的一部分)。这一政策的继续是中国与美国在国际制度问题上不发生大的冲突的理由之一。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中心内容是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国际)治理机构。中国参加现存的全球性国际机构,是这些机构在21世纪的包容性和合法性(正当性)的主要来源之一。
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成为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第二个主要内容。如何改革全球治理?中国提出的一个办法是建立一些新的机构,如亚投行(AIIB),来促进全球治理的改革。表面上看,亚投行作为新建机构属于另起炉灶,但成立亚投行不是挑战、替代、颠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而是对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补充,具体来说,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开行等机构是互补关系。亚投行的成立实际上为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事实证明,改革全球治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大批盟友加入亚投行,表明了改革现存的全球治理是大多数国家的(国际)共识。①
协调旧的全球治理力量和新的全球治理力量的框架已经产生,这就是G20。中国是G20的创始国,更是G20目前存在的主要理由——世界经济老牌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协调。G20在2008年上升为成员国领导人参加的多边峰会,中国则在2015年成为G20领导机构“三驾马车”的成员(与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一道),而在2016年则将成为G20轮值主席国。G20达成了协议,要求改革现存的IMF等全球性机构。但是,G20中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则在改革IMF等现存机构,让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即不是原来的G7,而是G20来管理全球经济)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中国在2016年杭州峰会上,如果能让G20在推动对现存全球治理的改革上发挥中心作用,以及让G20成为管理全球经济的主要平台,则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国际领袖。
中国提出(提议)建立真正的新的国际制度(国际机构)是下一步的事情。除非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目前势头发生大的逆转,中国为一个更加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设计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将不可避免。亚投行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新的国际机构(国际制度)。中国如果在现有国际制度中全面融入且促进这些机构改革到位了,协调了新旧国际势力之间的关系,推动现有国际制度适应21世纪的世界现实,接下来才能带头建立真正的全球治理新机构。即使改革成功,现有国际机构也无法满足全球治理的需要,世界需要新的机构。这些新机构不是对现有机构的补充,而是与现有机构并存,甚至可能最终取代现有机构。如果中国设计的全球治理体系被世界认可和接受,真正的全球治理时代将开始。
有人认为,全球治理的趋势是多元化(pluralization),且把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等看做是中国试图多元化全球治理。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一书中的观点,以及他关于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和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IMF等)之间“并存”的看法,其实更代表了一些西方人的深层担忧。③但这样的担忧其实是多余的或者错误的。如上所述,由于中国继续加入而不是停止加入现存的全球治理,同时,中国为了现存的全球治理的存续而担任主要改革者与协调者之一,全球治理其实并不存在多元化的势头。
中国继续加入现存全球性的国际制度
以中国与IMF的关系为例。
第一,1944和1945年,中国是IMF的创始国,这如同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一样。但因为中国的国内政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取代中华民国)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80年才加入IMF。
第二,中国在IMF中拥有执行董事,现任执行董事是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博士。
第三,中国参与了G20集团要求IMF的2010年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提出的时候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仍然屈居IMF第三大股东国,即屈居日本之后。这表明,旧的国际治理体制不可能让中国拥有应该拥有的地位。截至写作本文时,由于众所周知的美国因素,IMF的这一改革尚未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了2014年11月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G20峰会并同意了该峰会的《公报》:“我们承诺维护一个强健、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重申将继续落实圣彼得堡峰会承诺,并因此对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第15次份额总检查以及新份额共识的持续拖延深感失望。落实2010年IMF改革方案仍然是我们最首要的任务。我们敦促美国批准上述改革方案。如今年底前未实现,我们将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现有工作基础上研拟下一步的政策选项。”④
第四,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继2002年中国加入IMF的数据公布通用标准(GDDS)之后,“中国将采纳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这一采纳标志着中国的经济数据透明度提高、国际可比性上升。习近平宣布这一决定后,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在布里斯班发表了“欢迎”声明:“我对中国接受SDDS的意向表示欢迎,这将极大地促进及时和全面的经济与金融数据的提供。中国致力于改善统计数据的发布,我对此表示赞赏,并注意到近年来取得的进展。中国计划从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提升到SDDS,是这一进程中的下一个重要步骤。”⑤2015年6月,中国的宏观数据公布标准正式调整为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⑥
第五,自2009年以来,尽管中国没有正式申请加入IMF设立于1969年的“特备提款权”(SDRs),但是,关于中国加入SDRs,以便使人民币成为与美元、欧元等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并驾齐驱的国家货币的国内外讨论非常热烈。一般认为中国政府希望人民币被纳入SDRs。
从形式上讲,中国已经加入了全部现存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国际制度),但从内容上看,如同上面提到的人民币尚未加入SDRs(当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货币没有加入SDRs,但世界上叫做“大国”的,尤其是“第二大经济体”,没有加入SDRs的,除了中国,没有第二个),以及中国刚开始按照IMF的标准“治理”国内经济统计数字,都说明中国在实质上还没有完全进入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将近40年,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入(20世纪80和90年代一度甚至用“接轨”、“融入”,而目前则用“对接”)现存的国际制度体系。如上所述,中国仍然在继续这一政策。
从2009年年G20匹兹堡会议以来,经过了2010年G20首尔会议,中国开始以现存全球治理的改革者的形象出现在国际体系(世界经济)中。
以刚刚过去的G20布里斯班峰会为例。如上所叙,中国同意和支持《G20布里斯班公报》的内容。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这份多边《公报》的最重要部分其实不是2014年G20澳大利亚轮值主席下的“增长”主题,也不是其澳大利亚精心推动的另一个主题“(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而是“加强全球制度”。也就是说,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主张加强而非削弱现存的全球制度。现存的全球制度是现行的世界秩序的化身或者代表。
然而,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主张的加强全球治理不是指维持不改革的旧的全球治理(以国际组织为化身),而是要求改革全球治理。从2010年到现在,中国改革全球治理可以分为两个内容,或者两个阶段:
第一,谋求在国际体系内改革全球治理。中国参与了改革IMF的行动,但中国很快发现改革旧的全球治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得到大多数国际体系的成员的认可、同意和支持,如果控制全球治理(国际组织)的霸权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同意、抵制和充满疑虑、上纲上线(即担心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上升会影响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的控制或者主导),全球治理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这里不是说美国就是全球治理改革的阻力,而是说,美国不会简单同意或者支持多边机构,如G20的全球治理改革意见。尽管美国参加了这些多边机构(如G20),但美国的国内政治进程决定了,美国参加的多边进程往往会被否定。奥巴马政府继续小布什政府而参加G20进程,同意了G20的IMF改革主张,但是,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上也因美国国会封杀IMF改革计划而恼火。奥巴马总统没有让G20布里斯班峰会取消其《公报》中的“落实2010年IMF改革方案仍然是我们最首要的任务。我们敦促美国批准上述改革方案”,而是同意了这样的多边声明。
第二,当发现改革现存的全球治理困难重重,如同其他国家,中国也选择了另一种改革路径,姑且将这一做法称为“在国际体系之外改革全球治理”。
亚投行的出现加强了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主要改革者国家的地位。亚投行的概念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中国充当了冲到前面的全球治理改革者的角色。加入亚投行的欧盟诸国(欧盟大多数国家加入亚投行)等美国的盟国不顾美国的反对与中国站到一起,主要是因为这些欧盟国家都支持全球治理的改革。加入亚投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全球治理改革的“投票”。加入亚投行的都是主张改革全球治理的,而反对亚投行的则是不主张全球治理改革的。美国因反对亚投行而成了反对全球治理改革的力量。由于改革全球治理会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甚至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超过日本,且影响日本在一些全球治理机构的控制地位,如同美国,日本从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出发,反对亚投行,也不参加亚投行。
亚投行是改革全球治理的一个方法,但却引起、暴露了改革全球治理的复杂的国际政治。关于全球治理及其改革的政治如此复杂,中国由此也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中国原以为只要不主张控制、主导、霸权而是主张“多赢”“共赢”,就不会有那么复杂的国际政治阻力。美日反对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和欧盟大多数国家加入亚投行说明,关于全球治理的世界政治仍然是复杂的,即多赢和共赢仅仅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方面、一种可能,并不是全部方面和全部可能,“零和”仍然是普遍存在,不管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
展望未来,已经走上全球治理改革者道路的中国,并没有退路。重新接受美日对全球治理的控制,不谋求对IMF的改革,停办亚投行或者不搞新发展银行(即金砖银行),也未必就能讨得美日的欢心,却使一个更加需要全球治理的中国在国际体系更加举步维艰。同时,中国假如在全球治理改革上退缩,又会得罪那些期望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国际改革势力(如欧盟国家)。唯有继续扮演改革者的角色,同时在旧和新的国际组织内处理好复杂的全球治理改革的政治,方能争取全球治理改革的实质进展。
从财政、金融的角度,G20如果涉及太多的所谓“非经济”的东西,很明显是不必要的负担。在回答由G20衍生出的B20、T20、L20等各类组织所能扮演什么样的作用的提问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表示,所有各类这样的机构都反映了一个需求,即把各方面的想法和方法都综合进来去解决问题,因为G20现在对维持全球的经济稳定来讲异常重要。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则补充道,G20一开始只是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由财长会向领导人峰会报告,然后在峰会上做出决定。但是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衍生品,“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一百多个”。这上百个会议都要向财长会议做汇报,然后由向峰会做汇报。“我想到这个事情,头都大了。中国有句话是集思广益,各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但如果最后都出口到财政部长这里,然后向峰会、向领导人报告,我们觉得恐怕很难操作”,“很多机构都是越做越大,然后做加法容易,做减法很难。轮到我们当轮值主席了,很发愁”。⑦
然而,若从整个国家的外交和全球趋势来看,G20代表了主要的新旧国际政治势力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是一度被国际政治、历史和国际战略学者吵得热烈的“国际权力转移”的解决方案。老牌的国际政治力量,如美国、欧盟和西方七国集团(G7)代表的所谓“既得力量”(established powers)和中国、巴西、印度等代表的“新兴力量”(emerging powers)通过一个框架即G20并存。这是难得的走向新的全球治理和新的世界秩序的有利机会。G20是两次金融危机(1999年G20的成立是为了回应所谓“亚洲金融危机”,而2008年G20上升为政治领袖的峰会则是为了回应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物。我们要感谢金融危机,为未来的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框架(即G20)。
这类框架之所以理想,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是21世纪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笔者在2011-2014年是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承担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21世纪的大国协调——增进大国之间的多边主义》的主要研究员之一,与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印度等著名研究机构的学界同仁一道,就21世纪的大国协调进行了为期3年的系统研究。我们的结论是,在21世纪“国际权力转移”和“多极化”的趋势下,更加相互联系的全球化世界迫切需要大国协调,而不是相反。但是,目前的大国协调,从联合国安理会(P5s)到G7,并不能满足21世纪的世界政治现实。而G20和“P5s加上德国“(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框架)等则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面向未来的大国协调。⑧
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欧洲协调(即欧洲范围的大国协调)被视为是当代全球治理的历史起源。⑨同理,21世纪的大国协调也是21世纪全球治理的基础。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述《21世纪的大国协调》国际学者组向全球各国推荐大国协调作为走向全球治理的途径。
笔者在2015年于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大学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应该率先促进亚太地区大国协调局面的形成,并进一步以G20为框架促进全球的大国协调。⑩
2015年中国加入“三驾马车”,与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一起成为G20的轮值“领导”国家之一,即负责G20宏观政策的协调与合作进程。这是因为中国将在土耳其之后,担任2016年G20杭州峰会主席国。担任G20等轮值主席国就是担任国际领导,中国如何履行好这一国际领导责任?
对目前的全球治理转型来说,最关键的不是别的,而是把G20当做为21世纪的大国协调的方式之一。大国协调是全球治理的集体领导。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轮值G20事关全球治理的未来,是中国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最重要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全球治理的进化与其他生命一样是分“代”的。首先是全球治理的起源,比如上面提到的19世纪产生而一战前崩溃的欧洲协调(European Concerts)是全球治理在欧洲的最早实践起源;1945左右,为避免世界重蹈世界大战而设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安排,从联合国到国际金融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冷战(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使这些二战后的国际治理(即全球治理的前身)无法发挥作用,联合国安理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全球性、统一性的和包容性的,因为世界划分为美国和苏联两大集团、两大阵营;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的呼声出现,开始探讨联合国改革方案,国际金融制度(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也提上议程,但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实质进展不大;在21世纪,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面对许多全球问题更加需要全球治理,但谁来提供全球治理?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崩溃”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探讨、设计“后布雷顿森林体系”(post Bretton Woods System),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全球)金融治理(安排)的构想、计划、倡议。
本文认为,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等新型的国际金融组织还不属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范畴。中国在许多场合不断告诉世界,亚投行等机构的设立不是另起炉灶。这是中国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继续:不管是金砖合作(BRICS)还是亚投行(AIIB)都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补充”,金砖合作与亚投行等与现存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平行和相互取代的。
这样的说明,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是正确的,也是中国的本意,但是,难道中国就彻底排除了“另起炉灶”即催生下一代全球治理的可能?
中国必须要超越目前的全球治理,不必在全球治理上“韬光养晦”,而有必要在发起亚投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之后,再进一步,鼓励一些重要的学者及其所在的学术机构大胆探索下一代的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如果目前的全球治理改革失败,全球陷入严重缺少全球治理而出现大混乱,甚至无序的状态(目前不少非常重要的美欧学者对此十分担心),则中国不妨公开提出我们的全球治理方案,为一个更加有序、包容、民主、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我们的贡献。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四个主要角色:参加者、改革者、协调者和设计者。发现和定义这些角色是为了进一步明晰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国高速增长之所以可能,与中国加入并“强化”现存的全球治理有关。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从现存的全球治理中“受益”,尽管这些主张者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学术研究:即仔细认真地探讨中国过去的增长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然而,从逻辑上讲,如果认为现存全球治理已经变成中国下一步增长或者由于增长导致的发展的阻力,那么,中国就需要寻求全球治理的变革。
现存的全球治理,从WTO到IMF,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为其越来越“不争气”,对世界秩序的贡献越来越弱,这些机构的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且要求他们做的改革和他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进展有限,甚至没有进展。
经历至少三代人的演变,发起这些全球治理结构并一度做出主要贡献的美国和欧洲(欧盟)与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一方面,西方仍然需要通过控制这些机构显示西方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性(centrality)或者领导地位,所以竭力维持对这些机构的控制,即维持现状;另一方面,正是美国而不是别国的作为对这些全球机构的失效、低效率、不作为、改革无进展、僵局等负有主要责任。不仅如此,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欧洲也是)正在成为这些全球机构的掘墓人,即美国在放弃或者抛弃当年发起、创立和维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另起炉灶之图谋和行动很多。比如,除了利用WTO,美国不顾不管WTO的死活,而是进行TPP和TTIP的谈判;美国拖欠联合国的会费到现在也没有补交的希望,至于美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的国际干涉,更是多得可列一个长单子;而最近5年,则是美国国会不同意IMF改革方案,即使奥巴马政府希望美国国会有所作为。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现实、迫切又长远的问题是:现存全球治理,具体来说,现存全球机构向何处去?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旧的全球治理能够经过改革而获得新生吗?或者,旧的全球治理因疾而终之后有无新的全球治理取而代之?新的全球治理是多元化还是相反?这是事关世界秩序的根本问题,需要我们深入讨论。
注释:
[1]David Daokui Li,"The AIIB as China"s Pilot Attempt to Reform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Foreign Affairs Journal,Summer 2015,pp.28-31.
[2]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将在2016年2月举行题为“Pluralizing global governance? China,BRICS and Global Governance”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3]庞中英:《读懂了基辛格,就读懂了世界?》,《环球时报》,2015年8月17日。
[4]见《G20布里斯班峰会公报》,2014年11月16日。
[5]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np/sec/pr/2014/pr14520c.pdf.
[6]http://finance.caixin.com/2015-07-18/100830275.html.
[7]http://economy.caixin.com/2015-03-29/100795866.html.
[8]http://www.hsfk.de/fileadmin/downloads/PolicyPaper_ATwentyFirstCenturyConcertofPowers.pdf.
[9]Jennifer Mitzen,Power in Concert: The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Global Governanc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10]http://www.hs-fulda.de/fileadmin/Fachbereich_SK/Professoren/Herberg Rothe/Implications_of_World_War_I_for_the_Current_ Conflicts_in_Asi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