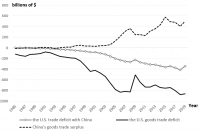11月13日,“黑色星期五”,法国巴黎见证的无差别恐怖袭击震惊了整个世界。14日,ISIS公开表示此次袭击系“哈里发的忠诚士兵”所为。此前,ISIS刚刚于周四宣称对黎巴嫩爆炸袭击负责,并发布视频威胁称将让俄罗斯“血流成河”。这一连串事件再一次将众人的目光集中于ISIS与伊斯兰教之上。自2001年9·11事件后,伊斯兰恐慌症在西方社会不断发酵。随着ISIS的兴起,公众对伊斯兰教的负面印象更是愈发深化。
对于“伊斯兰教与民主无法相容”这一观点最广为人知的叙述,来自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冷战后的世界并非一帆风顺,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会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逐步突显,愈演愈烈,其中“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最为根本。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写道,“伊斯兰文化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民主未能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他认为,西方面临的问题不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在伊斯兰教本身。
亨廷顿的观点自提出后就一直饱受争议。众多学者指出,伊斯兰教和其它主要宗教一样,其内容都具有多种诠释(multivocality)的可能。正如恐怖分子可以寻求循其所愿的解释,民主人士同样也可以在《古兰经》的基础之上构建宗教和解的架构。此外,当前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政教合一的表现,本身也不足以说明这一政体将来永远不会发生变革。西方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来,基督教的政教合一程度都远甚于当今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公元352年,君士坦丁一世以罗马皇帝的国家权力号召各地主教前往尼西亚(Νίκαια,今土耳其伊兹尼克)集会,共同发表教义声明,是为政教合一的体制起源,而此时距伊斯兰教的诞生还有三个世纪之久。直到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在欧陆兴起,大众观念中,国家权力的来源从神授转变为民授,政教分离逐渐成为共识。从历史角度看,没有理由认为,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会一直固守政教合一的传统。
因此,对于当下的恐怖主义问题,简单将其归咎于伊斯兰教造成的文明冲突,可能会掩盖真正的问题——为何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络绎不绝?任何一种社会动员形式,之所以能够实现,与其说是出于其领导人的政治口号和魅力,不如说是源自被鼓动者本身对于自身身份的意识和认同。
起初,人的生活范围大多局限在自己所属的小群体中,很难与其它聚落接触,因而身份几乎完全由出身和继承决定。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世界各地开始逐渐联结成一个整体,经历了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所描述的“从社群到社会”的转变——整个社会日渐融合,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其社会身份不再固定,而须自行探索和选择。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理论,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印刷普及使得用同一语言印刷的书籍和报纸得以传遍整个民族,这一转变带来了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想,民族身份也逐渐成为了取代社群身份的认同基础。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共同的民族身份是凝聚国家的基础,因而国家边界也必须扩展至囊括本民族全部人口的程度。二战时期,希特勒便以此为全体德意志民族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基础,因而有效实现了政治动员。
从这一角度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潮同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民族主义颇为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奥斯曼帝国解体,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而与此同时,传统居于印度和印尼的穆斯林也开始迁往美洲。如今,穆斯林占据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可以想见,杂居的穆斯林信众在非伊斯兰地区时常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遵循本地社会规范的外在表现同探求自我价值的内在追求,此间差异巨大,俨然不可调和。然而,在外界社会看来,身份认同危机很可能被简单视为异族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不足为虑,这无疑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例如,今年二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尔夫(Marie Harf)在接受采访时曾暗示,恐怖主义的根源或许在于“就业机会缺失”。但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所言,穷人的真正耻辱并不在于缺乏资源本身,而在于他人的漠视。黑格尔所谓“寻求认可的斗争”即是此意——自我身份无法获得公开认可,会对人性造成根本性的压抑。
当然,寻求身份认同并非永远导致暴力冲突。近代历史上,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即为探寻自我价值的的和平典范。但当今欧洲的情况似乎并不如此。早在2006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于论文中指出,“无法更有效地整合穆斯林移民,无疑为欧洲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欧洲社会不愿公开直面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而是将每个穆斯林当做独立个体看待,也不如美国一般为所有公民培养了基于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独特国家身份。久而久之,“文化多样性沦为了自由多元主义的装饰品”,仅仅表现为少数族裔餐厅和五彩缤纷的装束,而一旦这种表现被视为“出格”,即会立刻遭到禁止——2004年法国对于穆斯林头巾的禁令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一旦主流社会无法提供身份认同的可能,甚至忽略身份认同的必要,极端主义者就立刻找到了可乘之机。福山指出,正如同希特勒为德意志民族提供了民族主义的自我价值一般,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也为部分散居各地的穆斯林提供了自我价值的来源。而这一点ISIS在组织形式上体现得格外显著,其官方宣传刊物《达比克》(Dabiq)长期号召全球各地的穆斯林信众从其居住地“出走”,迁移至ISIS所在地。2014年出版的第二期杂志为其读者提供了详细的行动指南:如果无法成功出走,则应在本地向ISIS领袖宣誓效忠。“生活在警察国家者,若会由于此种宣誓而遭受逮捕,则应以匿名方式向全世界传达效忠之言。”如果“出于极端无法控制的原因”,甚至不便匿名效忠,只要虔信ISIS是属于所有穆斯林的国土,亦不至死于“蒙昧” 。公开宣誓效忠有双重目的,除了“在不信教者的心中种下痛苦”之外,更可以“彰显穆斯林对彼此的忠诚”,凝聚身份认同。事实证明,ISIS的这一宣传策略直击要害,极为有效,也为世界带来了惨痛的代价。
9·11事件发生前一年,美国政治学者艾尔弗雷德·斯特潘(Alfred Stepan)曾将宗教和政治关系的理想形式描述为“双生容忍”(twin tolerations),亦即政治体制容忍宗教发展,而宗教教义同时尊重政治体制。不幸的是,这十五年来,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依然出于政治和宗教互不容忍的窠臼之中,甚至不乏恶化之势。此次巴黎悲剧之后,执政者和社会公众如不直面这一问题,努力向真正解决的目标迈进,类似的悲剧只怕会不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