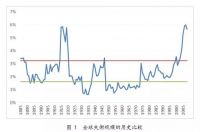从“基地”组织的美国“9·11”恐怖袭击,到IS的被称为法国“9·11”的巴黎恐怖袭击,从本质上来说,这是野蛮与文明间的战争与冲突,但“文明冲突”的话题再度被炒热。
尽管伊斯兰世界对IS加大了谴责与声讨的力度,巴林、约旦、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君主国亦参与了对IS的空袭,但在伊斯兰教去污名化的努力上仍显得无能为力。在IS的恐怖暴行和歪理邪说面前,“伊斯兰”这个阿拉伯语词汇所饱含的“和平”与“顺从”的意义显得更加珍贵。
穆斯林之王的迷梦
IS远扬的恶名及昭著的恶行地球人都知道。然而仅仅就在一两年前,全世界对于IS还知之甚少,就连其到底叫什么名字都争论不已:是ISIS还是ISIL?如果说ISIL译为“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确无争议的话,那么ISIS就有至少两种译法:“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和“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
事实上,这些译名争议来自于不同文明对同一片土地在命名上的各自表述,即大致上涵盖如今的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西亚阿拉伯国家的地中海东岸地区。
首先,“黎凡特”(Levant)代表了西方的立场,该词来自于意大利语Levante,意思是“升起”,即太阳自地中海东岸升起,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在推广“黎凡特”这一名称上发挥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其次,“大叙利亚”代表了介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立场,“叙利亚”(Syria)一词来自于古希腊语Syrioi以及更早的Assyria(亚述),即亚述帝国统治下的近东地区,即便归属西方世界近2000年的叙利亚地区在被阿拉伯人征服并皈依伊斯兰教以后,该词在19世纪之前仍具有强烈的西方和基督教的涵义,且在当地并不流行。直至一战结束后,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于1920年成立的阿拉伯叙利亚王国首次正式采用“叙利亚”(阿拉伯语为Sūriyya)为国名。但全新的叙利亚国家也继承了西方语境下“大叙利亚”的衣钵,心怀“大叙利亚”之梦延续迄今。
最后,“沙姆”(Sham)代表了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沙姆”是地道的阿拉伯语词汇,意为“左手边的土地”,这来自于在阿拉伯半岛上坐拥两大圣地的希贾兹人眼中的图景,他们面朝东方,以北为左,以南为右,于是乎称左手边的地中海东岸地区为“沙姆”,称右手边的地区为“也门”(Yemen),即今天的也门共和国。由于阿拉伯世界自一战以来分裂为诸多西方人臆造的所谓“人造国家”,且未有一个国家以“沙姆”为国名,因此阿拉伯世界以外对“沙姆”一词极为陌生。
IS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各国政界、学界乃至普通民众对地中海东岸地区地理、历史和文明的再认识,“黎凡特”“大叙利亚”与“沙姆”之间所暗含的相互矛盾的立场开始浮出水面,如何称呼地中海东岸地区成为某种新的政治正确。
正当国际社会对这一名称基于各自立场进行艰难且谨慎表述的时候,这个恐怖组织2014年6月的“贴心”更名行动立刻使得国际社会一直以来的分歧烟消云散,因为它的名称中消除了任何带有地理意味的词汇,仅仅保留了“IS”。国际社会从此在称呼该组织名称上如释重负。
但更大的问题也出现了,IS的更名行动已经表明,它的胃口不再满足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的实际控制区。不仅如此,IS激起了新一轮地理文明的关注热潮,它将视线首先投向地球上那些历史上和现实中被穆斯林统治的欧亚非地区,首选在这些地方实现存在。其名册上引经据典、以古典和生涩词汇命名的板块包括:安达卢斯(Andalus)、欧罗帕(Orobpa)、安纳托尔(Anathol)、高加索(Qoqaz)、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呼罗珊(Khurasan)、马格里布(Maghreb)、齐纳纳之地(Land of Alkinana,源于埃及旧城)、哈巴沙之地(Land of Habasha,源于古埃塞俄比亚部落)、沙姆、伊拉克、希贾兹、也门。
IS已在利比亚、埃及西奈半岛、沙特、也门、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并有成员在摩洛哥、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活动,并将“国家”划分为“省”(Wilayat)。
除了设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省以外,其实际控制的还包括设在利比亚的拜尔盖(Barqah)省、的黎波里省和费赞(Fazzen)省,以及设在埃及的西奈省,非实际控制的包括当地效忠组织所建立的阿尔及利亚省、呼罗珊省、西非省(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建立)、高加索省(俄罗斯达吉斯坦),并单方面在也门设立了若干省;其触角正在延伸至东南亚和东非,并已接受印尼和菲律宾有关极端组织的效忠。
总而言之,IS头目巴格达迪拾起了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丢弃了90年的“哈里发”王冠,以东西方文明消长与交融的地中海东岸地区为大本营,做起了迷梦。
在无视与轻视的缝隙里野蛮生长
IS的兴起过程中有许多偶然性因素,美国失衡的中东战略和“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为其壮大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国际社会并未能预测到IS会在日后有着如此超强迅猛的势头,并最终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全世界头号恐怖组织。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在阿富汗生存空间极度萎缩的IS的前身“一神论与圣战组织”迁往伊拉克并加盟“基地”组织,从此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名义开展活动。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以“撤军伊拉克,增兵阿富汗”为主要内容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的推进,美国于2011年开始撤军伊拉克,该组织随之开始急速壮大,名义上仍为“基地”组织分支,但已开始走向攻城略地的“建国”道路。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该组织又趁机进入叙伊交界地区发展,并与“基地”组织叙利亚直属分支“努斯拉阵线”(Al-Nusra Front)爆发激烈冲突,因统治区域的变化而于2013年更名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这招致“基地”组织的不满,“基地”组织最终在2014年2月断绝与该组织的关系。IS在被“基地”组织赶出教门前的一个月正式宣布“建国”,其“首都”为叙利亚城市拉卡,而这仅仅被视为“基地”组织“建国”实践的另一个案例,伊斯兰世界对其重要性显然关注不够。
“基地”组织长期以来以隐形存在方式为主,“来无影去无踪”是本·拉登与美国长期周旋的法宝。不仅如此,“基地”组织领导层不断变换藏身地并寻求各种势力的庇护,其袭击目标主要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因为“基地”组织的这些特点,即便出现了其分支机构在也门的“建国”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只被视为“小插曲”,丝毫动摇不了“基地”组织的一贯形象。
2011年5月,时值也门陷入党派部族势力拉锯、社会乱象丛生之际,“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AQAP)在相继占领南部阿比扬省省会津吉巴尔市、贾尔市以及沙克尔市等城镇之后宣布建立以津吉巴尔市为首都的“伊斯兰酋长国”。直至2011年9月,经过数月交战也门政府军收复津吉巴尔市后,此次“建国”实践才宣告暂告一段落。
2012年1月,该组织又故伎重演在也门南部拉达地区宣布“建国”,类似戏剧化的“建国”活动接二连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伊斯兰世界无法对“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区的“建国”活动予以重视,认为这不过是也门式“建国”活动在沙姆地区的复制,其命运只会是昙花一现,遑论其影响力。
更何况“基地”组织不仅不支持其“建国”,甚至还将其除名,伊斯兰世界普遍相信该组织在失去“基地”组织这个大靠山后,其“建国”迟早会分崩离析且该组织的生存前景堪虞。
伊斯兰世界此时主要关注的领域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以后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及其政治局势问题。当时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去国出逃、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被俘身亡、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囚笼受审和民选总统穆尔西的军方罢黜、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苦撑待变以及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被逼交权和哈迪的沙特流亡,这些图景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其次是美国在21世纪两场反恐战争中所制造的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塔利班的卷土重来、伊拉克的群雄割据、伊核问题的反复多变,使得伊斯兰世界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最后是老生常谈的巴以问题。中东世界诸多新问题层出不穷,巴以问题已在“阿拉伯之春”以后高度边缘化,但其核心地位仍难以撼动。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依旧冲突不断,伊斯兰世界总体上依旧不时隔空劝和促谈,以最大限度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试图实现该地区的稳定。虽然“基地”组织制造了“9·11”恐怖袭击,但此后十余年并未有大的动作出现,伊斯兰世界此后逐步自我减压,尤其是本·拉登被击毙以后,“基地”组织被认为遭受重创而元气大伤。
在“阿拉伯之春”中生机勃勃的伊斯兰大国土耳其和沙特在中东地区展开了模式之争,对IS一度都采取了有限支持的态度,但其具体目标有所不同。土耳其极其关注藏匿伊拉克库尔德区的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与IS之间的剧烈冲突,其心腹大患是库工党而非IS。土耳其甚至放松与IS控制区之间的边界管理,默许诸多圣战者借道土耳其领土前往叙利亚。
沙特因海湾战争以后谋求美军直接保护而饱受伊斯兰激进势力的谴责,为了巩固王室统治的合法性和自我强化“伊斯兰盟主”的名号,沙特利用其巨额石油美元一方面斥巨资修缮圣地麦加的朝觐地点和展开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资助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激进派别以抵消过分亲美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其中就包括IS,当然沙特与IS在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上有着利益的一致。
IS迎着伊斯兰世界无视与轻视的眼光,在土耳其和以沙特为首海合会君主国的保驾护航下,最终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权力缝隙中成长起来。
IS对伊斯兰教的滥用已到极致
剥掉“基地”的外衣后,自立门户的IS可谓无拘无束,更加魔性大发,开始四面出击,全线开火。
首先,与老东家“基地”组织开始恐怖竞争,其斩首、火刑、性奴、挫骨扬灰、集体屠杀、教派灭绝、毁灭文明等暴行连“基地”组织都看不下去,予以强烈谴责。其残暴指数急速上升,促成诸多“基地”分支改旗易帜,成为IS的“省”或盟友。
其次,除了一贯的反美立场外,IS还同时招惹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国。IS以比利时为据点,在法国巴黎多处制造暴恐案,并威胁袭击伦敦、纽约和华盛顿,炸毁俄罗斯民航客机,处死日本、挪威和中国人质,其结果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一致通过决议授权打击IS。
最后,袭击伊朗及其中东盟友。IS不仅在叙利亚、伊拉克与伊朗武装人员直接交手,还威胁入境伊朗;不仅如此,IS血洗真主党在贝鲁特的根据地,还威胁取代哈马斯统治加沙。一时间,IS亲手促成了一条具有最强代表性的反IS阵线。
IS不断利用现代社交手段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其宣传和招募大量运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手机APP等时髦工具,其发布的宣传片堪比西方大片,这些对蛊惑极端主义分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IS对伊斯兰教的滥用已到极致。
伊斯兰世界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关口,如何书写伊斯兰世界过往、当下与未来的历史需要全世界穆斯林的集体智慧。
西方著名神学者卡尔·洛维特将上帝的救赎历史与人类的演进历史、基督教史与世界历史进行了神学前提下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回顾与探索,对于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也进行了反思。伊斯兰世界的救赎,归根到底,既离不开真主的至仁至慈,也离不开全世界穆斯林对其他人类文明与历史表述的尊重与借鉴,而IS及其“哈里发”从神学理论到“建国”实践,无疑是此种救赎的倒行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