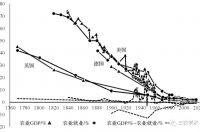改革开放一开始,执政党就把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这是大势所趋。那个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资源极度匮乏,社会不同群体之间陷入政治恶斗。改革就是要抓经济工作。这个改革策略非常正确,为社会提供了无穷的动力来追求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数亿人脱离贫穷,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不过,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政府是其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学术界把东亚经济体(包括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称为“发展型政府”,即政府主导和引领经济的发展。和这些经济体相比较,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要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不得不站在经济这一边,也就是和资本、企业家(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结成紧密的关系。这样就产生了人们所说的“权势一体化”或者裙带资本主义的局面。权势一体化不仅导致了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失衡,而且也导致了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
不难看到,我国的早期改革者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导致把经济政策简单地应用到社会领域,从而使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货币化。自由派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闯入了我国的社会领域。
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只有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主要表现在政府推动的私有化运动。但在很多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社会抵制,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都没有能够私有化。社会领域没有被强行私有化,主要是因为民主机制的存在,人民用选票否决了政府的私有化计划。这在撒切尔当政时期的英国表现尤其显著。在当代,新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导致了政府对金融领域缺少监管,从而酿成了危机。在我国,新自由主义有了不同的命运。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不一样。
我国社会没有抵抗能力,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很快就进入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在任何国家,这些领域并没有被视为是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企业,都是要求政府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被视为单纯的经济企业,成为暴富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医疗部门率先引入经济政策,医院成为暴富领域。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对付危机,有人建议教育的产业化。尽管政府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但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从此之后走上了激进的产业化道路。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导入了另外一个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即房地产。
改革、发展、稳定,这应当是中国所追求的良性发展道路,但现在的情况是,发展越快,社会越不稳定。为什么?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政府是通过破坏这些社会领域而追求发展的。在任何国家,如果医院、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个社会肯定是不会稳定的。在权钱结合面前,社会没有了任何权力。没有政治权力的合作,新自由主义不会在我国的社会领域如此快速蔓延。我国社会一直在抵抗着社会的被市场化和货币化,但一旦政府站到了资本这一边,社会便没有了任何有效的反抗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都是通过 GDP 主义这一巨大的动力机制摧毁着我国的社会秩序的。GDP 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化。政治人物需要 GDP 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就连一般社会成员也需要 GDP。
在一个以钱为本的社会,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缺少了经济数据,就变得毫无价值。医生可以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止治疗、律师可以为了钱而出卖灵魂、普通人因为担心被索取金钱而不敢扶起倒地老人、教授为了致富而把学术和教育当成了副业,等等,中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都是各种变相的 GDP 主义的产物。
但是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秩序可言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着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终极根源。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社会道德和信任就会变得毫不相关了。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上,市场和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种分离使得人类能够逃脱泛道德化的社会行为,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但另一方面,社会也必须受到保护,经济和社会必须有一个边界。如果经济领域可以也必须加以市场化,甚至必要的货币化,但社会领域则必须也可以拒绝过度的市场化和货币化。
无论在哪里,这种边界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无论怎样的社会,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没有这样一个边界,社会秩序和道德解体危机必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