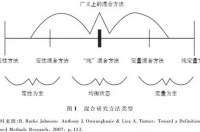近日有关中国即将推行债转股的话题引发不少热议。其实,债转股并非新鲜话题,早在17年前,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国有企业面临亏损和银行信贷不良资产增加,政府便通过债转股方式化解银行债务危机,即将国家开发银行和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贷款剥离给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为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其中,国家开发银行的一部分贷款直接转为对企业的股权。时隔多年,新一轮债转股有何不同之处?在执行的过程中又该从上一轮债转股过程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一方面,两轮债转股推行所面临的经济基本面情况有很大不同。1998年那轮债转股共计转股企业580户,转股金额为4050亿元。当时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国有企业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后来通过债转股等辅助政策,通过重点推进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中国经历了三年痛苦的企业转型,直到加入WTO之后,国有企业轻装上阵,民营企业活力增加,中国经济才凭借制造业优势,走出经济低迷,实现其后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而如今的情况是,虽然中国企业杠杆率不断攀升,但银行不良贷款率仍处于可控范围,但不良贷款增加速度较快的局面值得关注。根据中国社科院李扬团队的研究显示,2008年之前,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一直稳定在100%以内,全球金融危机后,加杠杆趋势非常明显,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由2008年98%上升到2014年的149.1%,扣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杠杆率提高到123.1%,高于美、英、德、日等对比国家情况。
可以说企业杠杆率过高的局面值得警惕,当然,如今银行不良资产率表现还是好于1999年的。根据银监会数据,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在2015年达1.27万亿元,相比于去年的8426亿元,不良贷款同比上升51%,而不良贷款率也升至临界值1.67%。此外,关注类贷款达到2.89万亿元,同比增加37%。说明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仍明显好于1999年,但快速增长趋势值得重视。
另一方面,两轮债转股所处的改革历史阶段不同。1999年债转股改革意在帮助国有企业纾困。其背景是,自1984年国有企业实行“拨改贷”以来,中国国有企业从国家无偿调拨的资金变成了企业必须支付利息的有偿贷款,虽然迈出了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伴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企业的放款迅速上升,而企业诸多经营理念与方式没有改善,最终导致国有企业财务状况不断恶化。归结来看,当时“拨改贷”虽然引进了选择机制,但没有建立退出机制,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为其提供了“最后的晚餐”,其后通过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以及银行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等多重改革带领中国经济度过危局。
然而,相比于早前五大行未上市的行为,如今情况是,此次债转股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主要国企均已上市,处理银行与企业坏账更多的是市场微观主体自主行为。这也就说明新一轮债转股过程并非“最后的晚餐”,更不是“免费的午餐”。是否选择债转股,选择对哪些企业债转股,以及如何评判债转股的收益与风险等,应该更多的交给市场主体自主选择,而非依靠行政力量,要重点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边界。
当然,尽管两轮债转股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经济基本面情况大有不同,但上一轮债转股推行过程中,仍有一些经验与教训值得总结。
第一,债转股要避免向僵尸企业纾困,处理好去杠杆与去产能的关系。上次债转股的主要纾困对象是国有企业,而笔者担忧此轮债转股是否也会演变成对僵尸企业纾困?
毕竟债转股出台的背景意在化解企业高杠杆率,而对于这方面需求较大的往往是多年来不断债务展期才能存续的企业,且这部分企业相当多数量处于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之中,如钢铁、煤炭,且以国有企业居多。根据Wind数据调查,截至4月16日,在1725家已披露年报上市公司中,144家连续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数,其中大多集中于传统的钢铁、化工、煤炭、水泥、玻璃等产能过剩行业。
同时,考虑到一直以来,国有企业在银行融资方面都存在着天然优势,如今中国经济基本面整体疲软,优质项目缺乏之下,银行似乎也更有动机将贷款向存在隐形担保的国有企业倾斜。
如此看来,去杠杆与去产能关系如何值得思考。可以看到,今年五大经济工作任务之中,“去产能”位列2016年中国经济工作任务之首,特别是钢铁、煤炭产业是去产能工作的着眼点,意在五年之内,钢铁行业去掉1-1.5亿吨产能,3-5年煤炭行业退出产能5亿吨、减量重组5亿吨。如果债转股在执行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向产能过剩企业纾困则不是一个好的迹象,因为这不仅与当前去产能的政策意图相悖,延缓结构调整的进程,也无法减轻银行金融风险,而是把风险从高杠杆企业转向了银行。
第二,债转股之后,公司治理要遵循市场化原则。与上一轮债转股类似,当前国企改革同样没有完成,在企业公司治理尚不完善的背景下,银行能否很好的履行股东职责,并得到股东应有回报?
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一旦银行由债权人转为股权持有者,进驻被整合的国有企业,且不说银行是否有足够多的专业人员可以进驻入股企业,就算是银行向入股企业派出董事、监事等人员,但在现有体制下,其行政级别很可能低于原债务企业的管理者,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出资方利益不受影响?银行能否履行其对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职责?
第三,债转股过程存在股东结构变化,如何减少由于大股东之争而虚加的损耗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可以看到,债转股会造成原有股东结构的变化,如果转股金额与企业原有资本额相比数额较大,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而这一过程也许仍存在矛盾与道德风险,比如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控股的企业而言,出于增加税收,稳定就业的考虑,地方政府可能希望避免企业破产,并尽可能的采取债转股,而其中一旦股东结构发生变化,甚至是影响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绝对控制,由是其不愿意看到的。
例如,早前也有文章中提到,在上一轮债转股的过程中,原有地方政府作为企业大股东,为了避免控制权旁落,出现在了债转股之前,通过各种方式,如增加林权等,向企业虚增资产的问题,而这为未来企业实现盈利埋下隐患。因此,如何处理好债转股过程中,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关系,避免不必要的损耗也十分关键。
第四,债转股要因地制宜,避免在落实过程中盲目跟风。当前债转股涉及到的微观主体,银行、企业抑或是资产管理公司,大部分已经实现上市,债转股更多的应该是市场主体之间的自主行为选择。双方考虑的基础是各自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且受制于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未取得较大进展的背景下,笔者认为不宜大规模推进,以免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扭曲,孕育新的风险。
对此,反思早前的四万亿经济计划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参考。当时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本意在于避免中国经济的大幅下滑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但从执行情况来看,当时虽然名为四万亿,后期带动配套资金落实下来居然超过10万亿,且金融承担了更多财政的功能,为后来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风险埋下伏笔。
这说明,对于政府积极鼓励的政策,下级单位,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国有企业与银行,无论是出于政治考核还是自身利益,都有足够的动机推动并促成。而这其中便存在着盲目跟风,忽视中长期风险,重视短期效益的可能。新一轮债转股同样要警惕政策执行过度的风险。
综上,笔者认为,新一轮债转股是化解当前企业高杠杆与银行不良率上升的途径,但不宜过度渲染,而应该循序渐进,并强调在整个过程中保持市场化的运作机制,降低执行过度的风险。此外,要认识到,无论是去杠杆、还是去产能如果仅以纾困国有企业为目的,则是暂时规避风险的举措,若想从长期来看化解债务风险,培养健康的市场主体与竞争环境,配套新一轮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无法逾越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