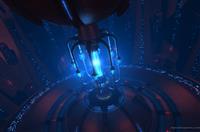在二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风风雨雨已经历了70年。它是二战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互结合的产物,“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1]根据《联合国宪章》(以下称《宪章》),该体制的核心机构是安全理事会(以下称安理会),其权力集中于持有双重否决权的中、英、法、俄、美等五个永久性常任理事国“手中”。这不仅表明了联合国组织结构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反映了二战后国际权力结构的新变化和新调整,更体现了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上的大国关系和大国责任。[2]
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队伍”里,中美关系不容小觑。作为亚洲大国,中国为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付出了许多努力,同时又承载着国际社会更多的期望和要求,正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世界领袖”的角色地位仍持续稳固,并随着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不时地调整对外政策。最近几年来,美国高调运用“再平衡战略”重返亚洲,给亚洲政治经济格局与和平稳定局势增添了新的变数。中国的“奋发有为”与美国的“战略转向”,共同开启了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大幕。[3]
鉴于中美两国在安理会内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显然会对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产生重要影响。集体安全是联合国的一项核心宗旨,它需要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善意合作,而当国际社会不得不共同面对恐怖主义、跨国洗钱[4]以及贫富悬殊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在国际法范围内,阐释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大国关系基础,分析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内涵及其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的影响,有助于明晰以安理会为核心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由此期望能助其改革与完善,进而提升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效率和质量。
一、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大国关系基础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国际法释解
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和突出的一种关系。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弄清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大国关系基础,有助于正确看待和规范理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
(一)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大国关系基础。首先,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是由大国设计并依托大国关系建立的。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权力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而大国间的权力政治“博弈”显然是十分危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凡尔赛条约》在规定上十分严苛,但对于战争的控制手段却又过于软弱,因此导致了1939-1945年之间的新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广泛残酷性激起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有很详细的描述,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对国会的演讲中以及与丘吉尔的通信中对其理想化的世界政治和安全组织充满了期待。[5]1941年8月,英美两国发表《大西洋宪章》,呼吁建立一个“永久性普遍安全制度”;1942年1月,其他26个国家发表宣言,支持《大西洋宪章》,并首次提出了“联合国”一词;1944年,中、美、英、苏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厘定了这一新的国际组织的基本轮廓,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大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上的地位和责任;1945年10月,《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国际集体安全体制得以建立,并由此开始“集中力量,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6]
其次,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核心机构是由大国协同领导的安理会。为了保障一种体制能够充分发挥效用,就必须建立一个核心机构来引导方向、规范行为、协调行动。作为集体安全体制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由法律化和制度化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和需要通过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宪章》中规定,“安理会是联合国体系内唯一拥有决策权的机构,追求全球安全需要服从五个大国的批准,并通过它们发挥地缘政治的作用来塑造世界安全。”[7]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世界上其他主要大国都曾就任非常任理事国或者正在任上。由于大国关系中存在着各种相互矛盾且又合理的要求,安理会不得不力图在不同的诉求之间寻找可以接受的平衡,以应对和解决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情势。
最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平稳运行依赖于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冷战时期,由美苏各自挂帅的“东西阵营”相互对立的格局常导致尖锐的利益冲突,使得安理会难以做出一致决议,致使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功能几近丧失。但大国也都深刻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分裂或者利益分歧的持续恶化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在“囚徒困境”中,不得不选择最大忍耐限度内的协调与合作。无论是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还是冷战期间爆发的各种危机,都充分显示了大国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不予克制的严重后果。在2014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上,西方大国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对战后世界秩序构成了挑战”,而俄罗斯则以“科索沃事件”为例来抨击西方大国的“双重标准”。[8]“领土完整是《宪章》的一项原则,但除了第2.4条外,《宪章》并未对此给予更多的规定,在与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而宣布独立有关的领土完整问题上也保持了沉默。”[9]政治“口水仗”之后,西方大国渴望在安理会内以法律的方式“对决”俄罗斯,同时采取单边经济制裁措施。但这些激烈行为或措施,并没有撕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关系,国际集体安全体制尚在平稳运行中。
70年的国际实践表明,没有和平、稳定的大国关系,没有大国担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就没有今天的集体安全体制。在这一体制内,中美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又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就注定了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特殊重要性。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深刻影响两国的全局利益,也作用于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秩序,更影响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稳定与效用。因而,从国际法角度解读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显得至关重要。
(二)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国际法释解。在宏观层面,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集中体现在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和建设上。一般意义上,竞争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自己一方的利益而对同一个目标的争夺或者相互争胜,争夺的目标不同就不会形成竞争。竞争者之间通常是互相排斥的,但一般不是敌对的;竞争的结果不是消灭对方,而是要获得“标的物”,即通常所谓的利益。在主权“林立”的国际社会,国家利益是国家主权的中轴,不是国家利益围绕主权旋转,而是国家主权围绕国家利益而展开。中美在竞争中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为核心动源,都深深扎根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中。[10]就美国而言,尽管人们不愿意将二战后依托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多边贸易体制(GATT/WTO)建立和运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称为“美国世纪的国际秩序”,但必须承认美国自那时以来在诸多领域内的强势地位和主导作用。[11]从中国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持续增强,外交已进入“奋发有为”阶段:在领土争端方面,中国的态度更加坚决,不惧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恫吓,坚决捍卫主权和正当权益;在经济外交领域,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扩大与周边国家的深度合作;在金融领域,中国不仅量力而行地对IMF和WB施加影响,而且还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可以说,中国正在以强有力的姿态参与“美国世纪的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建设。
但不可否认的是,竞争也包含着依存关系,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应该是有理性的,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进行的。非理性的、非规范化的竞争,必然会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并由此带来深刻的社会动荡,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从国际法角度看,中美之间的竞争首先应恪守《宪章》所确立的“各国主权平等之原则”,这不仅是法律上的、形式上的平等,更是实践中的、实质上的平等。其次,中美之间的竞争意味着相互间“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彼此尊重根据不同国情所选择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最后,中美竞争中出现的任何冲突或争端,都应以政治的或法律的方法和平解决,确保“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他国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12]
在微观领域,中美两国在战略上极力避免冲突和对抗,并进行着十分丰富的明示合作与默示合作。在安理会内部,中美在地区性武装冲突、地区人道危机等传统安全事项上进行协调与合作;在应对恐怖主义、贫富差距、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两国相互交流经验并达成协作;甚至在互联网世界里,中美双方的合作途径和方式也远超其间的分歧和争议。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的利益同向关系需要良性的互动合作,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也需要真正建立“复合相互依赖机制”。[13]国际法上,国际合作不仅是一项原则,也是一项义务,更是发展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内容。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美应致力于“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中美之间的合作无论是广泛的还是局部的,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持续性的,都应以国际法为依据、以民主为支撑。“在各个民族的命运深深纠缠在一起的时代里,民主与法制无论是在已建立起来的国界范围之内还是超出这个范围以外,都必须得到再造和加强”;没有民主与法制的国际合作,必然包含强权政治、强权逻辑以及强权实践等带来的恶果。[14]
二、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中的重大隐忧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遭遇的挑战
近年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首当其冲地成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中的重大隐忧。奥巴马政府虽然宣称“亚太再平衡”是一项综合战略,但实际上该战略军事安全的意味尤其浓重。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报告,宣称美国将致力于进一步削减军费,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但将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以维护亚太的安全与繁荣。同年6月,新加坡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峰会”上,美国明确提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及其推进“再平衡”的新军事战略计划。在来年的香格里拉会议上,美国表示将向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空军、陆军力量及高科技武器,以落实“再平衡”战略。美国宣称这一战略是为了保障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但中国绝对是其绕不开的话题。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该战略都具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指向性,为中美关系平添许多变数。[15]对于中美关系在亚太地区的表现,澳大利亚在2011年就提醒说:我们的领导人既不能无忧无虑地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即便超过美国,美国还能统治亚洲;同样也不能天真地以为,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会无损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16]
美国调整其亚太地区的安全政策或与近几年来的中国领土争端相关。在中国南海,越南、菲律宾等与美国关系密切甚或是美国亚太同盟成员的国家一直与中国存有争议。1994年11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后,美国就调整了对南海的基本政策,由“不介入”转为“介入但不陷入”。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被经济困境一时掩盖。但从2012年开始,南海局势升级后,美国对中国海军动向的多次表态,显示了它可以随时介入南海问题的姿态。在中国东海,日本毫无节制地渲染“中国威胁论”,不仅在教科书上大做文章、抹杀侵华历史,还对《开罗宣言》中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内容予以否定,并极力宣扬修改《日本国宪法》第9条,增加自卫权。对此,美国《2013年国防权限法案》中却明确规定,“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奥巴马政府也对此反复重申。
南海争端、东海争端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更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凸显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鉴于中美在安理会内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前述不利因素显然会给本已困难重重并一直饱受诟病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雪上加霜”。
第一,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在协调大国之间的分歧方面更加“力不从心”。冷战时期,东西阵营“你死我活”的对峙,使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一建立就陷入困境。“人们也许还记得,1983年,在有人谈及要把联合国总部迁出纽约时,美国代表团站在码头边,跟驶向‘日落地’的联合国欢喜地挥手告别的情景。”[17]冷战之后,美、苏两个大国形成的两极对立僵局一时松散,中、美、苏三角战略竞争关系也趋于松懈,但大国之间的权力政治关系并未终结。[18]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中国一直秉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对外关系方针,并依循《宪章》,关注和重视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实践和作用。[19]客观地说,《宪章》下纷繁复杂的程序要求虽然保证了由其确立的大国一致原则的实施及实施过程中的相对公正,但也使得安理会这一集体安全体制的核心机构因此而显得反应迟钝和遇事拖沓,并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为保守的机构之一”。[20]随着美国某些盟友(尤其是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它们都渴望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以求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上拥有发言权和决策权。[21]此类情势的存在和发展,都表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囊括了更为复杂和敏感的内容,使得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在协调大国之间的分歧方面更加举步维艰。
第二,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凸显更为严重的“人格分裂”。冷战时期,在安理会领导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内,不仅有东西阵营之间的严重分裂,还存在英、法、美三个西方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分歧。冷战结束后,国际权力得以重新分配,各大国的注意力也有所转移。俄罗斯不得不注重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中国则聚焦于国内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而三个西方常任理事国却在审视其在国际生活中倡导的国际主义理论和国家利益学说。西方三国之间的历史恩怨和民族隔阂及其与中、俄之间包含诸多不同内容的战略竞争关系,将其塑造成了国际政治上的一个矛盾集合体:一方面,在美国的主导下,美英法三国仍共同致力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在国内和国际一直持续努力推动政治民主,广泛传播其认定的规范性文化和普世价值,并重点将其融入中美合作事项中;另一方面,美英法三国对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也持怀疑态度,它们依然固守国家利益论的政治立场,把国家利益作为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这从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可见一斑。[22]在美国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不得不更加高度关注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比如在南海争端问题上,中国对待“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争端仲裁案”表现出较强硬的态度。而当大国各自独立的国家利益处于“上风”时,基于国际主义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则更显得“分力四野”了。
第三,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软安全”辅助办法的“工具”性质更加明显。尽管在国际社会存在着“人权碎片化”的现实,但人们必须铭记《宪章》下有关人权保护的“软安全”的重要性。[23]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办法,常设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7月正式建立、运行。它除了接手前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移交的扫尾工作外,还辅助安理会解决苏丹、利比亚、索马里、肯尼亚等国的国内局势问题,依据“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对犯有灭种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等罪行的前政要们予以通缉、逮捕、引渡和审判;[24]甚至还分别起诉了苏丹和肯尼亚的在任总统。[25]对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日本在东海、菲律宾在南海的领土主张,中国不得不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加以应对,在关涉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软安全”辅助办法的国际决策和适用方面,有时显得力不从心,更凸显此等辅助办法被西方大国予以“工具化”利用的频率和结果。正如某些非洲国家所言:国际刑事法院的做法有失公允,它已沦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26]
客观地说,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遭遇的种种挑战,都折射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中的国家核心利益分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在《宪章》下均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和义务,且仅从国家自身利益考虑,亦肯定不愿发生任何的武力冲突甚或战争。为此,两国须理性看待和运用它们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
三、中关战略竞争关系的理性运用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面临的机遇
现实当中,中美战略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双方发生冲突,相反,对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加以理性运用,推动对双方矛盾的理性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对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来说是一种积极的正能量。
首先,理性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有助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空间。由于国家主权的作用,因国家利益而起之争端,司空见惯。在中美间的各种争端中,经贸领域的问题近年来明显增加。中美两国都倡导“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以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出口为要务,从而导致在以“自由经济”理论主导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用,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皆可通过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得到解决,即使存在各自国内利益集团施压的情形,但从未演变成“贸易战”,既维护了世界贸易秩序的平稳运行,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增添了正能量。又如在2014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上,中国在安理会决议草案上的投票表决,有助于推动欧美和俄罗斯之间在这一争端上的和平解决,由此拓展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空间。未来中美如能理性处理相互间的战略竞争,达成一种可持续的战略稳定,确保做到“不冲突不对抗”,将以自己负责任的行动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典范。
其次,理性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有助于在目前缺乏规则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达成共识,进而有助于完善和健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不是一种抽象的法律规范或者法律体系,而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它通过主体按照法律规范要求的法律行为建立法律关系,最终达到社会生活法律化的有序状态。但“法律如果对社会变化视而不见的话,法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最终法律必然会成为破坏秩序的罪魁祸首”。[27]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理性运用,需要它们共同就地区海洋关系、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等问题通过谈判达成相应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准则,由此减少或防止潜在的双边冲突。仅就海洋领域而言,美国应寻求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中国则应尽可能推进起草与东盟关系的原则、规则。有智库研究报告也认为,两国应在亚丁湾双边海军合作以及美方向中国海军发出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邀请的基础上,促进更深层次的海洋合作,为制订解决争议和避免危机的新的规则和指南奠定基础。[28]当然,任何规则和制度的设计、谈判、达成和适用都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都必然带有“时代烙印”。中美在存有分歧的问题上应摒弃“零和博弈”的安全观念,为两国间那些正在走向社会化的国际问题制定规则,进而推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法律秩序的健全发展。
再次,理性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增加了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民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增强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力和能力。虽然中美之间在短时期内还不能达到“实力均衡”或“势力均衡”,但中国在各方面的努力正使中美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29]尽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一时置于危险边缘,但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两国不仅有交叉的国家利益,也有近似甚或共同的国家意志。此类情势,或可表明中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的共同需要。中美双方已认识到现有“自我克制”的缺陷和不足,并正在尝试通过对话达成两国在竞争中进行合作的原则、规则、制度及相应的运行机制,包括战略与经济对话、法律交流、人权对话、海军互访、海洋法与极地事务磋商等,以求降低甚至消除双方对彼此战略目标是否威胁各自关键国家利益的误解和紧张,并能相互尊重彼此的外交政策及依照国际法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中美双方在各种对话或交流中虽常存有分歧和激烈辩论,但“关起门来的言辞交锋远好过门外的武力战场”。中美以协商方式处理双方间的矛盾,显示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在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协调中逐渐增强的国际民主性。国际民主因素的持续增加显然会降低国家利益的不确定性,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会变得相对公正和透明,藉此会大大增强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力和能力。
另外,理性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有助于解决地区性的具体问题,进而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平等与发展问题,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暴力冲突源于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贫困。“随着不平等愈演愈烈,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受到压力、不堪重负,这往往导致经济和社会的日益不稳定,甚至引起动乱。”[30]但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理性运用,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了曙光和希望。在索马里,自1991年以来的国内战乱导致了政府缺乏管理、法制机构薄弱、贫困饥饿常见,其累积效应使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2014年1月,美国向索马里派遣军事顾问和教官,与非洲联盟维和部队协调打击索马里最大的反政府武装“伊斯兰青年运动”;而中国则向非盟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提供物资援助,并通过其他形式的经济援助,缓解当地饥饿和贫困问题。在苏丹,自1956年独立以来,国内政局一直动荡,饥饿和贫困问题更不能及时得以解决。与苏丹关系恶化后,美国自1993年起就将其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并单方面对其实施长达20年的经济制裁;而作为中国重要的原油供应地,中国给予苏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援助有助于解决当地贫困,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危及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紧张局势。在这一具体问题上,中美两国采取的是不同的策略,中国的积极参与给问题的缓解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必须承认,当今的国际形势已不同于70年前,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效用也应与70年前的有所不同。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建立在大国关系的基础上,对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理性运用,有助于提高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效率和质量。
其一,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应充分发挥中、美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影响,推动建立和平与安全的国别报告制度,敦促会员国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根据《宪章》,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理会,但这并不能减少甚或否定会员国的相关义务。[31]自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建立以来,尽管没有发生像一战和二战那样席卷全球的大规模战争,但局部的、区域的危机情势时有发生,这往往与会员国不履行《宪章》下的义务息息相关。[32]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发展援助,对地区乃至国际和平施加了较多的“软性”影响;而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军事部署,为区域乃至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了诸多的“硬性”影响。朝鲜于1991年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法律事实,并没有使朝鲜半岛笼罩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光芒,甚至为了进行核试验与核武研发,“拂袖”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解决机制,则凸显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中的“软”“硬”因素对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影响。诸如此类的种种考验和契机表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应充分发挥中美各自的比较优势,推动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别报告制度,在法律上要求那些存在国际争端的会员国向安理会提交年度报告,重点阐述其为解决争端而采取的措施,督促、鼓励会员国能更好地承担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其二,处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中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应重新审视区域办法与全球办法之间的关系,明确界定临时性区域办法的法律地位,预防大国的单边措施升级为区域办法的可能性。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全球办法并不排斥区域办法,但须要明确界定区域办法特别是临时性区域办法的法律地位,它关系到区域办法用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程度、范围。根据具体取得方式的不同,区域办法的法律地位可分为自动取得和主动取得两种。在第一种方式下,根据《宪章》,所有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无论其功能或性质,只要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目的,均可被承认为区域办法;其存在和利用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不得妨碍安理会的职权,如无安理会授权,不得依其采取执行行动,而对于已采取或正在考虑之行动,应随时向安理会充分报告。[33]但是,第二种方式的取得及其与全球办法之间的关系,《宪章》未有任何明确规定。从国际实践看,全球办法和区域办法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经常错位,因参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实而主动取得法律地位的临时性区域办法也司空见惯。2013年朝韩“天安舰”之争,引发了朝鲜半岛新的紧张局势,而美、韩违背安理会一致通过的《主席声明》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则使东北亚的局势更加动荡。[34]2014年乌克兰危机,凸显“多边组织合作的潮流中出现类似联盟性质的集团对抗,对欧亚大陆影响范围的‘争夺’也更加激烈”。[35]尤其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上,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它涉及多少国家、无论其内容多么丰富,它归根结底都是美国的单边措施,在法律上或实践中决不能升级为维持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区域办法。
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是为了防止另一场战争的发生,在这一点上已取得成功。尽管地区性的大屠杀和武装冲突时而再现,但如果没有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存在,过去的岁月可能会有更多更重的血腥。70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已毋庸置疑,它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于大国之间的积极协调与合作,它遭遇的种种危机也源自大国之间的消极对抗与冲突。
就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而言,尽管两国在政治理念层次存在明显差别,但在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时,两国之间的政治分歧显然应置于次要地位。[36]建构主义的利益理论解释了国家在进行多边或区域合作时行为或政策选择的深层次原因,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驱动模式,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谈判解释模式,而是国家在互动中合作身份和利益重新建构的动态解释模式。[37]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不仅反映了国际权力结构的新变化和国际秩序的新情况,更意味着已运行了70年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对人类来说,安全的需要高于一切。面对当今全球相互联系的利益以及通过这些联系而产生的复杂威胁,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需要在财富创造与稳定发展之间寻求平衡。仅靠单一的民族国家是不能够保障这种平衡的,它必须通过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来实现所有国家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利益最大化,进而为财富创造和财富分享提供安全环境和安全保障。安全利益是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基础,如果中美能妥善处理双边安全关系并将其推而广之适用于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可以预见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未来的能力建设、健康发展和效用质量。
注释:
[1]《联合国宪章》序言及第1.1条。
[2]See Richard Falk,“Glob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in Mary Kaldor and Iavor Rangelov(eds.),The Handbook of Global Security Policy,West Sussex:John Wiley & Sons Ltd,2014,p.321.
[3]参见李巍、张哲馨:“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第31-32页。
[4]冷战之后,随着国家之间武装冲突的减少,产生了某些真空地带,在全球化的作用下,跨国犯罪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其增长速度远高于合法的世界贸易。See John Robb,Brave New War:The Next Stage of Terrorism and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Hoboken:John Wiley&Sons,Inc.,2007,p.5.
[5]参见温斯顿·丘吉尔著,张自谋等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0-11),译林出版社,2013年。
[6]Richard D.G.Crockatt,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Vol.1-5(United States),Series C:North Americ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9.
[7]Richard Falk,“Glob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in Mary Kaldor and Iavor Rangelov(eds.),The Handbook of Global Security Policy,p.321.
[8]See James S.Brady(Press Briefing Room),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Ukraine,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3/17/statement-president-ukraine.(上网时间:2014年3月18日)
[9]Jure Vidmar,“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the Law of Statehood”,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697,Feb.2012,p.706.
[10]参见肖佳灵:《国家主权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497页。
[11]Shirley Scott,“Looking Back to Anticipate the Future: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Era Of the United States”,in Rowena McGuire and Charles Sampford(eds.),Shifting Global Powers,Oxford:Routledge,2013,pp.12-26.
[12]《宪章》第2条。
[13]参见李巍、张哲馨:“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第48-50页。
[14][英]戴维·赫尔德著,胡伟等译:《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15]参见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编:《战略评估2012》,2013年4月,第19页。
[16]See Peter Hartcher,“No Reason to Get Even Closer to Uncle Sam”,Sydney Morning Herald,Nov.15,2011,p.16.
[17]Peter R.Baehr and Leon Gordenker,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1990s(2nd ed.),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4,p.97.
[18]Ashok Kapur,Regional Security Structures in Asia,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pp.42-47.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6页。
[20]Susan C.Hulton,“Council Working Methods and Procedure”,in David M.Malone(eds.),The UN Security Council: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21st Century,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4,p.237.
[21]日本一方面大肆呼吁安理会改革,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援助扩大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甚至抓住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中亚地区的政治空窗期,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推行“丝绸之路外交”(Silk Road Diplomacy),谋求更多中小国家的支持。See Nikolay Murashkin, “Japanese Involvement in Central Asia:An Early Inter-Asian Post-Neoliberal Cas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Vol.43,No.1-2,2015,pp.52,75.
[22]参见[法]让-马克·夸克著,周景兴译:《迈向国际法治:联合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回应》,三联书店,2008年,第127页。
[23]Linda Carter,“The Global Impact and Implementation of Human Rights Norms:Introduction”,Pacific McGeorge Global
Business &Development Law Journal,Vol.5,2012,p.24.[24]See in detail S/RES/1591(2005),S/RES/1970(2011),S/RES/1844(2008).
[25]See in detail The Prosecutor v.Omar Hassan Ahmad Al Bushir,ICC-02/05-01/09;The Prosecutor v.Uhuru Muigai Kenyatta,ICC-01/09-02/11;and Decision on the Withdrawal of Charges against MrKenyatta,March 13,2015.
[26]See http://www.un.org/en/ga/69/meetings/gadebate/24sep/chad.s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5日).更有意思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强烈措辞谴责朝鲜长期存在的蓄意和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欢迎联合国大会将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递交安理会,并呼吁将朝鲜人权问题转交国际刑事法院。See in detail A/HRC/2R/L.18.
[27]李龙主编:《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
[28]参见“中美智库联手发布报告中美如何建构新型大国关系”,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2/24/c_119472726.htm;“基辛格: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充分认识合作的重要性”,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5-03/21/c_1114718130.htm.(上网时间:2015年3月25日)
[29]关于中美之间差距的表现以及中国的国际实力和国际权力的具体分析,详见王文峰:“中国实力地位与国际环境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6期,第3-6页。
[30]Secretary-General""s Message for 2014 World Day of Social Justice,http://www.un.org/en/events/socialjusticeday/2014/sgmessage.s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0日)
[31]详见《宪章》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
[32]See http://www.un.org/apps/news/newsmakers.asp?News-ID=108.(上网时间:2015年3月20日)
[33]详见《宪章》第34和第35条。
[34]See in detail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S/PRST/2010/13.
[35]高飞、张建:“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大国博弈及其对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6期,第96页。
[36]Sungmoon Kim,"Public Reason Confucianism:A Construc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9,No.1,2015,pp.194-196.
[37]See in detail 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Technology and the Logic of Anarch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9,No.4,Jan.2003,pp.536-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