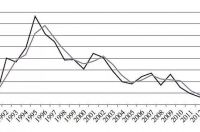原编者按:我们应当客观地对待长期以来演化成形的圈层本位意识系统,既要看到它在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上的稳定器功能,看到它对中华文化的推进作用,同时也应防止小圈子文化导致的小团体主义和山头主义,纠正以升官发财的不当政绩观。但无论如何,只有认识到这种隐性圈层本位,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文化,限制其弊端,吸纳其它优秀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亲密性与权威的分配
任何组织、民族和文化都要分配两种关键性资源:一种是亲密关系,一种是权威、权力,前者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后者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纵向关联。每个个体都需要在这种亲密关系和权威关系纵横交错的关系网中迅速定位,以避免不确定性和个体性带来的无助感和焦虑感,获得安全感和支配资源的恰当能力。
古希腊的雅典对亲密性和权威的分配主要依托商业契约以及公民身份,与之不同,传统中国社会分配亲密关系的主导原则是以血缘关系和拟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关系本位,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圈子”,而分配权威和权力的主要原则是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的官本位,也就是官僚制度(中性词)。“本位”有“原来的官位”之义,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复位而待”;亦可指原来的座位、原来的身子(佛教用语)。在这里,“本位”是指事物的根源,也就是以某物为基础展开逻辑陈述。
关系本位和官本位都是一种高级价值导向,其根基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共同形成的实体规范,农耕文明与治水文明是形成这两种社会规范的深层基础。传统中国人特别重视自己在圈子所处的位置以及所感受到的被圈子成员接纳的程度,一旦失去在圈子里面的位置,个人支配社会资源和享受福利的水平就有可能下降,个人就会非常焦虑和不安。因此,传统中国人最怕欠人情、丢面子,希望通过拉关系来让自己感到身心安全。同时,传统中国人也特别重视自己在官僚体系中的位置,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特征决定了个人如果想要追求更大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就需要不断地按照等级的规则一步一步向上爬。例如,宋真宗曾经写出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等来劝导世人好好读书,读书目的是为了中举做官,然后才有富与贵,这也成为维系传统文人精神追求的精神食粮。
关系本位与官本位两种系统的观念形态虽然并不一致,但二者往往以互相配合或者互相斗争的面目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传统中国历史经纬线。历史上关系本位与官本位之争的焦点在乡镇,皇权到底该不该下乡镇,就成为一个焦点问题,二者之争的另外一个焦点是圈子大还是官僚制度大,圈子的异质性与官僚命令服从的同一性往往存在冲突。当年燕王朱棣拥兵自重,入朝不拜建文帝,一位大臣认为:“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当各种圈子威胁中央集权之时,关系本位就受到打击,但同时官本位由于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太高,不可能将触角伸到社会任何一个细胞里,因此,还需要关系本位配合,于是,就形成了圈层文化现象。我们将圈子文化和官文化合称圈层文化,圈层恰好定义了圈子的特征,同时也定义了官僚制度层级特征。
就传统中国社会而言,无论是圈子规则还是官僚制度,都有一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圈子希望不断扩张,官僚也希望自己不断膨胀,扩张的本质是大量剩余劳动剥离了生产系统,进入了非生产系统,制度维系成本巨大,象征性符合生产过多,反而抑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创新,甚至有些物质投入到皇陵等奢侈性投入中去,浪费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合理利用剩余劳动并对之进行有效积累,才能促进社会生产的巨大进步。
但正如任何有机体组织一样,其扩张都有一定的限度,圈子和官僚的扩张也是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投入到圈子或官僚中剩余劳动不能再被社会承担。毕竟大量的剩余劳动投入到生产系统领域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经济的扩张,大量的剩余劳动耗费在制度、官阶以及圈子生产中,就会导致社会经济扩张的停滞。
传统中国社会构建亲密性的原则是关系取向。致力于研究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黄光国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关系取向’的民族”,“人情、关系和面子是衍生自传统中国文化的一套社会机制……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可以说是孕育‘人情文化’的温床”。[1]人情、关系和面子,似乎是每个人传统中国人都能够深刻体悟到的概念,这根源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导向的社会。
传统社会以个人与他人关系的远近来识别应当采取的行动原则。个人、家人、熟人到最外层的陌生人形成一个人的关系网络。谙熟传统关系趋向的传统中国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评价一件事情和行为并没有固定的标准,隐藏的标准是“谁做得事情,这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如何”。整体的原则是对待熟人以内的圈内人,采取的是一套讲究伦常和人情策略,而对于陌生人往往采取冷漠的态度,最近家长教育小孩时还常常强调,“不要与陌生人说话”,对待外人可以不讲人情,不讲公正。
人情关系的基本法则是“你给我人情,我也会还你人情”,也就是说,人情是关系社会中一种资源交换的手段。一个人的关系网络越大,自己的地位越高,越有面子,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往往越有利,因此,人人都要做足面子,如果人情账没做好,就会被别人视为不给人情,或不给面子。人情也可以作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手段,这就是走后门和搞关系盛行的根基。在人情社会中,资源越稀缺,搞关系就越盛行,真正能够在市场上随意买到的资源或商品,就不需要搞关系或者送礼。
一般来说,关系趋向主要有五种关系:一是血缘关系主要是宗族关系和婚姻关系;二是地缘关系是同乡关系,三是朋友关系,四是师徒关系,五是通过仪式获得关系,例如干亲、收养等。由此可见,关系本位是以血缘关系和拟血缘关系(同乡、干亲、战友)等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的核心载体是家族。“世代定居的农业生产与生活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以血缘伦理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组织是构成传统社会的细胞”。[2]
为什么传统中国分配亲密性资源要以关系本位为取向,这与中国先民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
我们分析文化可以从以下三个基本维度进行分类:基本假定、价值观或信仰以及行为规范。所谓基本假定,其实就是群体对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看法;所谓价值观就是什么是有用的,对自己的用处有多大,如何进行价值排序,也就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行为规范就是基于基本假定和价值观基础之上行事准则、制度等规范和行为表现。例如,一企业把手机视为语音通讯工具,这是基本假定,他的价值观就是“技术至上”,他的行为规范就是保障语音技术最大化的条件,寻找最好的技术和开发工程师;另一企业将手机不仅仅视为语音通讯工具,而视为上网、购物、游戏等功能的终端工具,他的价值观就是创意至上,他的行为就是不断从消费者那里获得建议,从而不断开发新的价值和新功能。前者是摩托罗拉、诺基亚的思路,后者是苹果、小米的思路。
同样,分析关系本位的文化也可以从这三个层次分析:关系本位趋向的基本假设层是基于以下认识:中国传统社会是定居农业的生产方式,由于土地的固定性使得农民被黏在土地上了,而且他们从事的活动基本上种植业,打猎和畜牧业逐渐萎缩,“不耕获,未富也”(《吕氏春秋·贵当》),再加上统治阶层鼓励耕稼,例如,“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汉书·文帝纪》),中原农业文明逐渐被强化成为民族自发的意识,随着中原文化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导,这种意识在历史上一再被强化。
黑格尔认为文明是有三种主要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地和平原往往产生畜牧业的文明,巨川大河流过的平原往往是农业文明的基础,而与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形成工商业文明,中华文化虽然以海为界,但却没有和海洋发生积极的联系。[3]尽管我们认为这种地理决定论实际上偏离了问题的核心,但也不得不承认一点:中华文化确实在后来的屡次海禁中丧失了海洋霸权的追求意识。
这种定居农业生产方式所需要知识、物质以及交往可以从家族和熟人社会中取得,农业社会所需要技能和知识是一种实践性和经验性知识,因此经验就很重要,这些经验知识在长老、长辈那里可以学到,因此,个人要想生存,就需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自己的交际圈。这个交际圈具有封闭的特性,晋《帝王世纪》记载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传统农业社会下先民生活封闭的特征。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们养成了强烈的家族本位,一个人首先是家族成员,其次才是社会成员。
在这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人们发现家族、朋友以及其它拟血缘关系的纽带就很重要。自己要想生活得好,就需要正确处理与他们的关系,定好自己的位置,尽自己的义务以获得圈子的认同和庇护。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其中仁义又是最基本的价值观。“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从亲情出发,人心才能有依靠,才能消除对于陌生人焦虑。
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规范表现为儒家所设定的三纲五常等礼教内容,君子就是要学习这些三纲五常,从而能够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于是,人情、面子以及世俗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伤了别人面子不是伤了一个人的面子,而是一个家族或者团体的面子,不近人情不是伤了一个人的自尊心,而是伤了整个圈子的自尊心。
圈子文化的核心就是关系本位,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个圈子构成的社会,圈子社会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派别主义,对于圈内人与圈外人的所采取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导致中国社会在一个表面的中央集权统治下,形成不同的利益圈子。一旦自上而下的官本位系统失去功用,或者遭遇到了“斩首”行动,圈子之间的冲突就显现出来,群雄并起,狼烟遍地,容易被外族各个击破,从而导致王朝覆灭。有句话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是条蛇,三个中国人是条虫”,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这与西方文献研究中国文化集体主义导向是否矛盾?一些学者发现,集体主义也可以分为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纵向的集体主义包括作为集体的自我感知和接受集体不平等的一部分,而横向的集体主义包括对集体的自我感知,但视所有的成员都是一样的,强调成员的平等。[4]中国的圈子文化中显著特征是不同人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横向的集体主义水平不高。陈等人发现中国企业中的纵向集体主义者是支持奖赏改革的,而横向集体主义者则倾向于反对奖赏改革。[5]根据关系本位的解释是中国所谓显著的集体主义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所外显的特征,而横向的关系本位则的支配逻辑则是以亲疏远近来决定是否团结一致。山头主义和“窝里斗”共同决定了圈子文化横向集体主义不高的特征,圈子之外的陌生人不再适用伦理法则,一旦党争起来,特别是残酷,例如,明末的阉党与东林党党争,直接导致整个明王朝官僚运作体系失灵,也是我们文化中一个重要缺陷,这个缺陷的制度基础是产权不清晰,个人主义被家族主义压制。西方启蒙思想核心是推倒了“神”而树起了个人在社会中地位,而中国近代启蒙的一个重点是将个人从从族权中解脱出来,所以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民主解决的是个人的社会地位问题,科学解放的是人的心智问题。
3、权力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官本位
中国传统社会分配权威和权力的取向是官僚制度。德国大思想家韦伯曾惊讶于中国传统官僚体制的庞大,确实,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即官本位是中华文化的另一个文化基因。《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传统中国社会由权力的上下关系来确定人的位格,从而达到“定纷止争”的和谐社会目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胡佛认为,“这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集体生活观,对全盘社会生活来说,即构成社会秩序的主轴”。[6]
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强化,追求官本位是世人价值导向。所谓官本位,其核心是在命令服从体系中寻找更有利于自己和圈子的位置,从而支配社会资源。其基本假设是越是在命令服从体系中具有有利的地位,其支配的资源越大,对自己和圈子有利。
官本位的基本价值导向是步步高升,直到权力巅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的目的是出仕,获取官位和俸禄。“不管哪个时代,人们如何划分职业,结果有何不同,但有一点,所有划分都是不谋而合,那就是无一例外地把‘官’放在第一位。”[7]
官本位的基本行为规则就是追求官阶、俸禄、特权以及名誉的最大化。秦皇借郡县制之利席卷六国统一天下,他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官员不能世袭而只能选任,秦虽二世而亡但这一选择影响后世。
官本位生成也有其历史根源,除了农耕文化之外,中国文化被人称之为“大河文明”,德国裔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于1957年发表《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书,他认为东方社会的形成与治水密不可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需要一个统一性的全国组织,而君主制由此而形成。中国专制主义成因很复杂,魏特夫的解读或许有其偏颇之处。然而,因大河而治水或分水的逻辑确实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成的重要线索。影响海洋变化的动力是多元的,例如地球、月亮和太阳等等,但控制大河水流动力因素主要是地球引力,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中国大河与散向四方的欧洲不同,黄河、长江以及珠江等水系主要是自西向东流入大海。这种水系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是文化和政治的大一统的基因”。[8]大禹治水就是中华文明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此后历代统治者修筑运河,很多古老的城市依水而建,都是在某种程度回应了种植业的生产方式的诉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家》一书中也认为水利工程与和建筑工程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官僚制的发展。
即使到了现代,很多地方因天干地旱引起的分水纠纷还很多,至于排洪泄闸更是事关种植业收成的重要事件。治水之所以成为治国逻辑,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治理河殇,就需要一个至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以便从整体上协调各个家族、部落、诸侯、地方之间不同的利益和意见。从历史上看,大禹以治水开国,其子夏启建立了家天下的命令服从体系。家国同构的金字塔体系,随着秦皇建立的郡县制随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根本保障,中央集权下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与关系本位即互相排斥,又互相结合,也是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根基所在。
水对于农业很重要,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楚简《大一生水》说,“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治水逻辑与治国逻辑类似,《管子·水地》说,“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人心正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治水是圣人眼中的治国之谜和中枢,由此可见,治水对于传统社会治理非常重要,河患不除,天下动荡,治水不当,也会导致诸如元末红巾军起义等事件。
命令服从体系的官僚制度的优点是能够形成统一的意指,防止由于关系本位导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分裂,从而构建一个天下太平与可以持续发展的社会,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追求的核心价值。政治的统一,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也是中华文化得以传言至今而不绝的重要原因。
然而,其弊端是由于执行和监督成本很高,往往导致官僚体系的内卷化,即大量的社会剩余劳动投入到官僚体制生产,从而剥离了社会生产领域,对于社会发展不利。一旦官僚的决策层出现重大失误,其产生的危害也是系统性的,往往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和王朝的更替。大量的精英阶层都期望进入仕途,结果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科技和文化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由于竞争激励以及体制弊端,贪污和腐败严重扭曲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不公正现象。这种追求官本位的现象,也带来了另一大问题:由于大量的知识分子只读圣贤之书,实践能力严重匮乏,在民族危亡之际,不能组织群众和协调指挥,只能以死报君恩。
关系本位与官本位一个是治理社会的纬线,一个是治理社会的经线,经纬有交叉但又明显不同,共同生成了传统社会治理的文化大网。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如果一个文化匹配并放大了一个民族的优势,就会推动这个民族前进,而当这种基本假定、价值观念和行为逻辑与规范得到进一步确认,就会成为统治者和民众共同信仰的理论从而加以强化。一种制度只有适合了民族心理而不是违反群体成员的自然倾向,才能会被真正的执行。商鞅变法成功的核心关键是通过系统化和权威化的方式整合了秦国文化,其中有一条就是放大了秦国人好战倾向,并制止他们内战倾向,而不是违背这种天性,所以大秦能够一扫六合而定天下。但当大秦将这种成功的模式用以统治天下之时,过去的辉煌强化了权威而忽视社会横向制度构建,即构建关系本位以配合这种刚性统治,结果就是二世而亡。
关系本位与官本位组织原则是不一样的。关系本位目的是分配亲密性资源,它的目的是扩张自己所在圈子的影响力。对待圈内人的原则与对待圈外人的原则存在巨大差别,熟人之间要奉行伦理规范,而对待陌生人或圈外人可能无需考虑这些伦理规范,甚至可能伤害圈外人的利益以获得圈子内的利益。对待一件事情应当与否的评价,不是根据统一性的原则进行评判,而是根据亲疏关系进行评价。圈子文化的这种特质就形成了古代中国大大小小的圈子,圈子与圈子可能“老死不相往来”,为了圈子利益,可以与其它圈子无底线械斗,这样,在大一统的背景下的社会随时都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一旦官僚系统运作失灵,或者君主失位或外族采取斩首行动,整个帝国就很可能陷入无政府的械斗状态。军阀林立,圈子党争不断。官本位的目的是追求在官僚等级中的地位,从而扩张自己支配社会资源和支配他人的特权。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遵循的不是圈子文化那种异质性原则,而是统一命令服从原则。上位决定下位必须执行,下位的命运主要攥在上位手中。因此,权力分配原则是决定命令式的。但是,这种直线型的命令服从体系毕竟是刚性的,上位并不一定都是上帝,下位什么信息都能获得,因此,发布命令可能会是错误的,执行起来就会造成系统性风险,再说,命令的执行与监督、评价都需要大量的成本,一旦大量的社会资源都用于等级结构的再生产,而非生产系统的扩张,甚至将大量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剩余劳动、资源都剥夺出来,维系越来越内卷化的官僚等级再生产,整个社会生产系统就可能停滞,导致经济危机。或者活不下去的失地农民就会揭竿而起,打碎这个越来越庞大而难以有效运转的官僚体系;或者是是统治阶层自发地进行官僚机构改革,清除冗官冗兵的畸形状态,但改革往往也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关系本位与官本位存在巨大的冲突,在秦汉时代表现为分封制与郡县制之间的斗争,在后世表现为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中央集权往往要求天下政令“令行禁止”,避免政令出不了皇城,而地方藩镇或诸侯王、官员往往为了自身利益,而有割地自立的倾向。为了清理圈子内权威命令针插不进去的现象,通过迁徙来达到拆散圈子扩张的中枢,通过烧其家谱、族谱来削弱血缘关系带来的凝聚力,战争、内动也往往会客观地削弱这种圈子关系的力量。通过一系列削弱圈子的策略,王朝朝廷牢牢建构了强大的权威政府体系。由于分配亲密关系也是社会重要任务,因此,官本位不可能彻底清除各种各样的关系本位。关系本位在传统社会中既是一种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分配亲密关系的,同时也是生于斯的文化培养的结果,儒家经典系统化地描绘了什么样的关系是恰当的,什么样的关系是不当的。
关系本位与官本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互补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社会的意识主流。更重要的是,关系的质量和数量决定着权力的高度和深度,反过来也是如此,形成一个双向反馈体系。“外儒内法”就是描述这种现象,关系本位构成了人与人之间横向的联系原则,这种圈子文化主要是受到儒家经典指引的,而官本位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纵向关联,这官僚文化主要依靠典章法律来维系的,但二者往往是互相渗透的。例如,处于权力顶峰的皇帝虽然可以金口玉律,也要受到祖宗家法的制约,受到儒家礼法的规范;而家族成员在家要遵守家规,在外要遵法守纪。正如硬币两面要通过侧面来链接一样,儒法之间还需要佛道等修心,治理社会心理问题,才能使得关系本位与官本位达到某种平衡。有时候在关系本位与官本位淘汰出来的个体,在经历宦海沉浮、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后,也需要看破红尘,寻找一种心理治疗的药方,信仰主义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当然中国传统的信仰主义不如西方信仰主义那么强烈。
总之,基于农业定居方式和大河治理基础之上的圈层本位是影响中华文明圈的隐性线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反馈和强化,尽管中华文化在长期与外来文明不断碰撞融合,并吸纳了外来文化的净化,然而圈层本位的两大隐性基因还是展现了其特有的稳定性。同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逐渐削弱圈层本位,例如,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现代政治制度的改革,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圈层本位的导向。
我们应当客观地对待长期以来演化成形的圈层本位意识系统,既要看到它在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上的稳定器功能,看到它对中华文化的推进作用,同时也应防止小圈子文化导致的小团体主义和山头主义,纠正以升官发财的不当政绩观。但无论如何,只有认识到这种隐性圈层本位,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文化,限制其弊端,吸纳其它优秀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