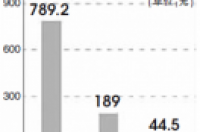——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梳理
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激烈而丰富的变革,表现于文化领域,乡村社会历经了文化冲突、文化改造、文化整合等过程。从“国家-社会”关系纵向演变的视角来看,本文将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传统国家-社会关系转型时期、国家对农村社会高度整合时期和国家体制性权力退出后的乡政村治时期。本文主要就上述三个时期农村文化的变奏与调谐作学理上的梳理,以期能够为农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乡土化”提供历史视野和构建背景。
20世纪初,中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随着国家对乡村整合的加强,国家行政权力开始下沉,农村传统的文化格局、文化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张力、冲突逐渐显现。学者们对即将发生变革或正处于变革中的农村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角度:一是剖析传统乡村文化特质,探讨文化转变动向;二是研究乡村社会中乡民的反抗行为及抗争性文化;三是研究国家与乡村社会文化衔接机制的变化。
费孝通、梁漱溟、毛泽东从儒家思想所构建的乡村社会文化特质出发,剖析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特点。他们认识到随着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传统乡村社会的变革不可避免。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靠“礼治”来维持,是“无讼”社会。随着国家强化自身权力、向基层吸取资源过程的推进,基层秩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费孝通提出基层社会的衰败。后礼治时代的农村文化将朝向哪个方向发展,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一种是改良说,以梁漱溟为代表,期望通过重建乡村伦理文化,来实现农村秩序的好转。梁漱溟将中西方文明进行对比,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伦理本位,“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1]37。梁漱溟把20世纪前半叶中国乡村社会衰弱与混乱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文化失调,他指出中国农村社会要改变落后愚昧的面貌,应从重建农村伦理文化入手。另一种是革命说,以毛泽东为代表,力图通过暴力革命来打破束缚农民的封建主义枷锁。毛泽东从传统社会的封建宗法思想对农民的压制出发,指出“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2]31。毛泽东通过考察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权力,得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的策略指针。
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民间秘密会社纷纷建立,透过秘密会社研究农民的抗争性文化成为学者探讨农村文化的一个视域。学者们对农民抗争性文化的研究,大体有以下四种观点,即地方生存策略说;农民觉醒说;倒退说;政权认同说。
一是地方生存策略说。裴宜理用“地方性生存策略”[3]248-271诠释农民的暴力行为。她认为农民武装组织的反抗模式是以传统乡村生活为背景的集体暴力形式,因此它所表露的行为逻辑和价值观是实际的、狭隘的、保守的、具体的,具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农民集体暴力的传统性还表现在他们反抗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是宗教习惯和传统习俗。就农民集体暴力的发展方向而言,裴宜理认为农民的反抗运动是出于一种地方生存策略,自卫性和排外性明显,具有“外力难以侵蚀的韧性和弹性”,难以转化为更具革命性的集体行动模式。
二是农民觉醒说。陈独秀、李大钊在组织农民运动时期,对华北一带的红枪会尤为关注。他们认为红枪会运动虽然具有某种“落后”的特征,但它证明中国农民已经觉醒了[4]564-570。陈独秀分析了传统农民暴力的价值观,“任何民族中封建社会时代的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不免有顽旧迷信的色彩,他们的行动往往偏于破坏而不免于野蛮,这本是落后的农民原始暴动之本色”[5]322。他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传统农民运动的局限性可以转变为行动的力量。
三是倒退说。张鸣选取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站位,指出红枪会现象出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背反,它“不仅没有导致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反而激出向后转的反弹”。张鸣认为红枪会在组织形式、口号和意识内涵上都是极端落后的,红枪会是“以现代化为背景的政权强化与武力强化在农村结出的恶果”[6]68。
四是政权认同说。杨焕鹏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出发认为“农村秘密会社在乡村的兴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权强弱及乡村民众对政权认同的程度”[7]。杨焕鹏认为军阀政治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较为严重,乡村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乡民对政权认同弱化,农村秘密会社最盛。
学者们对农村秘密会社和农民抗争行为的看法不一,褒贬各异。总体来看,学者们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一是承认农民的主体性,农村中潜藏着力量和智慧;二是农民的“反抗哲学”存在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与乡土社会孕育的乡土文化密切相关。
传统“国家-社会”关系转型中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与乡村社会文化衔接机制的变化,在这一方面学界的研究成果突出。学者们的研究旨趣主要有以下三类:一类是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强调宗族观念、传统信仰与惯习在国家-乡村社会关系中的作用。黄宗智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出发分析了20世纪前半叶国家政权不断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两种不同类型村庄的文化样态。一种类型是紧密的村庄共同体,它们在外来压力下宗族观念、传统信仰与惯习等文化因素成为构筑村庄内向集合体的心理基础。村庄在对付外来威胁时会“封闭”为一个武装共同体。另一类型的村庄阶级分化和小农半无产化程度高,宗族关系趋于崩溃,宗族组织和传统习俗趋于消失,村庄共同体趋于解散。这类村庄在面临外来威胁时会分崩离析,易于被不轨之徒僭取村内政权。
研究国家与乡村社会文化衔接机制的第二类角度是以张鸣为代表的关注文化权力阶层在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中的功能。张鸣在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野下,讨论了国家政治催化下农村传统文化权力阶层的变化。张鸣指出清末新政废科举兴新学,剪断了乡村社会与国家相联结的政治文化机制,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农村社会中“士”阶层的陨落。优秀人才从乡土社会流走,而留在乡村的精英呈现劣化迹象。传统乡绅在乡村的地位衰落,加剧了农村传统文化秩序的瓦解[6]46-47。
还有一类也是学者们讨论较多的角度,是着眼于农村社会的文化网络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以杜赞奇、李怀印等为代表。杜赞奇以华北农村为例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在基层乡村丧失合法性的原因,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内卷化”2个核心概念。杜赞奇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对农村传统文化网络的不恰当处理,造成了“国家权力的内卷化”[8]180。李怀印聚焦华北地区的河北省获鹿县,他的研究认为20世纪早期国家政权建设中,外加制度的话语霸权与乡民传统观念的辩护力一直处于互动之中。国家需要依赖具有凝聚力的农村社群以减缓国家与地方当权者的合法性危机[9]314。通过对获鹿县农村的考察,李怀印得出了不同于杜赞奇的结论,即冀中南农村并未出现明显的“国家政权内卷化”。二人迥异的研究结论恰恰证明了同一个理论命题,即地方文化网络对于国家-社会关系具有衔接作用。村庄的地方文化网络的紧密程度不同,国家对社会整合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到,学者对传统国家-社会关系转型中农村文化的研究,虽考察村庄不同,分析角度各异,但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农村文化格局的架构中宗族家族观念、传统惯习与信仰、农村文化精英,以及以上要素所构织的农村社会文化网络的作用尤其重要。国家政权建设是否顺利,文化整合是否成功,这些因素都是不得不考虑的。
在中国真正将农民带入国家政权体系的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政权深入农村后,深刻影响了农村的文化权力,就这一点学术界有过广泛的探讨。总体而言,学者们从三个角度探讨国家与农村社会的高度整合所带来的农村文化的变革。
第一个角度是讨论国家政权建构下国家整合方式和强度的变化。徐勇从国家政权建构的角度讨论了共产党“政权下乡”后,政治整合与文化整合相辅相成之下,给乡村社会带来的纵深影响。他指出,通过土地改革,共产党的政权组织第一次真正地下沉到乡村,而且摧毁了非正式权力网络的根基。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农民社会前所未有的国家化了。人民公社在农村建构起了功能性的权力网络,使农民感受到国家的“在场”,离散的乡土社会被高度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来[10]140。张鸣认为共产党通过革命将农村的文化权力结构打翻,农村丧失了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功能,经济能力和文化资源的缺失使得农村对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依赖加大,“群众运动”成为党和国家调控农村的最有效的手段[6]5。
第二个角度是考察国家高度整合对农村的社区文化、社群观念的影响。黄树民从一个特殊人物叶文德书记生命史的角度叙述福建林村的社会文化变迁。黄树民认为,国家对村庄政治文化改造中有“一种全国性文化明显抬头。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慢慢被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11]171-174。李怀印通过讨论1949年前后华北农村非正式制度运行的差异,认为1949年以后,农村集体化时期,土改和农业合作社运动涤荡了农村社群的权力结构、村社准则和群体观念,国家史无前例地渗透到农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全方位地对农村进行整合[9]314。
第三个角度是关注国家高度整合带来的乡村行动者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的变化。萧凤霞以乡、镇、村社区为个案,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乡村社区权力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的改造。萧凤霞认为乡村“细胞化”为国家控制乡村的行政单位后,引发了乡村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变化。乡村干部作为国家控制乡村社区的代理人,在进行道德选择时会有内心冲突;农民则扮演着乡村革命的协从者和受害者角色,常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
共产党“政权下乡”后,党和国家试图在农村重塑新的价值理念,但这种以国家为本位的价值理念灌输是否成功,或者说效果如何值得探讨。在这一方面学者们突破整体论、宏大叙事的讨论,从微观入手分析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与农村社会潜存的传统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
弗里曼、张乐天等从村庄的政治领域和农民的日常生活领域二个层面来研究社会主义文化整合中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着眼于国家-社会关系,考察了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的村民及其家庭是如何置身于新产生的社会主义文化之中的。弗里曼等认为华北农村在家庭、亲戚关系和居住地内在地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普遍的文化权力关系。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后在五公村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并没有使农村传统文化权力关系消失。当官方的社会主义文化宣传占据上风时,这些潜在的传统文化权力关系便隐而不露。如果国家控制削弱,这些文化观念和生活信条就会发挥作用,从而改变政治形态[12]372。张乐天以浙北的联民村为研究对象,采用“外部冲击-村庄传统互动”的分析模式描述了人民公社制度嵌入农村后,革命场面文化与传统的村落文化之间的张力。张乐天认为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尽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但革命的场面文化没有替代传统的村落文化,传统仍然支配着农民的日常行为,血亲、姻亲和邻里仍然是农民可以调动的主要资源。村落文化与革命的场面文化各有领地,私人生活领域和部分公共生活领域为村落文化所支配,政治及另一部分领域由革命文化支配,革命文化与村落文化既有碰撞、冲突,又相互渗透、交错、融合[13]167。赵文词透过国家意识形态影响下乡村精英的行为面相,研究现代文化与传统价值的交错互动。
赵文词通过对移居香港的广东陈村村民的访谈,从国家、社区、行动者间互动的视角,研究了陈村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文化。他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入农村后,与传统儒家道德发生碰撞,农村社会由此产生了两类精英,即“符合社区道德期望的精英”和“适应国家道德期望的精英”[14]17。赵文词刻画了两类精英在农村社会中的表现,突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道德的差异、潜在矛盾与冲突。高王凌突破“上层”精英路线,重点关注普通农民这一“沉默的大多数”对国家层面的集体主义话语系统的反蚀。高王凌考察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活中的那些“猫腻”,详尽描述了农民出于“生存逻辑”而产生的“偷”文化,提出了农民的“反行为”这一概念。他指出农民并不是制度的被动接受者,农民会改变、修正或消解上级的政策和制度[15]192。
高王凌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农村社会这一极在被国家不断塑造的同时,也以独特的方式塑造着国家。以上学者的研究多侧重于共时性因素的讨论,吴毅则将共时性和历时性因素并重,研究村庄场域中国家权威与社区权威的互动状况,考察国家“大文化”与地方“小文化”在村庄内部的交切。吴毅从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三个维度出发,引入“地方性知识”作为理解村庄社会变迁的重要变量。他认为乡土特性对于国家“大文化”有反渗和改造作用,地方性知识所形塑的“小文化”在社会变迁中具有能动作用。吴毅指出现代性和国家只有成功地实现与地方性知识的对接和互融,才可能对社会变迁发生根本性影响[14]373。庄孔韶同样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统一于对福建黄村的考察中,他的研究方法独具特色,通过“文化反观法”研究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互动,追寻中国乡土社会文化传承与濡化的历史根基[16]447-449。
此外,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及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等著作,都以不同村庄为研究对象,描摹国家与村落之间的互动下乡村社会及文化变迁的面相。
学者的讨论展现了国家对农村社会高度整合下农村文化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农村接受来自国家层面的文化整合有一个明显特征,即是文化整合与政治整合相辅相成、互为犄角。尽管如此,农村社会的本土性文化并没有被国家的新权力话语系统完全吞噬,二者的互动一直在此消彼长、相互交错中进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经济秩序的变化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互动网络的重建。人民公社这一集体共同体社会解体后,农户再一次成为分散的马铃薯,农村文化发生了新变化。学者们对国家体制性权力退出农村社会后的农村文化的发展状况十分关注,从总体上肯定了农村文化的进步,吕世辰、陈宇海等认为改革开放后农民的法制意识,市场观念,“义利并重”的价值观明显增强,科学、进步的生活方式为农民所接受。但农村文化发展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从“国家-社会”视角看,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关注农村社会家族文化、宗族文化复兴的问题;二是关注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问题;三是聚焦农村公共文化式微,农民公共文化生活衰落的问题。
对于农村社会出现的家族文化、宗族文化的复兴,许多学者认为农村传统宗族文化的回归是死灰复燃,有碍农村发展。何清涟、谢维杨、吕红平、肖唐镖等都认为宗族在根本上不适应农村的现代化要求,宗族文化复兴是一种文化的退潮。钱杭、杨平、贺雪峰、吴毅等认为农村集体化时期结束后,农户与国家和社区互动关系发生改变,宗族组织在当前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担负着重要职能。学者们在宗族文化复兴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站在农村现代化这个整体性目标的角度,认为宗族文化是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一种是从农村和农民的现实需要出发看问题,认为宗族文化所搭建的功能性网络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也有学者对农村宗族文化的复兴没有一概否定,而是持“发展论”的看法。如王沪宁通过对15个村落的实证调查,对村落家族文化得出以下结论:村落家族文化在“历史-社会-文化”变迁的冲击下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但村落家族文化在短期内不可能消灭,其消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村落家族文化包含着一定的正面因素,其具有以伦理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潜能。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对村落家族文化采取双重态度,即促进其消解,升华其精华。陆学艺指出,按单一的现代化标准评价村落家族文化,难免会强调其负面作用,但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及后现代化社会,村落家族文化将长期发挥重要作用[17]181-185。
关于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问题学术界有过激烈的讨论,对于农民合作的必要性学界已达成共识。徐勇、罗兴佐、吴理财等一致认为,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和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合作是依托国家强制力实现的,是一种外生型的合作。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农民仍需要合作,尤其是对于当前的“社会化小农”来讲,农民间自治性内生型的合作尤其必要。问题是当下农民合作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学者们从文化和心理角度进行了详细分析。曹锦清调查了黄河边的农村,得出了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结论。农民在合作中不是通过相互博弈、相互妥协来换取共赢,农民“特殊的公正观”的存在带来的往往是“共输”,结果合作失败。贺雪峰、吴理财深入剖析了农民合作难以达成背后的逻辑。贺雪峰认为“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得到的好处来‘算计’,而是根据与他人收益的比较来衡量自己的行动,这就构成了农民‘特殊的公正观’: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我的行动中额外得到好处”[18]。吴理财指出村落社会与市民社会日常合作的区别在于,“农民的算计不可能单单基于个体自身,在相当程度上必须将村落中其他人一并算计在内”[19]。对于如何推进农民合作,学者的解答各有侧重。赵晓峰指出为克服潜存的理性农民主客观选择悖论所带来的不合作,需要国家的介入,以政府力量为主导,以农民自愿合作为前提,推进农民合作[20]。徐勇在将农民视为“理性小农”的前提下,认为在利益驱动下,农民“善分也善合”,不可低估农民的合作愿望和能力。他表示应警惕历史上以外力推动下的农村“合作狂热”。对于农民的合作,只能是“水到渠成”,要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10]112-113。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互助合作、集体主义精神弱化,同时伴随公共文化式微,公共文化生活衰落的倾向,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学者们给予积极关注并讨论应对策略。周学荣、吴理财、宋亚平等将视线聚焦于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上,认为文明健康的农村公共文化的重建需要国家发挥作用,但与过去全能性国家不同,国家承担的是服务、引导、管理的角色。学者们指出政府应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品供给上增大对农村的支持。政府要改革传统的农村社会公益服务体系,变“养人”为“养事”,“以钱养事”,建立和健全一整套面向“三农”的新型社会服务体系。张良强调从农村文化的内在层面出发培育和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他通过对湖北、安徽两省八县(区)的农村文化状况进行实地调查,探究农村公共文化衰弱的背后逻辑。他认为农村文化建设要从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3个层面共建,相互配合,形成合力,避免只注重与农村文化相关的人、财、物等外在实体性建设[21]。李祖佩从农村文化承接主体的角度思考公共文化建设。鉴于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外双重困境,李祖佩指出要重视村庄内部的承接问题。他主张以村庄“中农”阶层为主要立足点,培育农村文化建设的内部承接主体,夯实农村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使文化供给内容真正得到村庄的认同和接受。吴淼从农民主体性视角探讨农村公共文化构建问题。通过分析农村文化的独特秉性和自身运行机制,吴淼认为要建设好农村文化,必须尊重乡土文化内生性、本土性特点,让农民担当农村文化的创造者、演员和评价者,而不是由国家越俎代庖。国家要做的是提供文化基础设施和培育民间文化,促进乡土文化自主发展。
从学者们的讨论可以看出,农民合作精神的复归、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塑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工程,从外部供给到内部承接,从实体性建设到软环境培育都需要重视,并且要协调得当。从国家到农民也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力。
四、讨论与反思
通过以上检阅可以看出,农村文化和谐发展需要关注三个实体,即国家、地方性文化网络、农民。传统中国农村,乡村社会游离于国家政权边缘,二者间关系松散。在固化的乡村社会伦理秩序格局中,乡绅这一阶层的存在较好地承接了国家主文化向乡村家户的延展。20世纪初,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相互游离关系被打破,具备了现代性的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整合。20世纪前半叶的战乱破坏了农村社会地方性文化网络,国家与农村社会间一以贯之的主文化出现断裂,农村日益走向失序与衰败,农民失望而无奈。共产党政权深入农村后,一种新秩序、新话语系统在农村社会逐步确立,农村的权力文化网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文化网络被大幅度挤压。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日益以全能主义的姿态进入农村社会,农村“在场”的文化网络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功能性特征愈加突出,其“乡土性”的特征逐渐淡化,结果遭致了农民对国家主流文化宣传的“视听疲劳”,国家文化整合的效果大打折扣。农村改革后,国家体制性权力退出农村社会,农村地方性文化网络大体呈现2种发展方向,一种是向传统家族、宗族文化网络复归;一种是市场社会化背景下农村文化网络涣散。农民或抱团于宗族,或原子化存在,农村文化发展状况不容乐观[22]。为此,从国家-社会的视角来看,新农村文化建设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在农村社会要有稳固的阵地,以促进农村社会整合,引导农村文化的发展方向。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为社会秩序提供保证,是社会整合的基础,也是文化整合的前提。传统中国,儒家思想将血缘性的伦理法则上升为国家政治法则,并在乡土社会构建了与国家制度相一致的思想原则。乡土社会的伦理法则同化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被社会化了。因此从形式上看,乡村社会游离于传统国家之外,但主流文化价值观使二者有机统一在一起。传统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整合、协调作用给我们以启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松散、阶层分化加速,农民社区认同感不高,公共文化疲软,亟需加强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文化领导力。国家应主动占领农村的文化主阵地,通过多种渠道加大主流文化价值观在群众中的宣传和渗透,在农村社会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其“乡村社会化”。
第二,构建农村地方性文化网络实现国家主流文化的“乡土社会化”。农村地方文化网络好比人体的神经,起联系和传输作用,一方面它沟通了农民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它还是国家政权深入农村社会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国家使自己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传统乡村社会,乡绅阶层游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承接着使国家意识形态“乡村社会化”的功能性角色。乡绅以及以乡绅为纽结的社群关系构成了乡村的地方性文化网络。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开启后,乡绅阶层被排挤出局,国家主流文化由上到下一以贯之的“脐带”被剪断,乡村的地方性文化网络涣散了,乡村社会堕入混乱无序的境地。新时期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应积极搭建农村地方性、内生型的文化网络,使国家主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留乡”。
第三,文化整合要走群众路线,关心文化承接主体的现实文化需求。文化整合要走群众路线,文化的领导权应该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治人”。广大民众自觉自愿认可和赞同是文化领导权确立和巩固的基础。我国集体化时期,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灌输是一种被政治领导权同化的文化领导权,它没有关照农民的现实情感,因而是一种“无根”的文化,最终当国家体制性权力从农村社会退出后,“集体主义”精神黯淡了。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要尊重群众的现实文化需求,走外供与内生相统一的路子。一方面国家要根据农民的现实文化需求提供帮助和引导,增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另一方面要以农民为主体,挖掘农村本土文化资源,活跃农村公共文化,重塑农村的社区认同感和集体主义精神。
第四,正确看待农村社会传统的、惯习性的文化形态,重视其作为亚文化的整合与规范作用。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和本源型传统,与家户制相联系的家户主义成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的传统[23]。土地革命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家户传统曾受到新的权力话语系统的排斥,但农民的生活方式并未改变,与家户传统相关的惯习性的价值观念仍然顽强地存在和延续着。所以说家户传统不是能够简单替代,更不是能够简单“消灭”的。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应正确看待农村社会传统的、惯习性的文化形态,如宗族意识、家族观念等。这些传统的文化形态作为农村的亚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尚能发挥伦理道德方面的整合和规范作用。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
[6]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7]杨焕鹏.红枪会与近代乡村自卫(1912-1937)——以鲁东地区为中心[J].民俗研究,2010(3):98-99.
[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9]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徐勇.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
[11]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后的中国农村改革[M].台北:台北张老师出版社,1994.
[12]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3]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4]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5]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16]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17]陆学艺.内发的村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8]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5-7.
[19]吴理财.对农民合作“理性”的一种解释[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8-9.
[20]赵晓峰.农民合作:客观必要性、主观选择性与国家介入[J].调研世界,2007(2):28-31.
[21]张良.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农村文化的三维性分析——基于湖北、安徽两省八县(区)的实证研究[J].中国
农村观察,2010(2):87-96.
[22]禹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J].湖南社会科学,2013(6):214-216.
[23]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J].中国社会科学,2013(8):10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