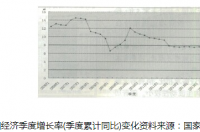小农理想有这样几个特点:保有自家生活需要的土地,以家庭内部分工实现自给自足;邻里最低限度合作,满足低水平的公共服务需求,冀盼正派乡绅秉持正义,维护小共同体秩序;耕读持家,希望小共同体向大共同体(国家治理体系)推送出代理人,维护小共同体的利益。这种小农理想在旧时代不无存在根据。就是在今天,因为中国城乡社会经济高度不均衡,小农理想也有作用空间。事实上,小农理想对农村发展的实际过程有广泛影响。如果判定小农理想完全主导中国农村发展政策,无疑是不恰当的。但小农理想通过舆论,通过某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农村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则恐怕是不能否定的事实。但从中国大局看,小农理想不利于中国农村现代化。
放弃“土地拜物教”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是一条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的财富创造观。17世纪的重农学派以为只有农业创造财富,而土地与劳动是基本条件。这种前古典主义的、已经不适用当代社会的观点还在中国能觅到踪影,例如,总有朋友担心农民离开农村后没有办法生存,要给他们回归农村留个后路。其实这个关怀完全没有必要。只要明晰土地产权,农民走哪里,怎么处理土地,应该是农民自己的事情,给农民自由选择权即可。
其实在现代农业经济中,技术与资本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土地与劳动的贡献。二战以后,世界农业总产出增长数倍,而土地没有增加,农业劳动力更是大幅度减少,这说明,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来自技术与资本。这种结果表现为地租率的下降及土地价格的相对下降。
在土地市场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价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了许多。笔者走访波兰时,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地价情况。1公顷较差农地约4000欧元,合每亩人民币2700元;而较好的农地则合每亩人民币1.4万元。农村地区由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也不贵,算下来每亩约13万元左右。
在人口密度高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我们想象中,日本人多地少,一定是地价高昂。其实不然。东京郊区1亩农地可卖到40万元人民币,考虑到日本农产品价格极其高昂,这个地价也不过是高昂地租的10倍左右,大体与国际价格相当。在北海道,一般的农地每亩合人民币约3000元,而牧业用地甚至可以无偿使用。
土地对经济发展贡献率下降,不是说离开土地后还可以发展经济,更不是说土地制度改革不重要。对于农业,耕地越多,越有利于农业轮作及土地休耕,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但是,农业经济成长的根本出路,是用资本替代劳动,因此,我们不必哀叹什么“空心村”越来越多,不必欢呼地租率与地价的提高。
农业发展:要农场化不要公司化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源。但一些乡村精英的脑袋也不精明。他们喜欢上了农业雇工经营,以为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必由之路。我国很多地方的行政村都设立了公司,有的把原本承包给农民的耕地收归集体统一耕作。于是,村长变成了总经理,书记变成了董事长。
地方政府大多热衷公司化农业。目前究竟有多少公司型企业涉及到田间生产环节,尚没有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从进入农业的企业基本都使用合作社的招牌看,数量应该不少。目前我国合作社数量约150万家,其中示范社在10万家左右,而达到示范社标准的多有公司背景。按笔者的调查,公司化不见得比家庭农场有更高的效率。差不多在1000亩以上的公司农业,都会出现土地分包的情形,否则管理成本会非常高昂。反过来说,一个农业生产单位一旦出现土地分包情形,就意味着出现了因规模过大而发生的“不经济”问题。一些公司化农业投资者直接或间接从农民那里以较低的租金率拿到土地,借助政府的财政支农项目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整理,然后再高价出租给实际农业生产者,自己从中净赚一笔。在有的地方,土地的一进一出所产生的差价可以达到3倍以上。这种以套取国家农业补贴为目的的公司不会认真从事农业经营。分包农户因为土地租约期较短,也没有长期经营行为。
因为公司化农业与庄园经济的兴起,我国农业领域的雇工人数出现增长势头。一些地方官员经常说农民获得了多种收入,有工资收入、租金收入、补贴收入,因此以为好事,遂大力推动农业雇工经营。但据笔者在国内外调研、访问,可认定一般农业田间生产如采用雇工生产方式,其效率会很低。欧美家庭农场的劳动力不足使时,也回请人参与,但通常会以聘请“合伙人”的方式来操作,而不是按计时工发工资。国内有的专业农户个笔者讲过一些生动的故事,说明农业雇工经营与家庭农场经营之见的巨大差异。
依笔者之见,为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促进农村社会转型,应遏制农业公司化、农场庄园化、农民雇工化趋势。政府对相关行为可以不强力静止,但决不可鼓励,尤其不可将支农资金投到这种趋势的当事人手上。
一概反对村庄成立公司也不对。有的村庄事实上已经不是农业居民点,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变成了工业用地,或者变成了大鱼塘,技术上不可分割,成立公司解决一个分配问题,很有必要。但是,就农业耕作来说,家庭经营足以承载起现代规模化农业,不必成立什么公司。
笔者主张大力发展家庭农场,也不是说完全反对“城市资本下农村”。城市资本进入农场以外的农业产业链的其他环节未尝不可,但从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由农场主组成的合作社经营农业全产业链更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家庭农场的规模无论多大,对于农产品的巨大市场来说,还是一个小的经营单位,农场主对市场价格没有影响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农民自己的合作社。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的农民合作社可以十分庞大的规模,足以对农产品价格发生影响,对供应做出安排。这种农业组织有了明显的垄断性。从欧盟的经验看,大体量的合作社控制生产计划以后,减少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提高了产品质量,以致欧盟国家多年未出现农产品严重过剩问题。合作社对市场的控制明显利大于弊。
村民自治不是农民自己全额负担公共服务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取消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因为那个制度带来了不小灾难。但是,村一级的“政社合一”在实践中还存在,在观念上更没有没有取消。“政社合一”体制的核心,是集体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用集体收入的一部分满足社区公共服务需求。
旧时代农村公共服务比较简单,乡绅当家大抵能解决农村公共服务问题,甚至不必有村庄的公共预算。现在不同了,村干部不再是免费提供服务的乡绅,公共预算不能完全没有。政府财政没有实现城乡公共财政权覆盖,村干部找钱成了第一要务。
我在农村调查当中,问基层干部“坚持现有农村管理体制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回答很朴实:如果不实行现在这个制度的话,村庄的公共开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还有第一线官员朋友说的也很直白:如果没有集体经济,上级到基层检查工作,可能没有茶喝,因为集体买不起茶叶。村里面干部说,如果没有集体经济,“我们没有工资发,村里面的道路坏了没有钱修”。
原来就是一个“办公经费”问题!或是农村公共服务经费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而去束缚农民手脚,其实得不偿失。
那么进一步看,我们在农村到底有什么样的钱要花?我总结一下,目前中国农村社区涉及十大“公共事务”,分别是:村容村貌、环境卫生、邻里关系、民俗民风、生产互助、扶贫济困、社会合作、土地整理、产权保护、祖宗祭祀等。这其中,土地整理与产权保护的成本虽然比较高,但却不是经常性的公共事务。农村的其他公共性事务,例如各种社会性保障,本来由政府提供,小型社区不需要自己负担。
以上那些社区性公共事务果真要花很多钱么?不是!处理这些事务,古代中国都基本是免费的,当代的欧美社会基本也是免费的,因为小型社区的公共服务常由志愿者提供。在欧美国家,某些公共服务的组织责任,会实行轮流坐庄制,坐庄者是不取报酬的。
退一步说,这些社区性公共服务如果不能免费获得,我们又可算一笔账。如果我们给每个村补贴20万人民币,形成针对解决农村社区性公共事务支出问题的全国城乡公共财政全覆盖机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全国涉农的村庄是大概50多万个(不少城中村和城郊村庄已经实现了公共财政全覆盖),实现公共财政全覆盖大概需要1000亿人民币。
有了这个1000亿支出,就可以实现“政经分离”改革与更深入的产权改革,从而能更大程度地放活农民经营权。通过深化改革,农业GDP如果若能增长15%,就意味着多产出9000亿左右。这个帐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没有1000亿吗?当然不是。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涉及“三农”的支出近3万亿。用1000亿换来9000亿,这个改革红利可谓巨大!很高兴中央最新发布的关于农村综合改革的实施方案,肯定了“政经分离”的改革探索。希望这项改革为深化农村产权改革提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