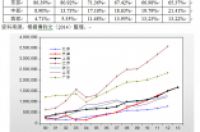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至少在150多件作品的800多处论及中国。虽然他们两人曾筹划出版包括其中部分文章的文集,但最终却没有实现。在当时,他们“论中国”的文章被广泛转载和摘引,如发表在美国最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系列文章,至少被《纽约半周论坛报》和《纽约每周论坛报》转载了20多篇,并被《纽约时报》等摘引。不过,海外对“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真正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25-1956:俄英德语种马克思恩格斯专题文献编译导读阶段
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主要讨论了东方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在7月7日的第三十次会议上,梁赞诺夫作了关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报告,称“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文章也将被编入①。1925年梁赞诺夫用德文发表了《马克思论中国和印度》一文,1926年英国《劳动月刊》发表了节译自该文的《马克思论中国》以及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同年出版的美国《工人月刊》也刊登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并在文前加有介绍该文和“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编者按。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也掀起了一股“太平天国热”。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拉狄克在读到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论述后颇为兴奋,于1927年1月22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马克思是十二分的注意到太平暴动的进程,曾著了许多论文在《纽约论坛》上发表。……还在二年以前我即很奇怪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会没有关于太平暴动之记载,在五卅事变后梁尚诺夫同志首先发现了马克思关于此伟大的事变之论文。”②有学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不论是在俄国还是其他地方都流行出版各类马克思主义专题文集: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文学、马克思恩格斯论印度、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论西班牙,等等。”③单就“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而言,先后以俄语、英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出版了一系列编译类的专题汇编,其中,俄、英、德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传播最为广泛。
1937年4月,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编译部根据各种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作品,编译出版了汉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9卷、第11卷上、第11卷下、第12卷下以及俄文第2版第9、12、13、15卷中,均收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文章。在俄文版《资本论》(1936)、《剩余价值论》(1936)、《政治经济学批判》(1935)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的相关卷次中,也有一些涉及中国的片段。此外,在1959年出版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中,也收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文章。其中,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因为缺乏参考书而在引文的翻译上存在缺陷,且误收了并非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中英冲突》一文,少收了6篇文章④,但其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以发表时间为序分类编排的体例,却为以后在中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各版本奠定了基础。该书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的论述分为三编,分别是:古代东方底特点与中国(包括“生产力•村社”、“国家•土地所有权底形式•地租”、“商业•高利贷•货币”三个主题),关于中国的论文(共17篇),世界商业与对华政策(包括“欧洲人之‘发现’中国”“对华商业”、“列强与太平革命”、“俄国与中国”四个主题)。
1951年,英共党员道娜女士编纂出版了英文版《马克思论中国》一书,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并附有导论和注释。该书后来多次再版,并于1973年由高山林太郎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道娜是英共历史学家小组的重要人物,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家,曾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道娜所编纂的这本书尽管名为《马克思论中国》,但也收录了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没有收录马克思的《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段》、《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以及《新的对华战争》的第一篇,且误收了并非出自马克思的《一些官方信件》(又名《毒面包案》)。此外,该书还附有与收录文章有关的大事记,校正了原文和引文中的一些印刷错误。这本书对英语世界的读者了解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述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后来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文献的编纂提供了参考,例如1957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就根据她这本书增加了5篇文章并对原译文进行了校订。
1955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编译出版了德文版《马克思论中国: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收录的文章与道娜《马克思论中国》一样,因而也存在误收、少收的缺陷。不过,该书还增收了1856年9月26日至1869年12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中的12条、《资本论》第2卷中的1条和第3卷中的3条关于中国的论述,并增加了40条注释、1834-1864年相关事件大事记、70多条人名索引以及近百条德语与其他外国语对照表。1959年4月30日至5月12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率团访问中国,期间向中国转交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赠给毛泽东主席的108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其中就包括这本《马克思论中国》。
此外,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在1975年也出版了由罗泰教授作导论和注释的西班牙语版《中国:活化石还是火药桶》,其中收录了多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文章。在米兰,1960年出版并于1965、1970、1976、2008年再版的意大利文《印度、中国、俄国》一书,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东方三国革命的文章,其中包括《时评。1850年1-2月》以及另外17篇与英文版《马克思论中国》一样文章。不过,这两本专题文集多是以50年代的英、德文版为蓝本,影响较小。
二、1957-1983:美国学者关于共产主义中国性质的论争阶段
受1950-1954年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再加上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朝鲜战争爆发等事件,使美国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出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对华决策的需要以及中苏关系紧张等国际形势变化,基于地区差异的比较共产主义研究⑤广为流行,中国成为摆在美国学界面前的迫切问题,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之一⑥。不仅如此,这类研究还延伸到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对“毛主义”的评价问题,关于传统中国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中国历史的延续与变革问题。当然,在这些研究中也折射出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例如安多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其有效性是有限的,它与非资本主义的或非欧洲社会的关系是可疑的⑦。再如佩弗认为,马克思是天才的甚至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但作为19世纪的欧洲人,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分析方法主要是用来解释或批判他了解最多的世界,即欧洲资本主义世界,显然他并不是一个了解世界一切方面的人,更不用说了解他根本未曾生活其间的世界特别是中国了⑧。
在20世纪50年代,以魏特夫、史华慈等人为代表,在探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时,较多提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论述。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费正清将早期中国看作古代东方社会的一个典型,其中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特点的论述,显然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⑨。魏特夫在1951年发表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中国只是在表面上假装接受马克思,中国共产党竭力回避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特别是对中国的评价,以至于许多中国人对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述知之甚少;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关于历史和政治的观点被列宁乃至斯大林的观点所取代,这一点很少被提及⑩。1954年史华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的论争》一文,探讨了1928至1937年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争,并论及了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他指出,马克思并未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仔细进行过研究,中国似乎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的所有分类,或一点儿都不符合,这一争议一直未完全解决,直到通过国家行为用目前的共产主义制度才将其“解决了”(11)。
1957年,魏特夫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书,其核心观点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为了利用有限的水源并抵抗定期的洪水需要进行大规模治水,这有赖各方面的有力协作,也需要有效的工程管理,于是形成了纪律、从属关系以及相应的道德信仰观念、最高政治权力,出现了专制君主、东方专制主义,这就是所谓的“治水社会”,而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这种“治水社会”形态。他指出,将东方世界与封建欧洲等量齐观,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新单线论”所造成的,这一理论运用意识形态和政治手段消灭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和多线发展的概念,把中国等东方国家的传统制度说成是“封建的”,认为现在的俄国和中国已经达到一种较高的社会主义或原始社会主义发展水平,已经战胜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魏特夫还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公社的形式,这种农村公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12),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的消失并没有瓦解“亚细亚生产的经济基础”,而19世纪50年代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把东方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性质神秘化,则是“对科学的犯罪”。他认为列宁进一步阉割了已被马克思阉割过的关于亚细亚的概念,担忧布尔什维克革命会倒退为旧沙皇制度的复辟,而斯大林则对亚细亚复辟的可能性不大在意,结果最终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复辟的代表”。他还指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建立了一种农业专制主义,这跟过去的专制制度极为类似,但中共党内的官僚统治者并未警惕亚细亚复辟问题,甚至共产党中国成为了真正亚细亚复辟的产物(13)。魏特夫曾是德共中央委员,在30年代与共产主义运动决裂,后成为“百万人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委员会”成员,特殊的经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共产党中国充满偏见。不过,他的这部著作在当时的西方对“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评价产生了广泛影响。
到了60年代,魏特夫在此基础上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观》,连载于《中国季刊》1962年第11、12期,详细阐述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中国观(14)。对于他的观点,马思乐等人进行了批评,认为他并未掌握马克思论中国的实质,即马克思当时关注的是英国的外交政策而不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15)。这一时期还有两本重要著述提及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是出生于上海、后到了美国的唐纳德•洛威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于1966年出版的《论“中国”在马克思、列宁、毛思想中的作用》;另一本是先在法国出版、后于1969年在伦敦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亚洲》,由德恩科斯和施拉姆合编,并由施拉姆从法文译为英文,这本书在70年代美国关于“毛主义”的讨论中影响很大。
进入70年代,特别是随着中国“文革”的开展,《近代中国》杂志主编黄宗智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有关“毛主义”的讨论,在讨论中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论述。魏昂德认为,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毛泽东的战略与思想,魏特夫否认乃至攻击其原创性,史华慈捍卫其原创性,而施拉姆则有条件地肯定其原创性,但在他们与此有关的论述和研究中,却只对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进行了微不足道的分析。例如《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一书,只用了10页的篇幅来阐述马克思的著述,而且几乎全部是从马克思论述殖民主义的信件和文章中零散摘出的(16)。施拉姆在回应魏昂德等人的质疑时也承认,在他和德恩科斯共同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亚洲》这本书中,因为论述的重点是列宁以后对马克思的发展,因此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非欧洲世界的著述只摘编了有限的部分。魏昂德在随后的答复中并不否认,从马克思所写的新闻和政治小册子里可以拣选出许多预言、断言和华丽的词藻,其中有的包含了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也有许多是相互矛盾的,但他要批评的是一些编选者误将这些构成马克思整体理论中一个阶段的侧面大加阐述,而这些阐述却与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著作割裂了。事实上,马克思有关亚洲的零散论述并不能指导我们去掌握其理论的实质内容,孤立探讨这些不完整的章节只会产生误解,因此人们需要详尽掌握有关此类问题的其他著作和论断(17)。之后,施拉姆又针对魏昂德的上述观点进行了评论。他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关于亚洲社会的观点,真的如魏昂德所说与其基本理论假设不一致吗?当然不是,而是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亚洲社会不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而如此落后,而是因为社会自身性质里天生的弊端使其生产力无法得到发展,因此文化诸因素的重要性很难与作为马克思哲学观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一致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见解是马克思的非代表性思想,而是从黑格尔和孟德斯鸠那里学来的东西,只是反映了马克思所生活时代的知识界的一种时尚。而最能反映19世纪中期特点和马克思思想特点的,是认为亚洲的进步只能是欧洲工业革命影响的结果,直到生命将尽时,马克思仍坚持认为欧洲是世界进步和创造性的源泉,即使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需要欧洲无产阶级的倡导。虽然魏昂德在大肆渲染和误解这一问题,但他肯定从《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中读懂了,我们并不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理论是理解亚洲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指南,相反,我们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企图恢复亚细亚生产方式、试图将中国逐出世界历史的法国、匈牙利和其他欧洲共产党员,以致于我们遭到了这一运动的主将们的责骂。尽管马克思与毛泽东有诸多连续性因素,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却作了一些重大修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错了。因此,对于那些旨在证明毛泽东是一个伟大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要求在思想与行动的一切重要方面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一致)的人来说,应该看到马克思历史观中的“欧洲中心论”偏见和对工人阶级作用的推论,应该研究这些是否是马克思思想实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仅是马克思偶尔提出的、只具有暂时价值的理论(18)。
此外,在上世纪70年代,随着道娜的《马克思论中国》在1968年重印,有关这本书的书评也随之陆续发表。其中洛威认为,从20世纪来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中国的论述既不深入、也已失去光泽,与今日的中国共产党无关(19)。德里克在一系列论述中,特别是在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也谈到“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问题,他的这一著作在海外引起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编纂的广泛讨论。进入80年代后,在关于中国政治以及国家权威主义、全能主义等的讨论中,也有人提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魏昂德的《共产新传统主义》。
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不断崛起,海外中国研究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获得一手资料,因此人们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又开始了新一轮考察。同时,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出版,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也掀起一次热潮。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再次被一些学者提起。
在历史学领域,美国历史学家石约翰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中指出,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产生兴趣与中国大同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有关,但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评价有一个从赞许到斥责的过程。使用“郡县社会”这一概念对中国进行非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石约翰认为:“马克思认为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马克思从未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社会政治关系进行理论上的分析。马克思对此的不确定性反映了以下事实,即他说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不一定契合中国,无论是封建的、亚细亚的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不适宜描述这个实际上没有工业但又充分发展的郡县社会。例如,马克思清晰而合理地将日本确定为封建社会,而那时的中国呈现的情形却与日本大不相同。”(20)
文学领域有人指出,马克思曾将英、中之间的冲突喻为一场决斗,并经常用假设等创造性、幻觉性文学世界的修辞来描述世界事实,以便读者将其作为文学来理解(21)。1985年,以研究“中国形象”见长的德国汉学家夏瑞春编辑的《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出版,共收录了18篇文章,其中就包括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对华贸易》以及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1994年台北出版的《西方思想家论中国》一书,收录了武汉大学刘纲纪撰写的《马克思眼中的中国:“以人道的真诚谴责殖民主义”》一文。2000年德国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英国在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卡尔•马克思对儒化中国和西方殖民扩张冲撞的描述和预言》。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发表的《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德国及意大利刊行的书刊杂志中所见太平天国的形象》一文,也用不少笔墨谈及马克思的“中国形象”。台湾学者杜奉贤在比较了马克思与韦伯关于中国的论述后认为:“马克思对中国的解释整体来说非常粗糙,在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意义上用处不大。但是他原本志不在此,又何能见怪,可怪的应是那些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误用马克思的历史公式来解释中国,或是以政治企图来扭曲马克思的言论。但至少马克思把他所知道的写了出来,而且秉持公道对中国寄予同情和期盼,这点是值得肯定的。”(22)
此外,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中,还有三种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倾向性观点需要澄清。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述是否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日籍华裔学者谢世辉认为:“欧洲中心史观是在19世纪由黑格尔、马克思、兰克等人提出的。”(23)霍布斯鲍姆也认为:“西方的哲学家们包括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信念,即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在欧洲而不可能在亚洲或非洲找到。这一错误信念至少部分源自其他地区在文字和城市文明上的连续性与西方历史的非连续性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别。”(24)1998年,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在《重识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一书中更是明确指出:马克思与韦伯及其信徒用狭隘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视野看问题,“所谓在欧洲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在世界其他地方了无踪迹,只有通过欧洲的帮助和扩散才能提供这些要素。这就是马克思的‘东方学’假设、韦伯的大量研究以及二人发表的有关世界其他地区的无稽之谈的落脚点”;马克思将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推广至中国、亚洲和整个东方,“他断言,在整个亚洲,生产力始终是‘传统的、落后的和停滞的’,如果不是‘西方’及其资本主义的入侵把亚洲唤醒,亚洲会永远沉睡”(25)。以上评价有失偏颇。事实上,自1840年起,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终生都有关于中国的论述,他们始终关注着中国。在早期,他们确实沿用了西方传统思想中以欧洲中心主义来评价中国的话语,但也同时说明了中国在特定社会阶段表现出的历史事实,后来他们则直接关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认为中国与世界(其他殖民地和欧美地区)相互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科技文化、革命形势、民族精神等一系列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把关于欧洲研究的结论套用到中国,相反,他们非常注意中国所表现出来的与欧洲的异质性和不平衡性,并对中国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这恰恰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述是否表现出鲜明的“颂华”或“贬华”倾向,还是从掌握的材料中得出了较为客观的中国印象。启蒙时代曾描述过中国的欧洲思想家,常被后人划分“颂华派”(Sinophilies)或“贬华派”(Sinophobies),如沃尔夫、伏尔泰和魁奈属于前者,孟德斯鸠、狄德罗则属于后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也受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对中国既有赞誉之词,也有批判之语,例如对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就是如此。但整个来看,他们更多是对中国社会现实运动进行客观评述,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并得出了一系列较为客观的结论。近年来,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美化”了英国侵华战争,有“歧视”乃至“丑化”中国人的倾向(26),这类观点广泛传播后产生了较坏影响。事实上,马克思确曾谈及奴隶贸易对资本主义的重要影响,甚至指出:“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用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机器大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27)他还将鸦片贸易和奴隶贸易相比较,并引用蒙哥马利•马丁在《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中的话说,“‘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进而强烈谴责了鸦片贸易以及殖民者对“中国苦力”“华工”的压榨。关于其他地区对于欧洲革命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也并未仅仅承认或赞誉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他们对印度、俄国甚至爱尔兰的民族运动也持肯定态度。例如马克思认为,相较于英国人,爱尔兰人更富有革命性,且由于爱尔兰还存在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因而爱尔兰革命可能是英国革命的先决条件(28)。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一些赞誉之辞并不是独有的,也不具有什么“颂华”倾向。
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研究相比以往是否发生了倒退。安德森认为,由于当时欧洲的东方史研究刚刚起步,马克思恩格斯在缺乏资讯的情况下,很多关于中国的看法或推论都与现实经验不符,例如自给自足的村社制度和治水社会这两个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实际上全盘继承了欧洲关于亚洲的传统论述,几乎未作修正而加以转载。……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欧洲人反思亚洲的传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比他们的前辈倒退了。”(29)这种评价有失公允。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研究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其欧洲前辈,即使与同时代人关于中国的论述相比,他们依然有很多独到见解,并为后续的中国研究提供了新范式,例如在关于中国研究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等的讨论中,均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柯文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主张从中国社会内部来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把中国视为“未发达”国家,需要按西方形象对其加以改造,因而他们仍属于“传统—近代”模式(30)。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准确。对于19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关注来自其外部的冲击及其带来的回应,并对由此造成的破坏性或建设性结果从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两方面给予了全面评价;另一方面,他们也关注中国社会结构对其生产方式的固化作用,重视中国对欧洲以及世界的作用和影响,强调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不断转变的地位。这种观念大大深化了他们对亚洲国家和东方社会之差异性、复杂性、稳定性的认识,丰富了他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多样性的思想,实质上也影响着后来欧美关于近代中国和共产主义中国的研究。
注释:
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②拉狄克:《列宁与中国革命》,载《国际评论》1927年2月9日第19期。原载《真理报》1927年1月22日。亦可参见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整理、校注:《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229页。
③Eric Hobsbawm,How to Change the World:Marx and Marxism 1840-2011,London:Little,Brown,2011,p.193.
④少收的这6篇文章分别是《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段》、《英中冲突》、《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俄国的对华贸易》、《英国的政治》。
⑤这一研究还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样化、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兴起等有关,例如1966年和1967年,在美国召开了关于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会议和讲座,1968年7至10月美国南加利福利亚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院创办了《比较共产主义研究》杂志,1993年后更名为《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此外,从方法论上阐述这一研究领域的著述可参见:Robert C.Tucker,“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munism”,World Politics,Vol.19,No.2,Jan.,1967; Frederic J.Fleron ed.,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Chicago:Rand McNally,1969.
⑥参见George E.Taylor,“Communist China—The Problem before Us”,Asian Survey,Vol.1,No.2,Apr.,1961.
⑦参见Stephen Andors,“Mao and Marx:A Comment”,Modern China,Vol.3,No.4,Oct.,1977,p.427.
⑧参见Richard M.Pfeffer,“Mao and Marx in the Marxist-Leninist Tradition:A Critique of‘The China Field’and a Contribution to a Preliminary Reappraisal”,Modern China,Vol.2,No.4,Oct.,1976,p.442.
⑨参见John King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4th and enlarged ed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7-31.
⑩参见Karl A.Wittfogel,“The Influence of Leninism-Stalinism on China”,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277,Report on China,September,1951.
(11)参见Benjamin Schwartz,“A Marxist Controversy on China”,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3,No.2,Feb.,1954,p.152.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
(13)参见Karl A.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pp.369-412,441-443.
(14)参见Karl A.Wittfogel,“The Marxist View of China(Part 1)”,The China Quarterly,No.11,Jul.-Sep.,1962;“The Marxist View of China(Part 2)”,The China Quarterly,No.12,Oct.-Dec.,1962.
(15)参见Maurice Meisner,“The Despotism of Concepts:Wittfogel and Marx o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16,Nov.-Dec.,1963,p.99.
(16)参见Andrew G.Walder,“Marxism,Maoism,and Social Change”,Modern China,Vol.3,No.1,Jan.,1977,p.102.
(17)参见Andrew G.Walder,“A Response to Wakeman and Schram”,Modern China,Vol.3,No.4,Oct.,1977,pp.389-390.
(18)参见Stuart R.Schram,“Comment on Walder”,Modern China,Vol.3,No.4,Oct.,1977,pp.399-400.
(19)参见Donald M.Lowe,“A Review Article:Marx and China,a Disparity of Two Worlds”,The China Quarterly,No.41,Jan.-Mar.,1970,p.114.
(20)John Schrecker,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2nd ed.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2004,p.209.
(21)参见艾多阿多•卡达瓦:《文学前的马克思》,载王逢振、蔡新乐主编:《批评的新视野》,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22)杜奉贤:《中国历史发展理论:比较马克思与韦伯的中国论》,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版,第160页。
(23)[日]谢世辉:《世界历史的变革——向欧洲中心论挑战》,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4)Eric Hobsbawm,On History,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7,p.224.
(25)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14,15.
(26)参见人大经济论坛:“卡•马克思说中国人是天生的蠢货?”,http://bbs.pinggu.org/thread-2576120-1-1.html.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2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页。
(29)Perry 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Verso,2013,p.492.
(30)参见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61,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