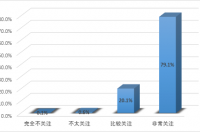巴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撼动者与终结者
巴特早年学习考古学。他因为随他父亲到芝加哥访学并申请入学,在1949年获得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到挪威之后,继续与芝加哥的老师们保持联系,并在1951年参加了芝加哥大学的一支考古队到伊朗进行考古发掘。发掘结束之后,他没有离开,而是留下来对当地的库尔德社会进行研究。后来,他到伦敦经济学院呆了一年,于195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南库尔德斯坦的社会组织原则》。巴特原想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但没有成功。之后,他追随利奇去了剑桥。为了博士论文,他到巴基斯坦的斯瓦特(Swat)从事田野工作。1959年,他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领导》。
从书名可知,这是一本政治人类学著作。政治人类学崛起于非洲研究,典型的政治人类学著作都在思考为什么一些缺乏国家组织(stateless)的非洲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动态平衡(equilibrium)之中。《非洲政治制度》(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 1940)和《努尔人》(Evans-Pritchard 1940)是为典型。研究非洲的政治人类学家在研究取向和视角上多延续自拉德克利夫-布朗,采取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与叙事方式。他们实际上探求的是那种制约个体的社会结构,以及这样的结构如何运作和发挥功能。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更多地从涂尔干的洞见中获取营养,所以,这部分政治人类学者在一定的意义上俨然为涂尔干主义者。这就是说,社会如何稳定地运作是他们观察的重点。他们研究非洲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的意义上有自己的道德诉求,表现出对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不满。
巴特虽然有这些学者的传承,但却另辟蹊径,并就此与结构功能主义告别。根据他自己在前些年写的自传文章所言,他所关注的是个体的选择:与基于由社会功能所定义的条条框框和一些法规和将政治组织视为“制度”的传统人类学的方式不同,我想去将它描述为参与者的选择和调整的结果:在斯瓦特,这些参与者是地方上的成年男性。……正如我所观察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才能最好地理解构成社会组织的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巴特发现,人们的决定取决于个体根据利益和策略所做的判断,而非取决于道德上的考虑。与这种情形相伴而行所要求的是理性。当然,巴特没有否定存在着具体的组织,而且当地人也知道当地存在着两大集团。但是,这些集团的模式从未要求组织般的制度化,只不过是些行动者策略性结盟之无意为之的后果。
巴特在斯瓦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他观察到了个体在结构中的作用,后来强调能动性的实践理论究竟有无受到他的启发我们不得而知,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确在他的《实践的逻辑》中引用了巴特。在“亲属制度的社会利用”(Social Use of Kinship)一章中,布迪厄援引了巴特的第一部著作中有关平表婚(parallel marriage)的见解来发展自己的理论。之所以援引巴特,盖因巴特注意到了一个结构主义者忽视或者排除掉的问题:究竟是经济发挥功能或者是政治发挥功能?前者有如保持“祖产”(patrimony)从而有益于继嗣群;后者则强化了继嗣群整合。巴特强调了外婚在集团斗争固化了最小继嗣群体是为法人团体的作用。巴特显然意识到当事的个体是有策略的,尤其继嗣群头人,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婚姻来控制那些代表着潜在分离势力的侄儿们。
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巴特的理论(包括巴特的批评者理论)使平表婚成为强化继嗣群团结和限制团体裂变的工具。所以平表婚不能解释为纯粹的婚姻交换逻辑,而所有的解释都无法回避外在的经济或者政治功能。由此足见巴特早年的著作已经通过关注个人的理性选择来寻求社会功能上的解释。换言之,个体的能动性在结构中的作用不能忽略。由此亦可见,巴特的一些想法与实践理论有些渊源关系。
如果说巴特1953年的著作在终结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上仅见端倪,他的斯瓦特研究就很明显了。当然,终结者不只是巴特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但巴特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地方政治的博弈,在结构中突出了个体的作用。因此,他的理论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加入了过程论(process theory)阵营,与这一阵营的其他学者一起,终结了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过程论是一种方法论和理论取向,20世纪60年代是其巅峰时期。最初提出过程论的是斯瓦兹(Marc J. Swartz)、特纳(Victor Turner)、图登(Arthur Tuden)。他们在为一本合编的书所写的序言中宣称:研究政治就是研究过程,研究人们如何决定和实施公共目标,研究社会成员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和运用权力来实现这些目标。在这一严格的定义里,最关键的术语是过程。人类学者所关注的过程是公共的过程(public process),这就避免滥用权力概念。 在过程论人类学者看来,作出决定和强加这些决定构成了权力。因此,政治人类学应该研究权力的竞争和权力拥有者实现群体目标的方式。该取向实际上强调“中介”或者“代理人”(agent)的角色。过程论取向的出现对于那些在殖民主义体系正在解体的情境里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而言,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发展。它的出现表明了人类学,尤其是英国人类学从结构功能开始向关注个体的动机、行为方面的转向,过程论的出现也推动了原先极少对话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和不列颠社会人类学之间的交集。
以上说明,巴特的学术思考一以贯之,注重个体甚于整体。在田野工作上,他也有别于常规民族志,并未寻求坐落性的社区(site),如村庄之类。而正是这种独特的田野作业方式,才使他更多地关注个体的能动性,更多地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具体的个体身上。因此,当研究主题转移到族群性问题上来之后,巴特很自然地关注人与人的互动,以及在互动过程中如何制造或者维系边界。巴特对族群性本质的解释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历久不衰,并推动了族群性研究的“认知转向”。
“边界”与族群性研究认知转向
巴特自己大概不会想到,他这种通过关注个体交易来理解族群性的做法竟然渐渐地引发族群性研究在方法论上出现了认知转向。在此,有必要先就这转向的过程略作回眸。族群性(ethnicity)成为学术课题是美国社会学界开始的。社会学关注自身社会的问题,而种族与族裔恰是美国社会的严重的问题,自然受到了社会学家的关注,族群性成为美国人类学课题应与社会学有关。笔者相信,在人类学领域里,美国人类学家20世纪60年代在东南亚从事研究时最早使用了这一概念。这些人类学者在研究旨趣上与传统的美国文化人类学略有不同,他们受到韦伯和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双重影响。他们的研究取向与社会学非常不同。社会学上对族群性的讨论一般并未对认同的主观意义详加分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社会的不同“种族”或者族裔早就在美国经济体形成过程形成结构性不平等,社会学家所研究的就是这种不平等及其所衍生的社会问题。而美国人类学家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异族环境里从事研究,很容易被新兴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纷争所吸引,关注不同群体在多种因素条件下的互动,因而很自然地与社会学有所不同。
虽然,利奇(Edmund Leach)在其经典的《缅甸高原政治制度》中已经考虑了群体主观意识方面的问题,但在书中,既不见“族群性”,也不见“认同”。1965年,美国人类学家在东南亚的老挝、泰国一带做田野时发现,当地一个称之为“Lue”的族群,对于自身为谁看法因不同国家的在场而有所变化。这使得人类学家们思考,在多大程度上族群之所以为族群是由文化所决定。换言之,人类学家开始怀疑文化在族群界定上是否有效。
与此同时,格尔兹正在刚挣脱荷兰殖民主义枷锁的印度尼西亚从事田野工作。独立不久的印尼,族群和文化多样性在新兴国家的语境里多有纷争、碰撞。格尔兹由是指出,既定的民族国家模式与后殖民国家丰富的文化、族群、宗教,甚至种族多样性构成矛盾,这必然导致在新兴国家内部发生族群性问题。他援用了以赛亚·柏林(I. Berlin)的话:民族主义寻求一种认同,这种认同能使国家在世界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being somebody in the world”)。这是这些国家产生民族主义运动的动机之一。另一个动机是实践性的——追求现代化、提升生活水平。但这二者都与多样性相牴牾。而对于这种矛盾,除了社会政治条件之外,他用了“原生”的解释(primordial attachments)来说明民族国家模式与多样性之间所存在的紧张是本质性的。这些所谓原生的内容来自某些“既定”的东西,如亲属关系、出生的宗教共同体、语言、方言,以及特定的社会践行等等,不同群体的人们以这些来区别彼此。
在人类学领域里,另外一种对族群性的理解主要来自政治人类学,但也与殖民主义有关。 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开发种植园和矿井,吸引不少部落成员流入城市成为种植园或者矿井的员工,赚取货币。他们从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聚集的移民社会里,当地人很自然地根据部落扎堆的现象,语言和其他代表部落的象征使得同一部落或者相邻部落的成员走到一起。后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日益增多的部落成员进入城市从事各种货币经济。人们通过发掘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城市区域内形成非正式的组织,出现了各种并非建立在领土之上的“部落联盟”,力求在权力和资源竞争中占据先机。这种政治人类学称为部落主义的现象,在非洲之外的研究中称为“族群性”。这一现象的产生并非不同部落之间的疏离,反倒是因为来自不同部落成员,或者干脆是不同的部落,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互动密集化所带来的。
格尔兹和非洲研究的政治人类学家关于族群性的见解形成了所谓的“原生论”与“工具论”的“分歧”,但事实上二者间并无矛盾。前者把族群性置于民族主义运动和话语的语境里来观察、讨论,后者则更多地将之与利益与资源争夺联系在一起。在巴特的影响下,不少研究者还注意到,包括原殖民地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族群运动或者认同政治里,当地人的族群认同其实是国家或者当年的殖民当局为治理方便起见而在当地所作的人口分类。当地人把这些类别当作自己认同来表达利益诉求。而对分类满意或不满意也会产生大量的族群性话语。这些讨论进一步验证了巴特有关族群性是一种分类实践而非共享某些文化特质的假设。分类的实质就是制造“边界”,而“边界”则是在“遭遇”(encounter)之际才体现出来。族群性于是成为不同主体“遭遇”的问题,因而应当把族群性视为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而一旦将焦点转到“边界”上来,认知(cognition)就成为整个问题的核心所在。
“边界”(boundary)是社会人文学科和心理学上的重要概念。所谓边界不一定是物理性,它可以是他我遭遇之际有意或者无意间表现出来,用以体现彼此有别的方式和语言。虽然这是个常用的词,但在人类学上用来涉及认同,却出现得较迟,巴特很可能是第一人。前此虽然有格拉克曼和利奇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有类似的讨论,但巴特则直接用边界来解释何为族群性。
巴特的主要观点是:族群是社会建构的,但应考虑到周围环境的限制。族群并非先于文化和整体成员而存在,而且也不是固定不变。这就意味着,族群并不具有观念那样的持久性。巴特还认为,调查群体的实体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不应是孤立的,因为这样做产生给人以误导的印象,趋于相信族群是稳固的,在本质上被束缚着的凝聚物。从而,注意力应该聚焦于群体边界。晚年的巴特写道:他和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同事们的这本书引起广泛关注原因在于:
它的违反直觉主张:不同于人们话语里具体化的常识,不同于族群活动家和人类学教科书中的修辞。族群认同并非取决于共享文化与历史的大量事实,而是取决于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之更加有限的一系列标准,而且如果政治势力进行操纵,它还会深受影响。
巴特的重要贡献在于强调考察族群应该改变原来那种通过一系列客观的族群标志如服装、食物、语言等,而是应该考虑限制这些内容的边界。关于族群边界,巴特有两个重要观点:第一,边界是持续存在的,尽管许多人群和信息不断地跨越;第二,根据第一点进行推论,群体无法与世隔绝地存在,而是必须与其他相类群体互为存在。换言之,边界不可能无中生有地框定“某物”,而是辨别两个以上的“某物”。这样一来,族群性实为不同主体的分类实践。
巴特并没有忽视群体的文化内容,他将此考虑为两种类型:可以辨别的标志如服饰和语言等;“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如道德品行和其他社会规范。但他反对以这些内容来做分类标准,这是因为这些内容可以列出很多,而社会行动者在面对人类学家时可以根据需要有所选择,或者列举,以此在任何既定的场合说明自己身份和地位的正当性。在巴特看来,族群认同是高级的认同,超越了或者至少等同于其他认同,巴特的观点因之更接近于所谓的原生论(primordialism),因为个人之间的磋商(negotiation)、交易(transaction)对巴特而言是理性的选择,而族群性作为永久和本质性的条件会作用于限制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反映其族群认同。所以,如同他在斯瓦特所做的研究,巴特将族群性理解为分类实践也是建立在对个人的观察采访之上的。从而,族群性的过程就是个体理性选择的过程。显然,巴特从遭遇、流动的角度来理解族群性。
巴特的洞见不仅跨学科地推动学术界对族群性乃至民族主义问题的深入思考,涉及到这两个领域,你可以不同意他,但不能无视他或者绕过他。人与人之间一旦有他我之别,边界就产生了,这实际上就是分类。但是,产生他我之感并不一定非得剑拔弩张,更多的时候只是疑惑与不解,再进一步或许是刻板印象的铸成与浮现。而以上一些学者所提及的认同政治下的族群类别证明了国家对人口的分类会被社会所接受。一个范畴或者类别从原先未见之到见之于头脑中,就是认知的过程。根据洛克(John Locke)的白板理论(tabula rasa),人类的范畴或者类别绝大部分都是后天习得的。但先天的也不是没有。根据笔者的理解,所谓族群性研究认知转向,建议的是寻找这些更为自然的、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分类实践。在族群性问题上,人们习惯的是“群体性”(groupism)的分类,但需要了解更多的,在群体性之外的范畴,把族群性视为一个研究领域,将之视为理解、解释与经验概括的方式,从而超越本质性和群体性本体论思考(substantialist and groupist ontologies)。
边疆、主权、民族
巴特的边界对于我们理解边疆很有意义。当然这个边界指的不是通常所说的边界(border)亦即实体的,可以通过界碑和其他标志物来强调的主权划分标志。巴特意义上的的边界并非物理性的,尽管也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方式,如语言、肢体语言等而为人们所感知。边疆通常被理解为实体意义上的,但是如果从其他语言或其引申意义和象征意义来理解,也可以未必是实体意义上的。但毫无疑问,无论在地理意义上或者文明意义上,边疆都带给人一种空间感或者距离感。
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在词义上,中西文并没有多大差别,它指的是一种核心(core)与边缘(periphery)或者文野之别(civilization and wilderness)或者文明与野蛮(civilization and savagery)的对峙。边疆被赋予主权的意义完全是现代国家出现之后的事。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把边疆视为主权存在的标志。当然这里牵涉到一个事实,这就是边疆对许多国家毫无意义,比如众多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领土很小,与其他国家如同隔壁的邻居那样相处。而在我们的印象里,边疆则是广袤的,它虽然代表了主权但是人烟未必稠密,许多地方如同荒野。在我国,无论电子或者纸版辞书在内的边疆释义往往是指国家边界内侧的广袤领土。在这类释义里,首先强调的是国家边界,然后才是领土和土地。但也有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如《百度百科》对“边疆”的解释是“两国间的政治分界线或者一国之内定居区和无人定居区之间宽度不等的地带”。且不说该释义缺乏人文内涵,而且经不起细究。首先,边疆不是分界线。我们最好在学术讨论中严格区分边境(边界)与边疆。如果仅是分界线,那就没有携带土地和其他人文方面的内涵。其次,所谓“定居区和无人定居区之间宽度不等的地带”的说法也不严格。“宽度不等的地带”究竟有人或者没人?如果没人那它与无人定居区域又该如何区别?但这一释义至少注意到:边疆并不总是主权的象征或者体现。
寻找没被现代性濡染的边疆必须回到古代。边疆一词在汉语里最早可能出现在《左传》里。如《左传·昭公十四年》:“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这段话不可作为边疆体现主权的释义。那时候全世界都没有主权观念。宋代司马光《和范景仁西圻野老》有“蚕收百箔桑蔽野,麻麦极望无边疆”的句子,这里指的是农作物没有边际,但我们也可以由此体会出边疆之文野之别的意义。
在英文里,边疆也有类似含义。美国边疆研究奠基人特纳(Frederick J. Turner)视边疆为一方“自由的土地”,它随着欧洲定居者的扩张而不断缩小。因而,边疆从有到无解释了美国的发展。在他眼里,边疆是一片等待人们开发的处女地,或者待征服的蛮荒之地。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他著名的《中国内陆边疆》一书中,开篇之首即指出:中国内陆这片广袤的土地,包括满洲里、蒙古、新疆(他称为“中国的土耳其斯坦”)以及西藏,是世界上最不为人所知的边疆之一。在他看来,这片区域不仅是中国的边疆,也是世界的边疆之一。他所谓的边疆是最不为人所知之地。显然,边疆的本意与主权没有关系。
从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有关中国宗族组织为何在东南地区特别发达的推论,我们也可以领略到传统上对边疆的理解。弗里德曼认为,东南中国之所以宗族发达,乃因其稻作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前者需要人们联合修筑水利工程;后者盖因化外蛮荒,盗贼横行,人们需要聚族自保。姑且不论弗里德曼是否正确,但他对何为边疆的理解也是持传统的文野之别看法。事实上,前现代国家的边疆就是谁也管不着的地带,也是不同文明接触的区域。美国人类学家指出,特纳的边疆视野几乎忽视了在那里生活的印第安人,边疆还应当是“文化接触区域”(cultural contact zoon)。在欧裔定居者西进过程中,欧洲文化与印第安文化发生接触引发了涵化(acculturation)现象,导致了文化变迁。这种文化变迁并不是单向的。换言之,印第安文化也流向欧裔文化。
具有主权意义的边疆是从现代国家出现后才有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过,现代国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边疆转变为边界,亦即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谓的将松软的社会边界夯实。 在汉语里,“主权”(sovereignty)是比边疆要年轻得多的词汇。上文提及,“边疆”在中国古代文献里就已经有了,但“主权”是一个外来语。所谓“主权”(sovereignty)简单而言,就是“进行统治的合法权利”(legitimate right to govern)。事实上的主权也就是执掌生杀予夺大权(de factor sovereignty as right over life),既保卫又合法地杀戮(to protect or to kill with impunity)。如果通过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有关被驱逐的生活(banished life)、去象征化(desymbolization),以及“赤裸”(“bare”)等理论透镜来理解主权,那主权就是一个共同体或者社会必须通过与外界互动来成其自我及其道德秩序。
阿甘本的洞见使我们领略到主权在实质上延续着权力的暴力的本质。如果主权必须通过与外在互动方得以存在,那么,主权在本质上就是制造边界。它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如将一部分人隔离、拘留(如纽约的艾利斯岛和旧金山的天使岛在历史上就起了这样的功能),甚至驱逐出境(deport),这是我们看到的主权在边境上的实践;从阿甘本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身体既是最高权力(sovereign power)的对象也是它的场所(site)。身体不仅涉及人身权利(habeas corpus),权力还通过赋予其一系列的权利使之具有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资格。与此同时,这些权利可以通过法令和命令被剥夺之。一旦将象征和人性从生物学意义上的躯体剥夺,那无异于将人化约为“赤裸的生命”。因此,身体是为主权操演的场所。这在战争和其他极端条件下表达得淋漓尽致。阿甘本指出,最高权力往往被考虑为中央政府,该政府表现为典章性的和(自我)管理的现代与自由的形式。
象征着主权的边界本质上也意味着保卫和“合法性”施暴,具有法的意义,这是族群边界所不具备的。为了彰显拥有主权和行使主权,边界也就有了物化的形式,如界碑、哨卡、铁丝网,乃至海关、移民局、边防等。借用阿甘本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认为,身体不仅是行使主权的客体也可以是践行主权的承载者。所以,控制边境的移民局官员、各类边防军人、警察等,俨然为主权的体现。在缺乏强烈的主权意识之前,这套实施边境控制的国家机器无由建立。现代国家的边界是国家的暴力本质的象征。我们出国旅行,跨越国境时所遇到的许多人为的麻烦,就是这种暴力的折射,也是主权的实时体现。
如同族群边界浮现是在“遭遇”他者之际,主权也因为他者的存在而存在。意识到他我之别,是边界观产生的前提条件。而无视他者存在的帝制时代,边界观自然是模糊的。在理论上,主权观念要求一个政治单元必须同时承认其他政治单元在自身的领地之内也拥有同样的权利。我们很难想象,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制时代,或者任何形式的前现代政治单元里,统治者可能具备这样的观念。
根据一位西方学者根据《清史外交资料:1875-1911》所做的统计,发现“主权”概念在中国最早应该是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从1875到1894年,每百页文件出现一次“主权”;从1895—1899年,每百页出现2.5次;从1900到1911年,每百页为8.8次。但从1902到1910年间,则每百页22次。最高的是1909年,达到了每百页37次。主权是国家现代性的重要体现,它的雏形在威斯特法尼亚协议上初具。民族主义运动崛起之后,主权俨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所以,边界固定下来之后,“边疆”要么“消失”,要么意义转变,俨然代表起主权。国家成为主宰边疆的当然主体。原先越“界”往来的主体受到了限制,原来同为一个主体现在可能因为边界的规划分为几个主体,许多所谓的跨境民族或者族群就属于这种情况。
进入了20世纪之后,中国虽然已经走上现代国家之路,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周边国家还有很长的边界未定。然而,那时已有强烈的主权意识则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对边疆问题的讨论多聚焦于“土地”与“主权”。抗日战争打响之后,对主权的关注在政界和知识界与日俱增,边疆成为了热点议题。中国学者还意识到,对自己的边疆的研究“已较英法俄日等国人士落后数十年”,并寄望于急起直追。从那时起,边疆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这一关怀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由于边疆地区居住着大量的非汉民族,从民国时候开始,边疆研究实际上就是当地的非汉民族研究。边疆就与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成为言说中相互帮衬、互相论证的概念。长此以往,致使“边疆”与“民族”在社会日常的表述中呈现出自反性(reflexivity)。 由于边疆自民国时期起就在主权的意义上予以理解,于是就有了所谓“边政研究”,亦即“边疆政治研究”或“边疆政策研究”。由于这些研究当年都服务于政府的边疆治理议程,故而是为“边政建设”的组成部分。而所有边政研究者无不将非汉民族当作重点,强调边政研究实为边疆民族研究。并且推而广之,将所有少数民族均列入边政研究的范围内。例如,柯象峰就强调:在中国而言边疆之研究,盖不仅以邻国接壤之区为限也。东南沿海之区,已全为文化进步之国民所据,自不在边疆研究范围之内。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固连接异国,且拥有数量庞大之边区民众,与本部人民间尚未臻人同文车同轨之境地,且时有隔阂,固为边疆研究之主要对象。但西南各省,文化不同之民众,虽不尽在边疆,而与汉族相处及其错综复杂,且时时发生冲突,引起边患,隐忧堪虞。其主要者,如川西北之羌戎,川西西康之西番,川西南及云贵之,川南湘西云贵之苗,云南西南之摆夷,广西之徭,海南岛之黎人等族,合计为数亦不下于二千万人,研究边疆者,固不容忽视者也。……故我国边疆之研究,应为一较广之范畴,即除边区各广大民众外,边省内地,未尽同化之民众,以及在可能范围内邻近有关之各地民族,均可以加以研究。
显然,对边疆的理解已经不仅是地理上或者政治上,而是吴文藻所谓之“文化上的边疆”——柯象峰把非边疆的非汉民族也列入了边政研究的范围内。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柯象峰提出研究边疆在方法上最好分为两部分的建议,即:以地域和以民族。前者自然是“地理的分区”。柯象峰将之分为13个地区外加“其他”。换言之,在所谓地理分区之内一共有14个类别(地区),如东三省、蒙古、热察绥、甘宁青、新疆、康藏、川边、湘西、黔滇等等。后者则称“民族的分类法”。他列出了民族名称和地理分布,凡6类民族外加第7类“其他”。同时,他也说明,这只是粗略分类,如果进一步研究尚需细化,条分缕析。如苗族仍可以分为若干种,徭亦然。藏缅族中又可分为藏人、西番、等,自成一个单位。卫惠林则干脆将边疆研究与民族学不分彼此地并列,主张在边政建设与研究中应当尽快对生活在边疆的民族进行识别,他是众多边政研究者当中少有的主张除了中华民族认同之外,还需要确认其他民族以保证多样性传承的学者。众多边政学者在边疆研究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的讨论上,也都是关于如何在边疆进行少数民族调查的内容。换言之,研究边疆实际上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张少徽就此论道:身居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社会形态上至少可以分为四大类别,即蒙民社会,回民社会,藏民社会与苗民社会。由于种族,宗教,语言,经济组织,婚姻制度,历史传说,风俗习惯等的不同,这四种形态地社会无论在内部结构上,或在外部形式上,可以说是不尽一样。…… 边疆社会的研究,在今日就是以此等四种性质不同地蒙回藏苗夷社会为范围”。
我们应当注意到,生活在边疆地区的民众,无论是文化背景为何,在边政研究中常有以“边民”谓之者。“边民”由是成为一个消解多样性的用语,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倒是与民国政府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吻合。从边政学者的著述来看,对少数民族的信任显然是个问题。例如,徐益棠曾说:“往者,论边疆问题者每推其原因于帝国主义者之挑拨,证之以当时各边区之骚动,咸或有其显明之理由。”然而, 在谈及民国之后在西南地区所发生一些事情之后,话锋一转:“乃知中国之边疆问题,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又为其根本之原因”。在边政学者的眼里,少数民族因缺乏教育愚昧落后,需要被帮助和教化,否则易于为外人所利用。边疆之所以需要被认真对待正是因为非汉民族是那里的主要居民。由此可见,对非汉民族或者族群不太信任是推出边政建设工程的内在驱动力量之一,由此映射主权才是边政学之终极核心关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如同其他新兴国家,政府在主权问题上十分重视。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了少数民族在中国的特殊性,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60%以上的版图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所谓中国地大物博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由此足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的重视。正因为意识到了少数民族在国家中的重要位置,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之前就在陕甘宁边区进行过民族自治地方的治理实践,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积累了经验。1937年起,中共先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开办少数民族班;1939年陕北公学也承担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任务。1941年则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这些经验推动了中共实施民族政策的决心与信心,建国前的1947年,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宣告成立。
建国之后,中共对少数民族给予高度重视。从1953年起,政府开始对少数民族进行识别。到1979年为止,中国境内的非汉民族被规划为55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为了政权建设需要而进行的人口分类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民族型貌。而对这些规划过的各民族,历史都需要书写。政府藉筹备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之机,开启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该调查从1958年开始到1964年结束,共历时8年。此举不但出版了关于少数民族的“五套丛书”系统性地生产了有关少数民族的知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根据社会发展五阶段说,为各非汉民族所处“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定位。国家正是根据这样的阶段性划分来细化其社会政策——对各民族的扶持性优惠政策。
对弱小民族实施扶持性优惠政策无可厚非,但人口分类所产生的后果是否完全积极就难说了。可是,要实施这样的政策又必须对人口分类,显然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张。社会历史调查之后,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状况基本通过所出版的“五套丛书”定了调。 在这些叙事里,少数民族同样在概念上与边疆互为隐喻,如影随形。而且,由于各单一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定位以及对之的宣传,也加强了社会公众对少数民族罗曼蒂克的想象。关于少数民族的描述与叙事,总是与他们比汉民族落后之类的表述联系在一起,而且不仅经济文化落后还总是地处边疆等等。这样的表述对公众在认知上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
边疆与民族互为表述,使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类别(范畴)。而每一种范畴都要有其外沿与内涵,于是,边疆作为政治空间范畴,其内容除了主权之外就是民族;而“民族”作为类别,“边疆”也就成为其存在的“场所”。于是乎,这两个范畴完全成为政治性的。而支撑这样的分类范畴正是族群性认知转向所提倡去除的群体观。这一提倡者希望新的范式来取代固有的,已然沿相成习的旧有范式。在固有的范式影响下,人们往往一想到族群性就马上考虑到群体,群体成为了族群性的容器,这就固化了我们的思维。这种情况与近年来一些人类学家对文化概念的反思异曲同工。这些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应该“去狭隘化”(deparochialization)。我们不应再将文化视为某种框定的实体(a bounded entity),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化,都已经不再纯粹,都包含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或者文化成分。
考虑到边疆作为文化接触区域,这里有着丰富的文化和族群多样性,承载这些文化多样性的群体各自都成为了在这一区域内活动的“次国家群体”,其中有不少与相邻国家的同类群体还共享文化,这当然会使国家觉得边疆在主权上的重要性。现代国家的要务理应是民生问题,然而,由于众多有着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的民众生活在边疆地区,这就使国家在治理这样的地区时常常会处于两难窘境。如果将领土主权为第一要务,管控自然会是这一地区主要治理方式。如果民生是第一要务(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理应如此),把主权放在次要地位,又会使国家不太放心;如果二者兼顾,那就经常出现如何平衡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不要把边疆视为主权的象征,而应当视为不同文化接触和发生联系的场域。其实,民国年间不少边政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他们的不少讨论中都表达这样的看法,边政建设虽然是国家的边疆工程,但研究如何提高边疆非汉民族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及教育应该是首要的。其弦外之音即是,只有边疆各民族安居乐业,边患才能消弭。杨成志、吴泽霖、卫惠林、胡耐安等人莫不秉持这样的观点。
共存的国家与次国家主体
前文提及,现代国家的建立使边疆转变为边界。我国的边疆泛指边境的内侧区域,该区域远离中心。就此地理性意义而言是为边缘(periphery)。但在人文意义上,这片区域面积之大,又会让人觉得称之边缘不甚妥当。显然,我国的边疆概念不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从边政建设时期开始,为建设民族国家,边政学者即有人提出应该把所有有着较多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都视为边疆。这种想法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这也是许多人都有的一种强迫性联想,这种联想造成了边疆与民族在表述上的自反性现象(the phenomenon of reflexivity),从而也会影响到治理的效果。
作为接触区域,当今边疆地区的主体主要是国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次于国家的主体,它们每天都在“遭遇”——与国家主体遭遇和次国家主体之间的“遭遇”。这些次国家主体有些因为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划分而分布于不同国家的领土内。有鉴于此,我们就应该考虑到,如果在这样的接触区域内,国家如果把对主权的重视置于民生之上,良莠混杂的次国家主体之间的接触就有带来消极后果的可能性。
对于研究者而言,对多样性不同表达方式的探讨,远比讨论群体(groupism)更有意义。巴特认为族群性是一种分类实践的理论,使许多学者关注到国家的人口分类对群体认同建构意义非凡。但是,在另一方面,如巴特和其他学者所揭示的那样,人们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也在进行分类实践,而他们的分类可能与官方的分类不尽相同,甚至全然不同。由是推知,多样性越丰富,意味着主体越多。在边疆场域,这些主体都在国家这一主体的范围内,所以我才把它们称为次国家主体。它们包括各种族群、民族、宗教群体,以及其他有着各式各样的身份认同的群体。
从认知的角度讲,“类别为我们结构了世界,并使它有秩序”,因为我们的认知就是由无数的类别所构成。那些持续存在的分类实践都是习惯性的,但它们却是我们理解他者与自我的关键所在。这些类别我们只能通过观察边界是如何在人们的互动中显现或者制造来感知。对于外来的观察者来说,包括国家主体在内的许多主体,每天都在“遭遇”,这些“遭遇”都提醒各主体意识到自我,这样就产生了边界,造就了主体间性的现象。因此,体会多样性的不同表达远比强调某一“群体”更有意义。我们最好不要把边疆视为主权的象征,而应将之视为不同文化联系和接触的场域。
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治理术的分析告诉我们,所谓治理术就是治理者能使被治理者对治理者有信心,相信在治理者对治理下,他们对生活是有盼头的。作为政府的艺术的治理术,民生福祉是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 对人口的分类当然是治理术的一部分,但为推行特定的社会政策对人口进行归类配套,把类别固着于公民身上使之成为一种个人的先赋身份(ascribed status),并不见于大多数国家。理论上讲,这样做有助于资源配置,但在具体实施上却依然有着非常多的问题,而且也容易引起争议。所谓的认同政治也就经常产生于这样的环境里。
一旦人口分类与区域空间分类结合在一起,主权为主还是民生为主,权重一定有所不同。边疆作为主权国家的政治地理或者空间类别,必然成为主权的象征,这种认知必然影响决策者的政策走向。我们都同意韦伯的说法,信仰同一种宗教的人彼此间存在着亲和性。生活在边疆的大量非汉民族有一些与境外国家的主体民族文化背景相同,更有些与境外一些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这些背景性的历史与文化条件在过去可能不至于引发严重问题,但在全球化的当下,情况就变了。例如,恐怖主义者往往利用宗教来为他们的暴恐行为提供合法性,而信仰同一宗教的信众就可能成为他们的动员目标。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有赖于高科技的各种信息流通四通八达,这是全球化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具有消极的一面。许多极端势力通过这些全球化时代的技术急剧扩张,通过高科技手段传播它们的极端思想。费孝通曾指出,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而且还是问题的全球化。全球化的一些维度使这些反面势力得以在边疆成为另一种主体,如果从边界视角来看问题,这些反面的次国家主体与其他的次国家主体“遭遇”时,其他次国家主体与之遭遇之际所感受到的边界或者制造的边界究竟是怎么样的?这是值得治理者和研究者思考的问题。难道仅仅因为宗教相同彼此之间就不会产生边界或者制造边界?但是如果边疆治理沦为以管控为主,在治理上根据人口分类而区别对待,情形必将每况愈下。
国家的人口分类创造了诸多次国家主体,这些次国家主体与原先存在着的其他次国家主体并存、重叠,或者部分重叠、交叉,由此产生的认同其光谱色泽之丰富可能在我们的想象之外。因此,对于研究者而言,我们既要尽量不被这些类别所束缚,还要探寻其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民众自身的类别,这在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尤为重要。族群性研究的认知转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去类别化(de-categorization)地在微观的层面探寻互动之中人们如何进行类别实践,如何考虑他们多层的次国家认同,摆脱将所有涉及主体性的现象都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中思考。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像巴特那样,发现族群性也能被操控在那些声称代表本族群或者本民族利益者的手里。但他们真是代表本民族利益或者仅仅是利益相关者?巴特认为他们大多是后者。
结语
综上所述,巴特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巨大贡献在于关注到个人的选择动机,在他眼里,人是理性的,他们并不是像在结构功能主义眼里那样地被动地束缚于结构中,巴特因此成为结构功能主义的终结者之一。他一以贯之地对个体的考察使他转到族群性研究之后,很快地注意到边界的问题,这种边界同样是理性选择而来。他们在遭遇中“制造边界”或者“维系边界”,该概念与“语境”(context)一起,构成了族群性研究上的两个重要支点。从而,巴特将族群性视为人们的分类实践,而不是共享某些文化特质,认同,从此在族群性研究上居于中心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维系边界实际上就是分类实践,在巴特的影响下,族群性研究出现了认知转向。学者们注意到了既定的分类和国家分类如何影响到人们的族群认同建构和认同政治发生,也同时关注到人们日常生活里往往还实践着与国家的人口划分类别无关的分类。认知转向极大地丰富了族群研究的内容。族群性问题也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在我们语言里,今天的“边疆”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大异其趣,它从蛮荒的文明未至之地成为了主权的具体体现。但在这一空间里有着丰富的文化与族群多样性, 这些多样性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次国家主体,并且每日都在互动、“遭遇”。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是,因为生活在这里的群体,有些在边境的外侧是主权国家的主体民族,有些则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不同的主权国家内。更常见的是,这一空间里的许多次国家群体——不同的族群或者民族,与边界外侧其他国家的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共享一种宗教。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在各类研究和各种文化表述中,边疆总是与民族如影随形,因而在许多人的观念里,边疆已然与民族彼此间具有反身性,它们互为表里、相互隐喻。这样的认知影响着决策制定者与决策者的思路走向。如果考虑偏重边疆的主权意义或者象征,那么在当地的治理上必然以管控为主,而把现代国家首要考虑的民生置于从属的位置。这样做必然会对大量的、共存于这一空间里众多的次国家主体间的互动发生影响。然而,现代国家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民生都应是第一位的。
前文提及美国人类学家在泰国北部发现,当地自称为Lue的族群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时,对泰国的国家认同度很低。当时,由于交通不便,他们的居处显得比较闭塞,同外界接触有限。国家与他们的联系仅仅限于收税的场合。他们觉得税交给国家是白交,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的族别认同(ethnic identification)阻挡了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但在1989年的回访时,同一作者发现,Lue已经广泛地与外界联系,国家已经被视为提供教育、就业机会、健康服务、农业信息、发展基金的善举源头。作者写道:“村民们现在更多地觉得他们是国家公民,而不是弱势的少数民族群体”,而且他们也不再对位于中国西双版纳的所谓“老家”(“Old Country”)抱有“怀乡”之情。但作者却也遗憾地发现,Lue的文化独特性却也渐渐地融入了泰国国家主流文化里。这是一个重视民生加强了国家认同感的明显例子。相信政府如果在提供帮助的同时,鼓励他们保持自身的文化传承,他们的文化独特性当不至于面临消失。
族群性研究的认知转向提醒我们从微观上探寻人们的分类实践,这种分类实践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他们未必携带族群性概念所指涉的族群互动中的消极面。正如巴特所指出的那样,在微观条件下,人们的理性选择更多地考虑到个体的民生问题,但这并不一定包含有群体主义(groupism)的内容。因而,巴特的理论其实告诉了我们,边界是流动的,这样的流动建立在个体选择的基础上。然而,也正是这种流动性,“边疆”具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和张力。我们的“边疆”应当“去边疆化”,而“去边疆化”的唯一通途就是关注民生,通过切实的民生建设来促进地区的稳定。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