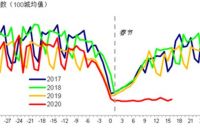2017年7月12-26日,长期主张“脚底板下做学问”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先后密集走访了瑞典斯德哥尔摩、芬兰赫尔辛基、俄罗斯圣彼得堡、爱沙尼亚塔林、拉脱维亚里加、丹麦哥本哈根、荷兰阿姆斯特丹、比利时布鲁日、英国伦敦、意大利罗马等地,参加了第三届东西方经济文化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沿途还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等多位政治人物、多位企业家和多位著名学者深度交流沟通,对中国崛起、企业国际化、全球社会发展等有了全新感悟。7月28日晚,王文回京后力邀同行的徐二明教授、谢耘教授第一时间将相关体会与公众分享,现整理王文讲座内容精华部分编发如下。
各位朋友周末好,感谢各位周末光临人大重阳,一起与我们探讨实地调研十个欧洲国家后的一些感悟式的结论。
我一直主张“脚底板下做学问”。现在这个年代可谓是“知识贬值,见识增值”的时代,因为获得知识的成本几乎为零,要想获得知识,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当然,百度不能做学问,不过,很多学者以Google做学问。相比之下,获得见识需要非常高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精力等。有时候,知识和见识之间有很大区别,甚至是截然不同的。
在知识层面看,一提到我们这次去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百度或者Google上搜,一搜“北欧”基本上都是“北欧模式”,基本的内容是小国寡民、福利高、收入高、幸福国度等等,但我去了以后感受却比百度谷歌上更丰富、更多元、更复杂。
不过,知识层面对北欧的正面是有现实基础的。25年前,著名美籍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写过一本书《历史的终结》,就把把历史终结点的榜样国家视为是北欧的丹麦。去年,差点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桑德斯也曾经讲过,我们美国未来发展就要像丹麦、挪威、瑞典那样看齐。前年盖勒普调查,155个国家眼里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北欧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与我们一路走过看到的表面现象也是一致的,街景很平静,天空很蓝,郊区很美,老百姓安居乐业,一幅中国古代道家所言的“小国寡民”状态。但深刻思考,问题可能更复杂一些。
在我眼里,大概有三点特殊的感受:
第一,满大街看到相当多老人,显示了非常严重的老龄化现象。无论是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哥本哈根,服务生、售货员、司机、教堂礼拜者、广场步行者,五六十岁以上的比例相当高。回想一下,的确,原来北欧国家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冰岛等北欧五国共计2600万人口左右,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近550万,约占20%。这什么概念呢?按联合国的标准,如果65岁人口超过7%,算“老龄化社会”,14%就是“老龄社会”,超过20%就是“超老龄社会”。
当然,有媒体也夸挪威、瑞典等的平均寿命在85岁左右,都是正面报道,但另一方面,由于预期寿命增加,退休人员领取养老、医保以及其他服务的时间拉长,使得国家财政承受的压力陡增,国家不堪重负,发展成本加大,北欧国家的债务上限屡创新高。2011年欧债危机,第一个破产的国家就是北欧国家冰岛。芬兰等国家的债务也已超过了欧盟的警戒线。从这个角度看,恐怕我们要更全面地看“幸福国家”的定义了。
第二,因为老龄化的严重,整个社会福利体系近乎终结。我一路上买了一些东西,在最后一国退税,发现北欧国家的税率是最高的。再核实,发现北欧国家税收在50%-60%。对此,我们知识体系中认为,税率高是社会保障高的表现,的确,北欧国家瑞典、芬兰、丹麦社会保障费用占GDP比例达到40%以上,其他国家像日本约25%,美国约18%,中国可能在10%。税负比较高的确是福利社会高的基础,但理论上看,这种模式并不能持久,而会产生竞争力的下降、社会活力不足。
根本原因是,诱使相当大一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工作,养了许多懒汉,有人把他称为“30%的人养活了70%的人”。我在赫尔辛基、里加、塔林街头,的确看到许多年轻人在做街头表演,提琴、舞蹈、古乐器等,但有一搭没一搭的,表情轻松,目光却是空洞,这实际上是社会慵懒症。数据显示,在瑞典一度有年均400万雇员没上班,占人口40%的国民靠休“病假”、领取各种社会福利金生活。病假补贴占到瑞典公共总支出的16%,失业率持续上升。由此再审视知识层面的“福利社会”概念,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更糟糕的是,如瑞典对收入最高阶层的征税率达到84%,资本外流严重,企业成本上升,人才流失严重,创新能力下降。近十年来,北欧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持续在2%上下徘徊,低迷不前。北欧最著名的三个企业品牌:诺基亚、爱立信、沃尔沃。前两个最新年报显示,2016年同比收入均下降了14-17%。一度垄断手机市场的诺基亚,未能跟上智能手机创新大潮,已退出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沃尔沃的利润增长了66%,沃尔沃人透露,主要原因是2011年被中国公司收购了。
不过,据《经济学人》报道,瑞典已在改革,把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67%降到2013年49%。个税、财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纷纷下降或被废除,种种最新的事实已说明,传统知识层面上的“北欧模式”正在终结或被改革,不再是当年人们内心的拥趸。
第三点感悟是,这一路十个国家,我们有不同的向导,但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一国都有向导提醒我们,要小心扒手,社会治安令人堪忧。在圣彼得堡,曾发生了挂在胸前的照相机大镜头盖被人不知不觉间顺走的案例。在罗马,“扒手”更是重灾区,听说中国人每两三人里就有一个在罗马被人割了口袋、偷抢了包的事例。过去,我去巴黎、维也纳,都曾被提醒要小心扒手。
当地人把这种社会治理的失效归因于“全球化冲击”。难民和中东欧的移民(如吉普赛人)大量涌入北欧、西欧国家,产生了大量社会问题,进而导致了主张极端排外的北欧极右翼政党支持率的上升。目前,瑞典极右翼的政党已是议会的第三大党,丹麦极右翼政党已是第二大党。
极右翼政党有很强的民意基础。比如,这次我们在丹麦参观某城堡,走错了路,从出口进去了,看门的一位大妈就相当不友好,对我们吹鼻子瞪眼睛,好像欠他们什么似的。多年前,在北欧另一个富国挪威,乘坐公交车,我与同行的中国朋友坐在最后一排,当时刚放学,几个高中生,人高马大上车,看到后座有几个外国人,就一边看我们一边窃窃私语。下了车以后,集体朝我们座位边的窗户上吐唾沫,场面较为惊恐,行为相当粗鲁。据说对中国人还算好一些的,对穆斯林就更受歧视。所以,欧洲正在面临非常强烈的“伊斯兰报复”。一些城市如布鲁塞尔、伦敦等穆斯林人口极剧上升,甚至有的区域90%人口都是穆斯林。有一本书中曾记述把欧洲称为叫“欧拉伯”(Eurab),是Europe和Arab的词合在一块儿,意指欧洲的阿拉伯化。
最后一点感悟是,一路见证了中国影响力在欧洲的提升。在圣彼得堡冬宫门前、彼得大帝像下,中国旅行者是可以用人民币直接购买东西的,这说明背后是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清算与汇兑体系挂钩的。在北欧、西欧等每个人多的地方,都会有当地人用“你好”、“谢谢”、“再见”与你打招呼。这些年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是明显的。
这次还非常有幸见到了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和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卡梅伦在英国脱欧后辞职,很少见到他的消息。这次他公开讲解了许多看法,包括要向中国学习基础设施建设,反思民主政治等等。
但我印象更深刻的还是萨科齐总统。他公开有一场大的讲座,我向他提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2008年你当总统的时候,也没有保护好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还见了达赖喇嘛,后面几年中法关系特别好。是什么原因让您对后面几年中法关系做了调整和扭转?”他一看有些挑衅性,立刻来劲了,说“不要以为2008年我对中国不好,2008年我是第一个表示来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许多欧洲大国都没来。”“为什么巴黎没保护好火炬?因为巴黎市长是我的反对派,他是在反对我。你应该去问他。”“为什么我要见达赖喇嘛,因为没有任何人决定我见谁和不见谁,但我也很顾及中国的感受,我没有在巴黎总统府见他,而是在波兰见他”等等。他很坦诚,给我很直率的印象。第二天早上,有机会与他早餐,他一见到我就说,你的问题我很享受,我喜欢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也说,是啊,那么多的人,给了您一个机会回应。
后来,在伦敦,萨科齐还与卡梅伦做了一场对话。他对中国的看法也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要向中国学习最重要的事情是,愿景!他特别欣赏中国领导人每五年、每十年给国民的许诺,让国民能够有更大的可能性实现生活愿景。而这些愿景正是国家发展的希望。另外,他还讲到,全世界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是不确定性,但中国很确定。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极其难以驾驭,非常佩服中国领导人的驾驭能力。
互动环节:
问:大家好!我来自清华大学,我有个问题想提给王文老师。您这次见到了萨科齐总统,也见到了卡梅伦,这都让我们感觉很高大上,去年您参加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也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我的问题是,刚才你已经点评了对其他大国元首的印象,特别想知道您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印象。
王文:这个问题还是蛮敏感的。(众笑)不过,人大重阳受到过三十多个国家总统、总理接见。坐在现在这个会议室位置上的总统总理就有近10位,如加拿大前总理马丁、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等等。中国学者越来越自信了,能够与各国总统、总理侃侃而谈。比如,这次主持萨科齐与卡梅伦对话的是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他坐中间,很自信,非常值得学习。国家崛起伴随着中国学者的崛起。
随着自信心的恢复,我们看世界的眼光也变了。过去,我们老说中国制度有劣势,现在反过来看中国制度的优势。长期以来,在知识层面受西方人影响很大,一提起美国,书上就写着“美国三权分立多么棒”,政治课、马哲课老师课堂上也会这样讲,说美国总统要是干不好,四年以后就会被选下来,显得很有制度优势性的。现在反过来看,他是制度劣势,因为干得再好,8年后也得下来,管他洪水滔天呢。最典型的,是小布什总统8年两场战争,耗干了国库。
选举制上台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执政者思想准备得不充分。半年多前,有张特朗普胜选后低头沉思的照片在微信里流传,配图文字大体是“原来只是想玩一下,现在竟被选上了,怎么办”。结果显而易见,他毫无准备被选上,半年多后的今天,他内阁主要岗位还有约一半没有填满。被填满的,还辞职、被炒鱿鱼得不少。前段时间,特朗普高调地说,美国愿意加入“一带一路”。我问几位美国官员什么意思,他们几乎一致回复是,“哎呀,千万不要相信我们总统的话,他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可见美国高层政治有多么地无序。
刚才几位老师也都提过萨科齐和卡梅伦都在反思民主、反思制度。的确,中国制度当然还是需要大量的改革,但从领导人的素质上看,中国还是要比纯民主制下的欧美国家强得多。其实,大多数人都与我有相似的感觉,在中国体制下,要干到正司局、副部级以上,那真是需要相当相当强的能力,非一般人能及。
我一直主张国与国平等,但从体量上看,我这次去多数国家都只有几百万人口,大量相当于咱们一个地级市。而中国国家领导人几乎都处理过几千万人口的省份一把手履历。萨科齐总统这次也明确说,中国领导人太厉害了,那么多复杂的矛盾要处理,这里体现了极强的政治优势。
问:今天听了王文兄的介绍收获很大,因为我们也准备带着中国大的品牌走出去,所以这个活动对我们也很重要,我想请教一下诸位老师,现在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情况,丹麦、瑞典、挪威总体情况怎么样,走出去有什么问题,怎么样走出去会方便?因为我们后面会有2000多个大的品牌随着我们走出去,所以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王文: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展很快,但过程很不容易。比如,近些年海航成为德意志银行最大股东,并购了希尔顿酒店,这相当于是中国工商银行、长安街沿线的酒店都被外国人并购了,中国人会怎么想?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的狙击、国外舆论的怀疑是必然的。中国引领的全球化,实际上是由中国企业为重要载体的,但这个中国往外走的过程相当漫长,也很艰难,但我相信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问: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介绍,知识的盛宴,我来自环保部,也是人大的毕业生,我提个问题,这次我们到欧洲访问之后,感觉到欧洲和中国在未来在全球治理领导力方面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文:我再补充一下,刚才谢老师讲的特别好。美国前总统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写过一本书,讲全球进入觉醒时代,不只是西方国家,1500年以来,技术、制度、经济、政治都是西方文明在领先全世界。21世纪以后,全球觉醒,一是西方从过去的傲慢中觉醒,正在深刻反思,二是发展中国家在觉醒,从盲目崇拜西方到发现自我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看来要真的感谢秦始皇,欧洲版图和中国差不多,现在却分成了二三十个国家,因为中国大一统制,有统一文化、文字、语言。欧洲却是持续分裂,直到二战后才逐渐走向统一进程,但这个进程比中国晚了两千年,且未来命运未卜。欧洲一体化对全球治理的示范作用,是被我们建构出来的,是被我们崇拜出来的。
这里我用一个有意思的亲历故事来说明,三年前去巴黎,发现有越来越多拉三轮的,像北京胡同的那种,我坐上一次感受,从凯旋门到卢浮宫5美元。我于是与拉三轮的那位年轻人攀谈。他说自己25岁,匈牙利乡下人,巴黎第四大学毕业,会德语、英语、法语,现在正在学中文。我问,为什么学中文?他说,在网络上找到一个中国女友,在上海工作,是一位公司总监,准备去找她。我问,中国女朋友知不知道你在拉三轮?他说,当然不会让她知道。现在一个月能挣1500欧元,500欧元是饭钱,500欧元住巴黎地下室租金,存下来500欧元正在攒机票钱飞到上海,然后就不用自己花钱了。我实在无意取笑上海或者任何女性,只是讲述了我的亲历。背后是中国人看待外国人的某种社会现象。(笑)我当然支持自由恋爱,老外有许多特别优秀,我只是说,中国女孩要警惕外国男帅哥是不是屌丝。(笑)
这段亲历让我思考,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到巴黎、伦敦等地打工越来越多,这是英国要脱欧的重要背景。许多英国人都说,英国摆脱了欧洲,但拥抱了世界。而这种移民的现象,事实有点像20、30年来甘肃、四川、安徽、重庆等地农民工跑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打工。中国优势在于,在大一统体制下采取“先富带动后富”的区域递进发展战略,一步步解决贫困,走向小康。现在,重庆就脱掉了“农民工输出比例最多省份”的帽子,因为重庆产业发展,如PC机制造等,农民可就近找到工作,收入递增。但在欧盟却很难解决,文化分散,政策分权,政治分化。如果说15年前欧盟因为一体化进程,还对全球治理有着示范性作用、典范性作用的话,那么,现在,欧盟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恐怕在极剧衰弱。现在英国脱欧了,马上可能荷兰想脱、意大利想脱,西班牙也想脱,不光西班牙想脱,西班牙内部也想独立。如果解决不了集权统一等政治改革问题,我对欧盟是看低的。
再说远一些,过去很多人都在鼓吹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现在看来,改革开放才是普世价值,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欧洲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美国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欧洲需要开放,美国也需要开放。近期有一部纪录片叫《将改革进行到底》,我上周还在《人民日报》还对此发了评论文章,明确讲“不改革,死路一条”。中国有很多不足与缺陷,但中国和欧美国家相比,它的特征是“具有可改革性”。而只有不断改革,中国才真正有未来,才会对全球治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