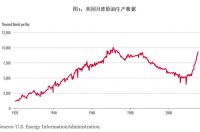特朗普上任以来,尤其是2018年以来的半年多时间,美欧关系出现了重要变化。围绕伊朗核协议存废、关税与贸易、欧洲一体化、北约前途及美欧各自承担的军事安全义务、欧洲国家是否应增加防务开支、对俄政策、环保气候问题及二战结束以来确立的国际制度等问题,美欧公开互“怼”,针锋相对,其性质已经不是所谓同盟内部的“摩擦”可以解释的。当前美欧矛盾在性质上是“事务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是一时一事矛盾还是反映长期趋势?本文拟作出回答。
美欧矛盾加剧是世界大变局的反映
当前世界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美国学者扎卡里亚有所谓“500年未有之变局”的说法,认为世界正在发生过去500年间的“第三次权力转移”;中国学者袁鹏则称之为“近四百年来的第四次历史巨变”。五百年也好,四百年也好,其观点与思路具有一致性,世界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当前世界大变局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带有一定转折性的变化。过去500年美欧等西方国家一度占世界经济贸易总量、制造业产值及军事实力总和的五分之四以上,目前大体降至一半左右。二是世界地缘政治重心东移到太平洋地区。过去500年来欧洲一直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大西洋因其连接美欧的枢纽地位,而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洋。现在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总量、制造业产值及军事力量总和已经超过欧洲,连接亚太与北美的太平洋较之大西洋更加重要,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已经由欧洲—大西洋地区转移至亚洲—太平洋地区。三是国际秩序面临剧烈的调整过程。战后以来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是在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如今西方实力和影响力下降,以中国及亚太国家为主的非西方国家加速崛起,过去主要反映美欧等西方国家意志与利益的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已经严重不适应变化中的世界,调整过程则相当剧烈和艰难。四是在全球化更广泛、深入地向前推进的背景下,过去数百年盛行的、主要反映美欧等西方国家意志与利益诉求的国际观、价值观,包括人们有关战争与和平、安全与发展,以及有关发展模式及国际合作与竞争、大国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等,也在变化过程中。
面对世界大变局,美欧的认知及其反应模式出现了重大差异。首先,对于全球力量对比变化,尤其是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美欧的感受及其受冲击程度与反应模式是不同的。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来看,美国经济总量已经由二战结束时的占世界近一半降到冷战结束时的三分之一,目前则降到四分之一左右,但美国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经济、贸易、金融、科技和高端产业实力,尤其是其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依然独步全球,较排名第二的中国也高出很多。换言之,世界大变局,尤其是国际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重心东移,对美国的影响依然限于量变范围内,而未涉及质变,美国依然有能力搞单边主义。欧洲则不同。所谓西方实力下降主要是“做空”欧洲,是欧洲“出让了”较多的份额。目前世界经济大国前三强已经不见欧洲国家的身影;全球企业500强中的欧洲企业越来越少;非西方国家增加在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股权和投票权主要是美国压欧洲国家“转让”其固有份额,美国并无损失;与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与冷战期间相比,欧洲英、法、德等国的军费开支、常备军数额都在下降,不管其是否愿意,它们都在从二流军事强国向三流军事强国“衰退”。总之,世界大变局背景下的全球力量对比变化及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对欧洲的冲击是质变而不仅仅是量变,美国则相反。这种认知及实际冲击的不同,必然会对美欧各自的政策反应模式产生不同的影响。
其次,对于世界地缘政治重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亚洲—太平洋地区,美欧的认知与政策反应模式也是不同的。美国地处两洋之间,欧洲—大西洋地区是其“左邻”,亚洲—太平洋地区则是其“右舍”。就地理空间而论,无论是转向“左邻”,还是转向“右舍”,对美国并无地理上的不方便。换言之,美国很容易“华丽转身”,适应世界地缘政治重心转向亚太的新变局。实际上,美国与亚太国家的贸易额已经超过美欧贸易额;美在全球的五个主要军事同盟有四个在亚太(美日、美韩、美澳、美菲同盟),美国与日、韩、澳、菲的军事同盟关系已历数十年之久,近年美日、美澳同盟还在加强而不是削弱,美与新加坡则存在准同盟关系,与印度的军事合作也日益加强;美中贸易额超过美国与世界上任何单一国家的贸易额;美国在亚太的“前沿驻军”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已超过驻欧美军。欧洲则不同。世界地缘政治重心东移意味着欧洲失去其在全球的地缘政治“重心”地位,正在逐渐“失宠”于美国,而美国不可避免会“见异思迁”。欧洲要适应这一新变局,就要改变其二战结束以来半个多世纪依赖“大西洋关系”的传统,走出“惯性”,调整思维,真正把崛起的亚洲及非洲当其近邻,而不是继续抱美国的“粗腿”,生拉硬拽地把隔着大西洋的美国当作自己的邻国。这要求欧洲人回归16世纪以前的历史记忆,即把如何处理好与亚洲、非洲等大周边地区的关系当作头等大事,其中如何处理与伊斯兰世界这一历史和地理上的“近邻”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好对华关系是关键。目前欧洲对“一带一路”和中欧“班列”采取积极姿态、坚持维护伊朗核协议的合法性、批评美把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以及援非政策与美国都持不同看法,等等,都反映欧洲在以与美国不同的方式,按自己的利益认知与需求,调整政策,以适应世界地缘政治重心东移的新变局。
再次,关于适应世界大变局的国际观调整,美欧也有不同。比如,对于战后以来形成的国际制度,包括联合国体制、世界贸易体制、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政治经济安全制度安排,欧洲采取维护立场。欧洲英、法等国是这些既有国际制度的创制者之一,这些制度本身也符合欧洲国家当时、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国际利益,在欧洲总体实力和影响力下降的情形下尤其如此。如要对国际制度“另起炉灶”,以欧洲目前的实力与影响力,不会在新制度创制过程中有过去一样的发言权和一样的席次排名及利益配置。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对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制度问题上的种种“任性”采取了明确抵制的态度。美欧在国际贸易问题、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的分歧,也反映了二者对国际制度何去何从的不同态度。再如,进入21世纪,不但大国标准、大国“圈子”在变化,大国的影响力、对国际事务的操控力以及争做世界大国的吸引力和边际效益等,都在急剧下降,这是世界大变局更深层次的内容。欧洲人战后实施欧洲一体化,是想在“国家规模”上能与美、苏平起平坐,以保持欧洲国家的世界大国地位。现在欧洲国家不但认识到做世界大国力不从心,也认识到做世界大国的吸引力和边际效益下降的事实与基本趋势,因而其“大国梦”淡而又淡,并相信美中俄等迟早会有此认识。因此,欧洲国家更渴望一个和平、稳定、能够进行和平商业竞争与合作的世界,不再追求军事强国地位,对增加军费持消极态度,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及“战争准备”问题上与美国不同调、不同步。
美欧矛盾直接源于其利害关系发生变化
美欧之间不仅对世界大变局的认知与感受及反应模式不同,二者间也存在诸多直接的利益冲突,而这些具体利益层面的冲突也是世界大变局作用于美欧关系的具体体现。
其一,在国际大安全问题上,欧洲开始把大周边安全视为其最主要的安全关切,这是对十五、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前欧洲安全关切的历史回归。自希腊、罗马时代开始,一直到“地理大发现”以前的中世纪,欧洲北部面临各草原游牧部落、“蛮族”入侵的威胁,在地中海以东、以南则面临波斯人、奥斯曼土耳其及伊斯兰世界的威胁,八次十字军东征证明了来自地中海以东、以南的威胁如何曾使欧洲人疲于奔命。按照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富勒的分析,1571年欧洲基督教国家联军在勒班陀会战中大败奥斯曼土耳其陆海军,才真正扫除了“自从1453年以来,整个东欧和中欧”所笼罩的伊斯兰世界对“基督世界”的威胁;而到1697年,欧洲人才“最后根绝了土耳其人对于欧洲的威胁”。
如今,时隔四五百年,欧洲在地中海以北、以东、以南的大周边地区再度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强势、伊斯兰世界的反西方诉求与北非乱局,其中如何解决好包围欧洲东、南两面的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更是重中之重。单是中东、北非乱局造成的百万难民“入欧”就使欧洲在安全及财政上不堪重负。而要解决这一周边大安全难题,欧洲不可能像四五百年前一样靠武力解决,欧洲也没有武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实力和意志。这就决定了欧洲人在伊朗核协议问题、叙利亚问题、美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问题及对俄政策问题上与美国的不同步、不同调。美国则不同,美国仍然坚持把中、俄等大国及伊朗与伊斯兰世界视为其安全威胁,对伊斯兰世界尤其以强势打压为主。特朗普政府不顾欧洲国家、伊斯兰世界及中俄等大国的反对,强行把美驻以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不惜承受国际信誉损失而撕毁伊朗核协议,摆出了只要保住以色列这一战略据点,就不怕大中东及伊斯兰世界再陷乱局的姿态,明显不在意欧洲的大周边安全关切。就此而论,美欧已经不仅是在大中东问题上各说各话,而是在欧洲安全关切上各说各话。
其二,在经济及贸易关系上,2016年美欧货物和服务贸易额超过11000亿美元,表面上互为头号贸易伙伴,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尽管如此,欧洲国家内部互免关税、欧盟国家内部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60%以上,可以说欧洲是美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却不是欧洲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欧洲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本质上大多在欧洲内部。在持“重商主义”观念的特朗普看来,欧盟及欧洲国家内部搞关税互免实质上构成了对美国的贸易歧视。特朗普祭出双边贸易和双边谈判牌,反对多边贸易体制,不仅是针对WTO和现有的国际贸易体制,也是直接针对欧盟体制下的欧洲内部关税互免现实。特朗普不时发表反对欧洲一体化言论,甚至公然鼓动法国等国退出欧盟、与美直接进行双边贸易谈判,以及为英国“脱欧”拍手叫好等,都根植于欧洲内部贸易额高于其外部贸易额、美国自认为受到了欧盟“贸易歧视”的偏见。
此外,特朗普还认为欧元与美元形成竞争,欧洲在高端产品方面,如高端汽车等,与美国形成竞争,欧洲依然是美国的强劲经济贸易与金融竞争对手。对欧洲国家而言,在现有多边贸易体制下,保持国际贸易额继续稳定增长是欧洲国家维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生命线。欧洲国家不仅要在欧洲一体化的机制下继续推动欧洲内部贸易增长,还要在现存的多边贸易体制下维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进一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伊斯兰世界和非洲扩大贸易份额。欧洲国家因而更希望维持现有的以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对特朗普政府攻击现有的多边国际贸易体制、攻击WTO、唱衰欧洲一体化、大搞双边贸易谈判的主张等,欧洲心存警惕,必然要直接反对。这也导致欧洲国家对于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国家钢铁及铝制产品征收高关税、以强势美元打压欧元的政策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直接反制措施。可以预见,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对欧洲国家打关税牌和双边谈判牌,欧洲依然会针锋相对、步步为营,与美继续互“怼”。
其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美欧不但有认知差异,而且直接影响其利益认知和政策选择,尤其是直接导致二者对北约及军事安全投入的政策分歧。二战结束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美欧同盟主要是军事安全同盟,这是美欧全面合作关系的基础。冷战时期,美欧对战争与和平的认知,尤其在军事安全威胁来源、性质的认知及其应对方式上具有一致性,即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与意图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美欧及整个西方世界的主要安全威胁,美欧为此而建立北约,维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不仅美国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也尽其所能地维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安全同盟为基础,美欧在经贸、价值观念及国际事务上也保持总体上的“步调一致”,冷战时期建立的“七国集团”及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即为证明。
冷战结束后,美欧同盟关系的安全基础出现变化。苏联解体及俄一度倒向西方,使美欧同盟不再以应对新的世界大战为指向,军事安全政策不再保持一致。美国继续维持超强军力和巨额军费开支,而欧洲主要国家,包括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军费开支、军队数量和军事实力则一再裁减、收缩。特朗普上台后,一反奥巴马政府关于裁减军力、军费和相对收缩的政策,为讨好美国军工联合体而大力增加军费,加强军力,美国各军种都在增编扩员,尤其计划未来30年投入万余亿美元用于更新核武库。而在欧洲各国,和平主义占上风,美国所渲染的俄罗斯对欧威胁,在欧洲看来主要是政治关系问题而非军事安全问题,美国难以刺激欧洲国家像冷战时期那样在意俄对欧军事安全威胁,并以军备竞赛对抗军备竞赛。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更在意恐怖主义袭击、难民危机、跨国犯罪、环保气候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而不太相信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尽管特朗普在2018年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力压欧洲国家将其军费开支增至其GDP总量的2%,但欧洲国家并未积极响应。
其四,在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调整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跃跃欲试,大有推倒重来之意,如攻击联合国无用、扬言要退出WTO、主张用双边谈判替代多边机制、随意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等。其中原因,是由于二战后初期美国在主导建立战后国际制度时,把“领导世界”置于优先地位。而在实惠方面,美则因其竞争优势、经济实力超强,确实向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有一定的主动“让利”与提供“公共产品”、并在一定程度上“自我约束”,允许欧洲及其他国家“搭便车”。特朗普上台后倡导“美国优先”而非“领导世界”优先,要从现有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中抽回美对国际制度提供的“公共产品”,放弃其义务和“自我约束”,不再允许其他国家“搭便车”,在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中尤其锱铢必较。简言之,特朗普既要“美国优先”、锱铢必较、处处争取“实惠”,以期实现美国经济与就业增长、收揽人心、争取连任;又要做世界“操盘手”,继续“领导世界”。在特朗普看来,美国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即使推倒重来,美国依然有主要发言权。且美可趁机解除其在现有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中的“自我约束”、所承担的所谓“不合理义务”、收回美向世界提供的部分“公共产品”以及二战后初期“出让”的部分权益。
以欧洲目前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而论,国际制度的任何大幅调整,都意味着欧洲国家将部分丧失其二战后初期所得。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制度如果大幅调整,欧洲最多可以保有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保持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较之欧洲英法德等国都更有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如,世行及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如果改组,欧洲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制度化地永久性把持IMF总裁职位。实际上,几年前世行改组,欧洲国家被迫向中印等国转让“股权”和“投票权”,已经证明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的任何大规模和实质性变动,都意味着欧洲国家的国际权势将“有所失”。总之,现有国际制度变动与否,美欧损益与感受差异很大。因而对于特朗普动辄拿现有国际制度说事,不时威胁要推倒重来,欧洲国家既敏感、也反感,美欧必然要互“怼”。
美欧关系未来:重归于好还是渐行渐远?
有关美欧关系的“未来前景”,常话常新,一直是战后以来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显学”,今天也不例外。2003年围绕因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产生的美欧分歧,美国人曾夸张地断定美欧二者,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金星”,以形容美欧分歧之大。国内学者则认为美欧“渐行渐远”。如果今天还可以在这二者之间做选择,笔者都更倾向于欧美“渐行渐远”的说法。无论如何,美欧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在下降,相互信任度在下降,美欧同盟的内容在空心化,同盟关系的“蜜月时代”已经日过中天,只会渐渐淡去,而不可能再复制,尤其是不太可能复制冷战时期的密切军事安全同盟或者冷战后初期的所谓“价值观同盟”。换言之,当前美欧矛盾既涉及具体事务,更是结构性矛盾。美欧同盟关系的基础变了。
美欧矛盾加剧与当前的美欧互“怼”,确实与特朗普因素有关,是“特朗普冲击”的直接后果。然而,早在特朗普上台以前,导致美欧矛盾的种种观念与利益分歧以及经济基础和国际政治基础已经存在,特朗普上台以来奉行的政策只是以较激烈的方式拉开了美欧矛盾的帘幕,催化了矛盾,使美欧矛盾以更激烈、更公开和互“怼”的方式展开。这也是美欧矛盾属于结构性矛盾而非事务性矛盾这一政治判断的基本内涵。
实际上,“特朗普现象”与“特朗普冲击”本身正是世界大变局的产物,是世界大变局背景下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是世界大变局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反映,也是美国面临世界大变局、应对世界大变局的一种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正因为如此,不论美国主流媒体、精英如何不喜欢特朗普,特朗普都能上台执政,不但会干满四年,还有可能连任。“特朗普现象”的可持续性有可能远不止八年。因此,特朗普倡导的“美国优先”有可能是对二战后以来美国坚持半个多世纪的“全球主义”的一种颠覆,是美国面对世界大变局的新姿态、新方向、新政策。在美国坚持“特朗普现象”或者说“特朗普主义”的条件下,美欧关系的“渐行渐远”难以逆转,甚至有可能继续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