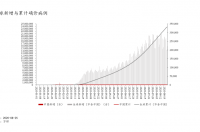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台以来,整个世界几乎一直趋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这个世界似乎就是特朗普一人的舞台,人们每日关切他的推特,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无论是实际层面的还是概念层面的,无论是物质意义上的还是心理意义上的。历史上并不缺“奇特”的政治领袖,无论是被视为是好的,还是被视为是坏的,但从来没有一个像今天的特朗普那样对世界造成如此的不确定性。
不过,这并非特朗普的个人能力,而是客观环境使然。这个客观环境就是“全球化”。从前,不管政治人物如何“奇特”,其影响力总是局限于一国之内,或者一个区域之内。但全球化可以把一个“奇特”政治领袖的影响力迅速扩展到整个“全球村”。另一方面,特朗普所造成的“全球现象”也几乎赤裸裸地表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或全球村,实际上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资本造就了全球化,也造就了今天的世界。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就政体或共同体而言,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地方性的政体,包括原始部落、城邦、各种类型的地方共同体。在这个阶段,各个政体之间可能存在贸易关系,但没有实质性的关联。第二、帝国时期。帝国是松散的联盟,帝国内部的贸易比较频繁,但帝国往往是“统而不治”或者用暴力手段维持帝国的整合;帝国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因为帝国的本质就是无限的扩张。第三、近代民族国家阶段。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各国对内部的一切包括人口、经济和政治等享有主权,“国家利益”的概念首次被应用于国家间的关系。第四、全球化下的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也可称之为“后主权国家”,因为尽管名义上各国仍然享受主权,但实际上国家所能享受的主权空间越来越少,出现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国家的这个演变过程中,资本扮演了主要角色。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简单地说,全球化就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资本和国家有些时候具有共同的利益,有些时候两者的利益处于冲突之中。早期,资本需要国家的支持而得以迅速全球化。历史地看,不管有无国家,资本本身也是会全球化的,国家的支持只影响资本全球化的速度。
而近代主权国家的形成,也需要资本的支持。历史地看,民族国家是最强大的国家组织形式,黑格尔因此把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称为“历史的终结”,即民族国家是最终的国家形式。同样,没有资本,民族国家也会形成,但形成的过程就会困难得多,缓慢得多。
民族国家主权力量的消解
当代全球化则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有学者已经作出分析。简单地说,民族国家的主权力量被两种力量消解了。在民族国家之上有跨国公司,资本在全球流动形成了跨国公司。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宣称自己具有完全的经济主权。全球化对小国家经济主权的负面影响更大,这些小国家如果不加入全球化,会永远处于贫穷之中;一旦进入全球化,有可能致富,但更有可能被洗劫一空。更严峻的是,资本不会容许任何一个国家流离于全球化之外。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全球化进程只是时间问题,无法逃避。
在主权经济下,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了一项技术,就会产生就业和税收,资本、政府和社会大家各有所得。但在后主权经济体时代,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了一项技术,不见得有就业,不见得有税收,因为资本既可以选择留在本国,也可以选择流出国外。可以确定的是,迄今为止,资本全球化都导致各国内部各社会阶层之间和各国之间收入差异的扩大。
在民族国家之下有非政府组织,或者社会力量。今天的社会力量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力量已经有天壤之别。传统社会组织大多是地方性的、局限在国家内部,今天很多非政府组织本身就具有国际性,犹如跨国公司。即使是地方化的社会组织,也和国内的其他组织,或者国外的其他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看看曾经为特朗普做顾问的班农所做的事情就知道了。社会组织有能力推动一场全球性的民粹主义运动,这种情况从前并不多见。
全球化尽管造就了“全球村”,但这个“全球村”并不存在一个高于主权国家的政府。这便是问题之所在。之前,人们对诸如联合国那样的国际组织抱有厚望,但现在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往往沦为大国的工具,较小的国家可以参与,但离开了大国,效果发挥不了实质作用。在客观层面,全球化对各国所造成的影响,如同一个国家内部过于集权,对地方政府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在一国之内,如果太集权,地方政府和社会就很难发展出自己的责任感,大家只看着掌握大权的中央政府,尤其是那些握有实权的领导人。
同样,在全球化下,各国不能脱离全球化而生存,“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很多国家的生杀大权。但在对付全球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时,各国政府则往往无能为力。即使想对自己的国家负起责任,但多数场合都力不从心。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不仅流行于较小的国家,即使是最大的国家,例如美国和中国都可以感觉到。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改变全球化的趋势。一些强势政治人物的确可以“逆”全球化的潮流而行,但结果自己也成了“受害者”。
如何应付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反全球化。反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有,但从来没有成功过。因此,人们可以预计,在未来,反全球化运动不会停止,甚至会越来越激烈;但在客观层面,这样的运动不会有实质作用。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可以和资本进行有意义的竞争或斗争。
在马克思时代,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时也有很多人真的相信能够这样做。但最终,一旦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民族主义战胜了国际主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最终原因。今天要再塑造这样一场社会运动已经是更加困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后的支持力量,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社会,更是落后国家的政府。而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有任何意愿来支持这样一场运动。
也有学者如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空想着让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但这种设想没有可能性,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成功过。道理也很简单,各国政府之间争吵不休的时候,资本早已经联合起来了。在西方尤其如此,在“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下,对外的民族主义(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和对内的民粹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的主流。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影响下的政府,可以实现“联合起来”的目标。
社会均衡发展靠什么制衡
一国之内的情况也差不多。任何一个社会的均衡发展就要求在资本、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形成制衡。经验地看,在这三者中间,资本是最具有变化动力的,往往是因为资本方面的发展打破现有的均衡状态。为了达到再均衡,往往是政府和社会联合起来,对资本构成有效的压力,从而实现再均衡。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就是这样产生的。从原始资本主义社会到福利社会的转型并非资本的转型,而是西方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产物,即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而社会主义运动简单说来,就是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联合对资本施加压力所致。
当然,就政府和社会关系来说,也有一些国家选择了消灭资本的激进社会主义运动,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尽管这些国家在最初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在消灭资本之后并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苏联和东欧国家没有能力和资本主义的西方竞争,结果败下阵来。也可以预见,尽管一些政治人物或社会仍然抱有理想,实现一个“无资本”的社会,或者一个资本完全由国家掌控的社会,但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小。原因在于,在全球化下,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封闭起来;如果动用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来自我封闭,最终的结局也是失败。
由此看来,如果要实现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再均衡,人们很难把过高的期望寄托在国际层面。因为各国无能应对全球化(国际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国际体系已经变得脆弱不堪。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大国,内部解决不了问题,就把问题外部化。尽管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今天美国举国上下的“谴责中国”(blame China)风气,会帮助美国解决任何内部问题,但无论对政府还是社会来说,“谴责中国”是最容易的。也可以预见,如果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和深化,现存的世界体系会继续弱化,甚至解体。
如同历史上所发生的,要解决问题,人们的眼光可能仍然必须落到一国的内部。今天的资本可以到处流动,这增加了政府和社会控制资本的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因为不管怎样,资本不管流到哪里,仍然具有“地理性”,仍然需要落脚点。存在于互联网空间的资本也是如此。尽管互联网没有主权性质,但互联网的使用者是有主权性的。
也就是说,各国政治人物不应当简单地“外部化”内部问题,而是着力从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过去的福利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一战、二战都是各国“外部化”内部矛盾的结果,不仅导致了灾难,更没有解决内部的任何问题。而福利社会则是内部发展的结果。简单地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了,但西方的内部社会主义运动则成功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不应当忽视今天美国民主党向左转的趋向。这次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民主党大有一股类似欧洲当年社会主义运动的趋势。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的美国成功“逃避”了欧洲发始的社会主义运动,但今天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正为社会主义运动创造新的条件。不管这场运动的未来如何,这场运动的趋向是从内部寻找解决方法,值得人们的重视。
不管怎样,持续数十年的急速全球化,不仅使得今天的国际秩序变得非常脆弱,而且各国内部的政治秩序基础也动摇起来。如果人们无法应付全球化所造成的这些挑战,无法从内部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没有很好的理由对未来的命运抱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