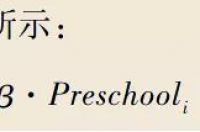
一、引言
个人的认知能力既是接受教育的一种发展结果,也对个人整个生命周期的社会经济结果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黄国英、谢宇,2013)。在青少年时期,认知能力会影响个人的教育机会获得和学业表现(Glewwe et al.,2017;黄国英、谢宇,2013),与早恋及越轨行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黄国英、谢宇,2013)。在成年时期,认知能力会影响个人的职业选择、工作经验以及收入(Heckman et al., 2006)。认知能力也是影响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它可以解释20%的代际收入固化(Blander et al., 2007)。
然而,针对中国部分农村贫困地区的调查发现,农村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水平滞后(Li et al., 2017),这是造成农村学生初中辍学率较高、获得高中和高等教育机会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Khor et al., 2016; Li et al., 2015; Li et al., 2017),长期来看会影响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发展绩效和社会公平(Khor et al., 2016)。因此,为了更好地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来促进农村青少年的社会流动,阻断农村家庭的贫困代际传递,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城乡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差距、背后的原因以及可能的政策干预工具。
在影响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认知能力的诸多因素当中,儿童早期发展和学前教育经历非常重要(Almond & Currie, 2011a)。它是提高个人能力、促进社会流动的“预分配”工具,兼具公平与效率的效果(Heckman, 2013:38)。然而,中国城乡儿童在学前教育机会上同样存在着差距。2008年全国0-6岁儿童在城市、城镇、农村地区的分布比例分别是18%、21%和61%,但是全国幼儿园在园人数在城市、城镇农村地区的分布比例则为25%、32%和43%(World Bank, 2011)。更重要的是,农村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效益相对较低(彭俊英等,2011),这是因为农村幼儿园保教质量不高(罗仁福等,2009),专任教师学历比例偏低,幼儿相对于专任教师/专职人员的比例明显高于城市幼儿园(World Bank, 2011)。
那么,学前教育经历对城乡儿童的认知水平及差距有何影响?对此我们还缺乏基于全国性样本的证据。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以下简称CEPS)基线数据,从学前教育的视角研究城乡初中生认知能力的差距。本文试图回答如下四个问题:城乡初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差距是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学前教育是否影响初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城乡学生认知能力差距有多少可以归因于两者不同的学前教育经历?如果采取普及性的学前教育发展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缩小城乡学生的认知能力差距?
研究城乡学生的认知能力差距以及学前教育在其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由于受数据限制,在已有的有关中国社会分层和教育不平等研究当中,仅有少数文献涉及认知能力(例如Huang et al., 2015;Xu & Xie, 2015;Zhang et al., 2015;黄国英、谢宇,2013)。在大量有关教育不平等尤其是城乡教育差异的研究中,主要关注学校层面的办学条件、经费投入、师资等差异,或者学生层面的教育获得差异。另一方面,鲜有研究将教育分层的递进过程追溯到入学之前的学前教育阶段。据笔者掌握的文献,目前国内几乎还没有研究利用全国性样本考察学前教育对城乡学生认知发展差距的影响。因此,本文有助于拓展城乡教育不平等的研究范围,更完整地理解教育分层的过程,同时也为学前教育的影响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
此外,本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针对高校扩招之后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甚至有所扩大的现象,已有研究将其根源追溯到中考阶段的城乡机会不平等(Li et al., 2015;李春玲,2014;吴愈晓,2013)乃至农村学生在学前和小学阶段的认知能力准备不足(Li et al., 2017)。刘精明(2014)也指出,认知能力对高等教育分层的影响大于家庭出身的作用。因此,从学前教育的视角探讨城乡学生认知能力差距的成因,有助于制定更好的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
二、文献综述
(一)认知能力与新人力资本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和贝克尔(Gary S. Becker)等人提出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它是指通过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移民等投资形式凝结在人身上、可以持续获得回报的技术和知识(贝克尔,2007:XVII)。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存在若干局限。首先,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不够准确。传统理论一直是从其投资形式去进行度量的,比如受教育年限和在职培训时间(李晓曼、曾湘泉,2012),但对于接受同样数量的教育而最终的成果质量不同就难以体现。有研究发现,各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世界银行规定的第2级基本读写能力所需的教育年限并不相同,从最少的9年到最多的16年不等(刘骥,2018)。
其次,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忽视了能力形成的时间性,认为不同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李晓曼、曾湘泉,2012)。然而,认知神经科学以及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能力的形成具有关键期和敏感期(Heckman, 2007)。
因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能力的‘新人力资本’”(Hanushek, 2010)。其核心是包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在内的“技能”(skill)和“能力”(capability),它试图解释能力的形成过程(李晓曼、曾湘泉,2012),强调要用一种动态的、生命周期的视角看待能力的形成(Heckman, 2007)。
生命的早期阶段是个人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和敏感期。在这一阶段对婴幼儿以及儿童进行发展干预,提供教育和保育服务,会对其认知能力发展产生即时的或者说短期效应。但是,这种影响是否会持续到青少年乃至成人阶段?对此,各个学科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其共同点都是从生命周期的视角动态地看待人的发展。
“胚胎起源假说”(fetal origins hypothesis)指出,胎儿在子宫发育时的营养状况与成年时期的多种疾病密切相关(Barker, 1990)。自此之后,社会学、经济学涌现出大量研究扩展了该假说,检验胚胎期和早期环境对个人社会经济结果的影响(Almond & Currie, 2011b)。
认知神经科学、发展心理学对大脑神经发育过程的研究表明,早期成长经历会对能力的形成产生持续性影响。“2-3岁是个体口头语言发展的关键期;4-6岁是儿童对图像的视觉辨认、形状知觉形成的最佳期;5-5岁半是掌握数概念的最佳年龄;5-6岁是儿童掌握词汇能力发展最快的时期”(庞丽娟等,2003)。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Benjamin Bloom)指出,出生后的前五年是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从17岁测得的智力来说,约有50%发生在胚胎期到4岁,约有30%发生在4-8岁,约有20%发生在8-17岁(甄丽娜等,2016)。认知能力发展的“时间窗口”相对较小,一旦把握这一时间窗口将终身受益,因此学前教育会对认知能力产生持续的影响。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解释了早期干预和学前教育为何具有长期效应。赫克曼(Heckman,2006)发表于Science的论文总结了早期发展干预研究的四个核心要点:(1)大脑结构与能力的形成受基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2)后形成的能力取决于之前的能力积累;(3)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是相互依赖的;(4)能力发展存在一个可塑性最强、最易受环境影响的敏感期。认知能力的敏感期出现在幼年阶段(Heckman,2006)。他与合作者提出了“能力形成的动态模型”(technology of skill formation),强调能力的发展可以通过后天有意识的投资或干预加以改变。该理论指出,人的能力形成和发展有两个重要特点:(1)自我生产(self-productivity)。能力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self-reinforcing),前一阶段形成的能力能够促进之后阶段能力的发展。(2)动态互补性(dynamic complementarity)。在某一阶段对能力进行干预或投资,其生产效率取决于之前已经获得的能力。之前阶段的能力存量越多,当前阶段对能力进行干预的回报率也越高。能力生产的这两个特征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能力创造能力”(skills beget skills)的长期影响机制(Heckman, 2007;Cunha & Heckman, 2007)。这一理论也被经验证据所证实:早期发展干预是一项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其价值超过之后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投资(Heckman, 2006)。
2.经验证据
对过去50年来美国早期干预项目的若干综述性研究发现,到项目干预结束的时候,干预项目能提高参与者的认知能力约0.23个标准差。早期干预和学前教育对认知能力的短期效应基本得到确认(Almond & Currie, 2011a; Blau & Currie, 2006)。
但是有关学前教育长期效应的研究发现则不确定。有研究发现,学前教育对长期的认知能力、教育获得等具有积极作用(Almond & Currie, 2011a;Blau & Currie, 2006)。坎贝尔和雷米(Campbell & Ramey,1995)对美国卡罗莱纳初学者项目(Carolina Abecedarian Project)的跟踪研究发现,实验组在8岁以及15岁时的IQ测试分数比对照组高0.33个标准差。赫克曼等人(Heckman et al.,2013)发现美国佩里学前教育项目(Perry Preschool)对受干预儿童的学业表现具有长期影响。但也有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学前干预项目的影响逐渐变小直至消失(Magnuson & Duncan, 2016)。对这一分歧的一种解释是干预项目的质量非常重要。学前教育具有长期效应的证据基本上都来自对高质量干预项目的跟踪研究。而那些没有发现长期效应或长期效应较小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全国/全州样本的调查数据,在这些样本中,儿童接受的学前教育项目质量不一,因此从长期来看,高/低质量干预项目的效应互相抵消了。
相对而言,中国的同类研究数量较少,以小样本研究为主。罗仁福等人(Luo et al.,2012)对三省六县农村家庭505名儿童的调查发现,接受过正规学前教育的儿童的认知发育显著高于未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一项对贵州农村两个乡总计370名儿童的研究发现,上过正规幼儿园或学前班的农村儿童在入学准备以及识字、数学的表现上都显著优于对照组儿童(Rao et al.,2012)。陈纯槿和柳倩(2017)对上海5177名15岁学生样本的研究发现,接受学前教育对数学、阅读和科学素养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王慧敏等人(2017)利用CEPS数据研究发现,学前教育对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业表现均具有长期影响。而龚欣等(Gong et al., 2016)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以下简称CFPS)的研究则发现学前教育和认知能力之间没有稳定的显著关系。
(三)城乡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状况
目前直接关注城乡儿童认知能力发展差距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CFPS数据的几项研究发现,农村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同龄人(Huang et al., 2015;Zhang et al., 2015;黄国英、谢宇,2013)。基于另一个全国12000多名4-6年级学生样本的调查发现,城市学生的认知能力显著高于农村学生(陶沙等,2015)。在回应审稿专家的修改过程中,我们又检索到两项相关的研究:赵国昌等(Zhao et al.,2017)和江求川(2017)均采用CEPS数据发现城乡学生在认知能力上存在显著差距,但是这两项研究并未考察学前教育对认知差距的贡献。城乡儿童的能力差异甚至在更早的阶段就已出现。对中西部三省六县家庭的调查发现,4-5岁农村幼儿的学前启蒙教育测试得分远低于城市同龄幼儿(Luo et al., 2012)。
上述文献回顾表明,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而学前教育对其有促进作用。尽管这种影响的长期效应不明,但至少在短期内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提出几个待验证的假说:(1)城乡少年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学前教育经历均存在明显差距;(2)学前教育对初中阶段学生的认知能力具有长期效应;(3)城乡初中学生在学前教育经历上的差距是导致其目前认知能力差距的重要原因;(4)针对农村的学前教育普及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学生的认知能力差距。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年基线数据。该项目以当年初中一年级(七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九年级)的在校生为调查对象,通过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抽样方法,依次抽取县(区)、学校、班级、学生/家长/班主任/主科目教师/学校领导等四个抽样单元。基线调查共抽取了来自全国28个县(区)、112所学校、438个班级的19487名初中学生。
(二)变量
1.城乡组别的划分依据
本文以调查时学生的户籍为标准划分“城”“乡”组别,后面提到的控制变量“户籍”的设定方式与此相同。这主要基于如下两点考虑:
首先,在中国社会,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许多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均与户籍相挂钩。以户籍而不是学校所属地区来划分城乡组别,可以尽可能地保证学生在调查时的户籍身份与其当年面临学前教育选择(是否接受学前教育)时的户籍身份是相同的。这一点对于户籍状态始终不变的学生来说自然成立。对于那些由农业户口转换成城镇户口且转换时间晚于接受学前教育时间的农村学生来说,两个时点的户籍身份不同。但是这部分学生的比例较小(N=460),因此影响不是很大。
其次,城市地区学校有不少农业户籍学生(持有非本地农业户口的流动儿童)。如果以学校所在地来划分的话,会导致城市组别当中包含两类户籍的学生。这些流动儿童尽管目前在城市学校就读,但他们在进入城市之前的很多经历与城市户籍学生截然不同,因此影响认知能力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尽管本文的处理方式也会导致城市组别当中包括一些转换为非农户口的“农村”学生,但这一比例远小于进城读书但未转换户口的流动学生比例。相对于以学校所在地界定“城”“乡”组别,本文的处理方式可以获得一个更加“纯粹”的城乡分组方式。
2.被解释变量
CEPS为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分别设计了一套认知测试题,本文将转换后的标准化得分作为度量学生认知能力的被解释变量。
3.解释变量
CEPS询问了个人在3岁之后是否上过幼儿园或学前班。我们据此构造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否接受过学前教育”(是=1)。
城乡学生在学前教育的年限上(在园持续期)可能也不同。因此,我们在比较城乡学生学前教育经历以及后面的政策效果模拟时,还考察了在园持续期的情况。按照国家规定,幼儿园接收3-6岁幼儿。CEPS在询问学生“3岁以后有没有上过幼儿园或学前班”之后,还询问了“是从几岁开始上幼儿园或学前班的”。有少部分学生回答的入园年龄在3岁之前或6岁之后。为了保证这两个问题的一致性并与国家规定吻合,我们删除了入园年龄在3岁之前以及6岁之后的样本。然后,我们假定儿童一旦入园就会持续就读到升入小学为止,利用学生汇报的小学入学年龄减去幼儿园入园年龄,推算其在园持续期。
4.其他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Gong et al., 2016;Liu & Xie, 2015;王慧敏等,2017),我们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学生认知能力的因素。具体包括:
(1)个人层面变量。性别(男性=1)、年龄、民族(汉族=1)、户籍(农业户口=1)、身体残疾状况(具有各类残疾状况=1)、是否独生子女(独生子女=1)。
(2)家庭层面变量。父母双方教育水平较高一方的受教育年限、目前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观自评(包括“家庭经济状况中等”和“家庭经济状况富裕”两个虚拟变量,以“家庭经济状况困难”为参照组)、家庭藏书量(包括“藏书量一般”和“藏书量较多或很多”两个虚拟变量,以“藏书量较少或很少”为参照组)、父母外出状况(包括“父母一方不在家”和“父母双方都不在家”两个虚拟变量,以“父母双方都在家”为参照组)。
(3)学校层面变量。学校在当地的排名(包括“学校排名中上”和“学校排名最好”两个虚拟变量,以“学校排名中等及以下”为参照组)、学校性质(民办学校=1)。
(4)地区层面变量。地区发展水平会影响个人各类教育机会获得以及教育表现,因此我们还控制了学校所在地区(包括“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两个虚拟变量,以“东部地区”为参照组)、所在区县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我们将样本限定在所有变量都没有缺失值的观测个体中,用于分析的样本最终包括17748名学生。考虑到七年级和九年级使用了不同的认知能力测试卷且总分不一样,因此分年级进行分析更加合理。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明,七年级和九年级城乡学生在认知能力及学前教育经历(入园率和在园持续期)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详见表1和表2的分析)。和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身患残疾的比例更高,非独生子女的比例更高,父母受教育水平更低,家庭经济状况更差,家庭藏书量一般的比例较高但是藏书量较多或很多的比例明显偏低,父母不在家(特别是双方都不在家)的比例更高,所在学校排名中上的比例较高但是排名最好的比例明显偏低,在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更高,来自中部地区的比例更高,但是来自西部地区的比例较低,当地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更低。
(三)研究方法
1.用于描述城乡差异的描述性统计
我们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城乡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前教育经历是否存在显著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否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2.用于识别学前教育效应的OLS模型和PSM估计
要严格识别学前教育对认知能力所具有的长期效应,需要采取随机试验并连续跟踪的研究设计,但是这种研究设计和数据目前在国内研究当中还很难满足。因此,大多数使用调查数据的研究,首先进行OLS估计,然后为了减少估计偏误,进一步采取倾向值匹配估计(例如Gong et al., 2016;陈纯槿、柳倩,2017)、工具变量估计(例如Borraz & Cid, 2013)等方法。由于本文的数据不具备追踪的特征,且缺乏合适的工具变量,因此我们使用OLS模型和倾向值匹配方法去估计学前教育的效应。
Cognitivei是第i个学生的认知测试标准化得分,Preschooli是表示该学生是否接受过学前教育的虚拟变量,Xi是一组控制变量。由于CEPS在抽样过程中具有聚类特征,同一学校内部学生的同质性较高,因此对标准误进行了学校层面的聚类调整。在进行OLS估计的时候,按不同的年级分别建模。在每个年级中,首先估计全国总体、全国城市、全国农村三个样本的模型;然后再聚焦于西部地区,依次估计西部总体、西部城市、西部农村三个样本的模型。这样一共有12个模型。
个人是否接受学前教育是一种自我选择行为。“接受学前教育组”(处理组)和“未接受学前教育组”(对照组)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处理组的年龄更小,独生子女比例更高,汉族比例更高,有残疾的比例更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父母受教育水平更高、家庭经济状况更好、家庭藏书量更多、父母外出的比例更低),所上学校质量更高,所在地区教育发展水平更高。尽管OLS模型控制了这些混淆变量,但随着混淆变量个数的增加,OLS模型很难保证在每一种混淆变量的不同取值组合上都存在可比较的处理组和对照组个体。此时,倾向值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下文简称PSM)就可以解决这一难题。该方法通过将多个混淆变量估计出来的一个一维的倾向值加以控制,为处理组个体模拟出一个(或多个)与之在各方面都比较接近的对照组个体,实现对象的可比性(胡安宁,2015:36-37),并且不依赖于函数形式设定。因此常用于无法开展随机试验、不得不采用调查数据进行的因果推断,以此作为OLS估计的一种稳健性检验(Gong et al., 2016)。在本研究中,PSM的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基于Probit模型预测个体接受学前教育的概率,也即倾向值。布鲁克哈特等人(Brookhart et al.,2006)指出,预测倾向值时控制的协变量当中应该纳入那些与处理变量有关的变量。此外,那些与处理变量无关但是与结果变量有关的变量也应该纳入,这样可以在不增加估计偏误的同时降低处理效应的方差。因此我们控制的协变量Xi与OLS模型当中的控制变量相同。
接下来对倾向值在共同取值范围内的个体进行匹配。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采取了近邻匹配(k=4)、半径内的近邻匹配(caliper=0.25σpscore,k=4)、核匹配(使用默认的核函数和带宽)、局部线性回归匹配(使用默认的核函数,带宽=0.5)等四种匹配方法。
然后,通过比较两组变量在匹配之后的标准化偏差是否小于10%来判断匹配是否有效平衡了数据。
最后,通过匹配后的样本计算“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for the treated, ATT),也即对于接受过学前教育的人来说,接受学前教育(事实)和假如不接受学前教育(反事实)两种状态下认知能力的平均差异。
进行PSM估计的时候,也是如前述OLS模型一样,分别对12个不同的样本进行估计。
3.评估学前教育对城乡认知差距贡献份额的Blinder-Oaxaca分解
Blinder-Oaxaca分解是一种基于OLS回归模型的用于解释组间均值差异的方法。组间均值差异可以归因于两部分:一部分源于两者的“禀赋”差异,一部分源于两者在“禀赋”上的“回报率”不同。“禀赋”是指影响结果变量的各个自变量的取值,“回报率”是指各个自变量的影响效应。以本文为例,学前教育因素对城乡学生认知差距的影响来自两方面:(1)两个群体的入园机会不一样;(2)学前教育对两个群体的认知能力的影响不同(回报率不同)。
下标u和r分别表示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根据(1)式,分别对城市和农村样本进行估计。为了表达简便,我们不再单独列出学前教育变量(Preschool)而是将其归入协变量X当中。那么认知能力的城乡组间均值差异可以由(2)式表达:
其中,等式右边第一项是“可解释的原因”或者说“禀赋效应”,它度量了城乡两组由于禀赋不同对认知差距的贡献;第二项和第三项是“不可解释的原因”或者说“系数效应”,它度量了城乡两组由于变量回归系数和截距项系数上的不同对认知差距的贡献。
4.用于估计政策干预效果的模拟分析
基于OLS估计的学前教育效应、城乡学前教育机会差异等信息,我们模拟了学前教育普及政策对缩小城乡学生认知能力差距的效果。详见后文。
四、结果与讨论
1.城乡学生的认知能力差距
城乡学生的认知能力发展差距具有如下两点特征(详见表1)。首先,城乡初中生的认知能力差距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全国性现象。七年级城乡学生的认知能力差距为0.248个标准差,九年级的差距扩大到0.362个标准差。这种差距不仅显著(p<0.01),其效应量也达到了中等程度的规模(cohen’s d="">0.2)。这可能是因为七年级学生是相对于九年级学生更晚入学的队列,随着教育的发展,城乡差距有所缩小。
其次,城乡学生的认知差距典型地体现为一种“西部问题”。将全国样本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的研究表明,城乡认知差距在西部地区更加明显。西部地区九年级城乡学生的认知差距高达0.478个标准差,这是一种程度较大的差异(Cohen’s d>0.5)。这可能与该地区的人口分布和资源集中度有关。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城市在当地资源的集聚性上更为明显。另一方面,西部的农村地区发展极为滞后,全国贫困县和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农村地区。西部的城市过度集中资源、农村发展极为滞后这两方面原因共同导致了西部地区城乡差距最为明显。这意味着要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政策应当聚焦在西部地区。因此,我们在后文将分别考察全国样本和西部地区样本。
2.城乡学生的学前教育经历
学前教育经历也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距。首先,城市儿童接受过学前教育的比例显著高于农村儿童,且差距达到中等程度(Cohen’s d>0.2)。同样,这种差距在九年级和西部地区更加明显(见表2第1部分)。
其次,接受学前教育年限的城乡差距更大。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中国约有48%的农村儿童接受的学前教育是一年期的学前班,而非城市儿童普遍接受的三年期幼儿园(World Bank,2011)。我们的数据发现,城市学生在3岁、4岁和5岁入园的比例分别为47.58%、35.84%和11.67%,平均入园年龄为3.76岁。而农村学生在3岁、4岁和5岁入园的比例分别为33.21%、37.06%和20.05%,平均入园年龄为4.08岁。表2第2部分显示,在园持续期的城乡差距不仅显著,且效应量更大。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城乡学生在园持续期的差距已经达到了相当明显的程度(Cohen’s d>0.5)。
1.OLS模型估计结果
OLS回归结果有如下五点发现(详见表3第2列)。第一,学前教育和认知能力之间具有显著且稳健的关系,在所有模型中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估计系数。平均而言,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的认知能力比对照组高出0.1-0.22个标准差(全国总体样本或西部总体样本)。这表明学前教育对认知能力具有长期效应。和其他变量相比,学前教育变量的系数不仅稳健,且相对较大。为了控制校际异质性,我们还估计了学校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和分层线性模型(HLM),发现学前教育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第二,学前教育效应在西部地区更加明显。我们猜测,这是因为其他影响认知能力发展的因素在西部地区也普遍较为缺乏,比如父母教育水平、家庭藏书量等,因此更加凸显了学前教育与认知能力的关系。
第三,学前教育效应在七年级样本中较大,在九年级样本中较小。这可能是源于队列效应——两个年级不是同一个样本,样本分布特征上存在差异。也有可能是源于时期效应——和七年级学生相比,九年级学生接受学前教育的时间更早,面对的教育政策和教育环境不同,例如学前教育的质量可能更低。当然,也有可能是源于年龄效应——年龄越大或者年级越高,影响认知能力的其他因素的作用越发凸显,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学前教育的作用。对此需要利用跨度较大的追踪数据去严格检验。总之,不能简单地将这一结果理解为“学前教育效应随年级提高而衰减”。
第四,对七年级学生而言,学前教育效应在城市学生当中相对更加明显。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城市样本中的效应几乎是农村样本中效应的两倍。这有可能是因为农村地区学前教育质量相对较低,限制了农村儿童的学前教育收益率。
第五,在其他影响因素中,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比较稳健且显著。对比家庭经济状况变量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书香”比“金钱”更重要。在大部分模型当中,身患残疾对认知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学校质量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不稳健,取决于具体的样本。
2.倾向值匹配估计结果
我们首先利用Probit模型估计个体接受学前教育的倾向值。结果发现,年龄越大,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越少;家庭经济条件越好、藏书量越多、所在区县人均教育水平越高,个人越有可能接受学前教育。身体有残疾、父母教育水平、民族等因素也与个人接受学前教育机会相关(但取决于具体的样本)。
然后,采取四种匹配方法进行配对。不论采用哪种匹配方法,绝大多数样本都能匹配成功。且几乎所有变量在匹配之后的标准化偏差都小于10%,这说明匹配过程有效地平衡了数据。
表3的3-6列汇报了接受学前教育者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与OLS估计结果基本类似。唯一的差别在于,对九年级学生来说,学前教育在城市样本中的效应小于其在农村样本中的效应,甚至变得不再显著。这可能是九年级城乡样本差异所致。
本文估计得到的学前教育处理效应与其他研究比较接近。例如马格努森和邓肯(Magnuson & Duncan,2016)总结了美国近50年来的各种早期/学前干预项目,发现这些项目能提高参与者的认知能力约0.23个标准差。陈纯槿、柳倩(2017)利用2012年中国上海的PISA数据,发现学前教育对数学、科学或阅读素养的效应为0.08-0.17个标准差。
但是,龚欣等人(Gong et al., 2016)利用CFPS数据的研究发现学前教育与儿童的认知能力并无稳健的显著关系。对此,可能有如下两点解释:首先,两个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对认知能力的测量方式不一样。龚欣等人使用的CFPS2010年数据测量的认知能力是指“从学校教育获得的字词能力和计算能力,题目的设计来自于中小学课程的内容,因此,CFPS2010测量的认知能力与受教育程度高度关联”(黄国英、谢宇,2013:126)。这种认知能力接近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定义的“晶体智力”——一种通过经验习得的认知能力,如语言文字能力、判断力、联想力等,它与学校教育高度关联。而在本文使用的CEPS数据中,认知能力测试内容“不涉及学校课程所教授的具体识记性知识,而是测量学生的逻辑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这比较接近卡特尔定义的“流体智力”——一种以生理为基础的认知能力,如知觉、记忆、运算速度、推理能力等。它随神经系统的成熟而提高,随着年龄增长达到顶峰之后再缓慢下降。由此可见,两种认知能力具有不同的内涵,其影响机制也不同。前者测量的认知能力主要来自学校课程教授的知识,受当前就读学校的影响较大。后者测量的是一种更为“内在”的认知能力,与神经系统的发育程度高度相关,而早期教育恰恰是在人的认知神经系统发育的敏感期和关键期进行的干预,因此对流体智力的影响更大。
其次,两项研究的样本量差异较大。龚欣等人的样本量不到3000人,而本文的样本量为17748人。前者样本量较小导致个体之间的变异性较低,因此估计结果相对不那么显著。
我们利用Blinder-Oaxaca分解技术,研究了各个因素对城乡认知差距的贡献份额。结果如表4所示。
总体而言,禀赋效应对城乡认知差距的贡献份额占了绝大部分(学前教育因素是个例外)。这意味着城乡认知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群体在特征上的差异。差异分解结果表明,父母教育和家庭文化资本是重要的贡献因素,学生是否有残疾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差异的贡献很小,学校排名仅仅对七年级样本中的城乡差距具有较大的解释力。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文化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父母教养子女的理念、习惯与知识,城乡家庭在这方面的巨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认知差距,而城乡学生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并不重要。
学前教育是造成七年级城乡学生认知能力差距的重要原因,它对七年级全国/西部城乡认知差距的贡献份额分别为27.55%和44.37%。具体而言,学前教育因素的贡献主要来自系数效应。也就是说,虽然七年级城乡学生在学前教育机会上的差距解释了一部分认知能力差距,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城乡学生学前教育的回报率不同。
但是,学前教育并不是造成九年级城乡学生认知差距重要的因素,其贡献份额不到10%。特别是在九年级全国城乡学生认知能力差距当中,来自学前教育因素的贡献份额几乎等于零。这可能是因为:(1)九年级全国城市学生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比全国农村学生高(见表2),禀赋效应为正;(2)但是,九年级城乡学生在回报率上的差异很小,甚至城市学生的回报率还更低一些,系数效应为负;(3)学前教育因素对城乡认知差距的贡献份额是上述两部分的加总,这两部分一正一负正好抵消,因此贡献很小。造成九年级城乡认知差距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教育水平、家庭藏书量,等等。在所有因素总的贡献率为100%的前提下,这些因素贡献份额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学前教育因素的份额。
由于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并不是同一批人,因此学前教育对认知差距的贡献在两个年级之间的反差还是要从样本之间的差异去解释,不能将其理解为两年之后七年级样本学前教育对认知差距的贡献份额会变得如现在的九年级样本那样小。两个样本之间的差异有可能来自“队列效应”——两组在家庭背景、认知能力起点水平等群体特征上不同;或者来自“时期效应”——两组接受教育的年份不同,教育系统本身随着时间推移也在发生变化,例如接受的学前教育质量不一样、受到了不同的教育政策影响,等等。
差异分解表明,造成城乡学生认知能力差距的主要因素在于城乡学生不同的学前教育经历、父母教育水平、家庭文化资本以及目前所在学校质量。要想缩小城乡学生认知能力差距,就需要缩小上述这几方面的城乡差异。很显然,除了学前教育经历以外,其他几方面因素很难甚至无法通过公共政策来干预。而以扩大学前教育覆盖面、提高保教质量为特征的学前教育发展政策相对更具有操作性。由于学前教育因素是造成七年级城乡学生认知差距的重要原因,对九年级城乡学生认知差距的贡献相对较小,因此我们以七年级学生为对象,模拟了普及性的学前教育发展政策在缩小城乡认知差距上的效果。
从理论上说,在影响认知能力的其他各方面因素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学前教育发展政策让七年级城乡学生在当年拥有同样的学前教育机会,并且学前教育对两者的效应也一样的话,那么两者的认知能力差距能缩小27.55%(全国)或44.37%(西部地区),政策干预效果很可观。那么,具体的政策操作应该是怎样的呢?当农村学生的学前教育机会、在园持续期和学前教育回报率均落后于城市学生的时候,干预政策需要在增加学前教育机会、延长在园年限、提高回报率几方面入手。我们参考马格努森和沃德佛格(Magnuson & Waldfogel,2005)的方法,模拟了不同干预方案的效果。由于提高回报率与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有关,在此我们仅考虑更容易操作的前两种方案的效果。
1.增加农村儿童的学前教育机会
如果政策能将农村儿童入园比例提高到城市同等水平,这意味着将全国农村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提高到85.66%,或者将西部农村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提高到87.47%。当其他因素不变,“增机会”的政策能够缩小城乡认知差距的4.44%(全国)或6.73%(西部)(政策效果如表5上半部分所示)。
然而,这种政策效果相对于差异分解所揭示的学前教育对认知能力差距的总体贡献份额而言,是相对较小的。这说明,仅仅扩大学前教育的覆盖范围还不足以消除城乡学生的认知能力差距。与此同时,还应当注重学前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比如尽可能保障农村儿童接受足够长的高质量学前教育。
2.延长农村儿童的在园持续期
有研究发现,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年限对认知能力具有正效应(陈纯槿、柳倩,2017)。我们利用OLS模型(包含相同的控制变量)发现,在园持续期和认知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效应在七年级全国城市、农村样本中的估计系数分别是0.077和0.062;在七年级西部地区城市、农村样本中的估计系数分别是0.055和0.052。这些系数的p值均为0.000。因此,延长农村儿童在园持续期也可以缩小城乡认知差距。
表5下半部分的模拟表明,假如将农村儿童在园持续期延长至城市儿童同等水平的话,即使其他因素不变,也能缩小城乡认知差距的11.29%(全国)或12.23%(西部)。
如果在保障农村儿童入园机会的同时延长在园持续期,那么即使目前农村地区的保教质量和其他因素维持不变,也能将城乡认知能力差距缩小15.73%(全国)或18.96%(西部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估计的政策干预效果存在低估。首先,CEPS的被访者都是在校学生,不含因辍学、失学而不在校的同龄人。这样一个“在校生样本”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其实高于真实的“青少年总体”,这一点对于农村群体尤其明显。因此,城乡儿童在学前教育方面的真实差距可能更大。这就意味着以城市儿童的学前教育条件为标准,提高农村儿童学前教育机会、延长在园持续期的空间更大,相应的政策效果也会更明显。其次,由于城乡学前教育质量的差异远远大于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年限的差异,包含质量公平这一目标的学前教育发展政策的作用效果会更显著。最后,由于能力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积累的动态过程,因此干预越早效果越明显。如果干预政策能让农村儿童在当年获得与城市儿童同等水平的学前教育,那么两者初始的认知能力差距就会比较小,从而会使得未来的认知能力差距也更小。基于这三点理由,不妨将本文模拟的政策效果理解为一种相对保守的下限估计。
五、总结
本文通过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基线数据研究发现,城乡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前教育机会都存在显著的差距,在西部地区更加明显。OLS回归以及PSM估计结果表明,学前教育会显著地影响初中生的认知能力。Blinder-Oaxaca分解发现,学前教育因素是造成七年级城乡学生认知能力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对九年级城乡学生的认知差距贡献不大。政策效果模拟表明,在增加农村儿童学前教育机会的同时延长其在园持续期,对缩小城乡认知差距具有一定的作用。
结合本文的发现,首先,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政策应当做到保障入园、延长年限与提高质量并重。仅仅增加农村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机会对于缓解城乡认知差距的帮助并不大。
其次,学前教育发展政策的重点应当在西部贫困地区。可以说,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城乡不均衡问题主要是一个“西部问题”。如果将政策重点放在西部地区,特别是扶贫攻坚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将会更有效率地缩小全国性的城乡儿童认知发展差距。
最后,学前教育发展政策的内容应当做到“医教结合” 和“家园共育”(李敏谊,2011)。本研究发现,儿童患有残疾既导致其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偏低,也影响其认知能力的发展。因此,学前教育发展政策应当整合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多部门的力量,协同干预(李敏谊,2011)。本文还发现,家庭的文化资本、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儿童认知能力也有很强的影响。很多农村家庭缺乏合适的亲子阅读环境,农村父母缺乏对幼儿进行早期/学前发展干预的理念和意识。因此,学前教育发展政策不能只依靠机构去提供早期发展服务,还要面向父母提供咨询和指导,提高家庭保育的质量。
本文仍然存在一些局限。虽然我们使用了多种方法识别学前教育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但本文的估计效应仍不是一种严格的“因果效应”。另外,本文对于学前教育效应在年级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只是尝试性地进行了解释,对此还需要跨度更长的追踪数据去检验。有关中国的学前教育效应研究还相当匮乏,还需要更多的后续研究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比如学前教育的效应有多大,效应是否随年龄增长而变化,产生效应的中介机制是什么,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