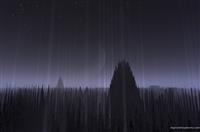
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实现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经济体;第二,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
一般上说,如果是后一种结果,人们称这个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验地看,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容易。二战以来,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大部分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更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大多在东亚儒家文化圈,除了中东的以色列,就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不过,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换。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2014年更是达到了28101美元,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时间。
这些经济体可以说是“例外”,因为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在东南亚,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14年仅达到10804美元。
在拉美地区,阿根廷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元,41年后仍属于中等偏上国家。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但几经反复,一直没能跨过1万5千美元的发达国家的门槛。
目前研究和讨论的局限
一般认为,促成这些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没有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和体制变革严重滞后等等。
中国在过去对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过激烈的讨论,但出现了两种极端相反的观点。乐观派认为中国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甚至认为已经逃避了这个陷阱;而悲观派则认为中国不仅有陷入这个陷阱的风险,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这个陷阱。
现在的讨论不像几年前那样激烈了,但这个问题客观上依然是存在的。今天,在中国的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甚至恶化的时候,更需要正视和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大陆的人均国民所得尽管接近1万美元,但远较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最后一个的中国台湾人均所得25000美元还低得多。尤其是像中国那样大的国家,不仅各地发展差异巨大,收入分配在各个社会群体中更是巨大,即使人均国民所得超越了这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很多地区和社会群体仍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这样,即总量来说,逃避了这个陷阱,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仍然会体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现象。因此,中国需要追求的不仅仅是总量上的人均国民所得,更应当追求比较公平的经济增长。
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各方面的讨论是有很大的缺陷的。第一,讨论的焦点在于政府,而非企业。或者说,过度强调国家的宏观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的作用,而忽视甚至漠视了企业的角色。诚然,产业政策可以促成企业的转型或者升级,但国家的产业政策需要结合企业的实际需要。
所谓的“有效供给”就是企业需要的供给,而非政府所设想或者计划的供给。政府一厢情愿的供给或者强制企业接受政府的供给,就会对企业产生致命的影响。不管任何地方,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而非政府。再者,现有的各种过于侧重国家宏观政策的分析,过于“宏观”了,很难看得到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说的“关联性”(linkage),即如何从一个因素的引入导向另一个因素的出现。
换句话说,除了政策寻租行为,很难看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产生有利于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微观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需要超越政府,而去探讨企业在辅助国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作用。只看政府行为,而不看企业行为,不仅逃避不了这个陷阱,反而会促成更快地进入这个陷阱,不管政府的“初心”是怎样的“善意”。
第二,过分强调那些已经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忽视了西方发达国家。研究这些经济体如何逃避或者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固然重要,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稳定性”更需要借鉴。
二战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危机,例如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近年来,多数发达国家也在经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政治危机。但不管如何,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稳定的,没有像发展中国家那么大起大落。
发展中国家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尼发生政治革命,过去数十年的建设成就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发达国家的例子如日本。日本自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一直被人们“嘲笑”,诸如“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等等。但问题是,日本的发展水平依然平稳,社会经济运作照常进行。即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发达国家的确发生“滞涨”,但并没有下降多少。这也和发展中经济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应当说,研究发达国家如何维持发展水平,对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发达国家如何维持“经济先进性”
归根到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无非就是财富问题,包括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两个层面。发达国家往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创造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企业的作用。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对维持企业所在社会的“发达性”起了关键的作用。
也就是说,至少就财富创造来说,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企业体制并没有出现严重问题。发达国家的问题是政治体制,即分配方面出了巨大的问题。企业所创造的巨量财富留在绝少数人手中,而政府无法把新创造的财富有效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而今天的中国,尽管同时面临财富创造和分配的问题,但主要的问题仍然是财富的创造,而非分配。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来进行财富分配,但并没有一样强大的能力来进行财富创造。财富创造的主体依然是企业。所以,中国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如何通过企业来创造财富。
发达国家是如何维持“经济的先进性”的呢?首先,发达国家保持了技术水平。到今天为止,大多核心技术都仍然在发达国家手中。在全球化时代,技术从西方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但核心技术并没有流出去。这里除了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名义保护核心技术之外,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性的,即维持企业的竞争性。
这里包括反垄断法律。反垄断才能维持一个经济体的开放性,不仅仅是对外的开放,而且是对内的开放,即让新类型的企业发展起来;否则垄断之下,很难避免政商一体的情况,经济最终演变成为寻租经济,不仅企业向政府寻租,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也可以向企业寻租。
其次是政府和劳动者(工人)之间的关系,意在维持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平衡,或者说是“做大饼”和“分大饼”之间的平衡。无论是民主国家的政府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都会倾向于“分大饼”,因为“分大饼”才会让老百姓满意,以展示政府的合法性。而老百姓(工人)也倾向于和资本分利(享受应当的财富)。
就是说,政府的意向和老百姓的意向是一致性。“分大饼”当然是需要的,但必须在“做大饼”和“分大饼”之间实现平衡,否则资本没有动力有所作为。在这方面,尽管发达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福利社会的压力,但政府仍然做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否则,很难解释西方优质资本和技术没有流失的现象。
更为重要的,发达国家为资本创造良好“地域性条件”,成为“嵌入地域的资本”。正是因为资本需要流动,也不会停止流动,更需要给资本创造良好的地域条件。尽管当代西方问题重重,但并没有出现高端资本外流的情况。财富分配情况严峻,但受影响的大多是底层社会,并没有影响到高层社会,即社会的实际统治者。中、上层中产阶层仍然和资本配合,享受资本所带来的好处。而这些群体也正是掌握资本和技术的阶层。
地域性条件包括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教育和培训系统、技术劳动力的提供等方面。资本可以流动,但这些则是“移不走”和“离不开”的。实际上,高技术和优质资本是离不开这些的,这些大多也是资本本身确立的(例如大学和技术培训学校)。因此,全球化下,西方流失的都是那些非核心的经济技术活动。这也是西方保持领先,或者衰落不那么快的原因。
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靠什么
在选举过程中,发达国家一般也会选择具有经济管理经验的政党上台执政。民粹主义的政党可以上台,但在缺乏经济管理经验和能力的情况下,不能有效执政,很快就会下台。
其他很多发达经济体也都是围绕着企业而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这尤其表现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上,也表现在这些经济体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上。中国台湾和香港所出现的问题既是政府的问题,也是企业的问题;而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成功则归功于政府和企业的有效配合。
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是本身的资本流向发达国家,而非相反。如上所说,发达国家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都是些技术含量较低的资本,例如劳动密集型资本。而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则是最好的技术型资本。发展中国家承担了环境、人权等多方面的代价,但因为吸引不到或者无法留住优质资本,其经济发展仍然不可持续。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对中国来说,数量型的经济扩张已经到了顶点,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无疑需要依靠质量经济,即依靠高端资本和技术。就资本来说,中国需要形成数个高端产业链,使得这些产业链具有地域性,并不会因为外在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流失。珠江三角洲曾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一直维持在劳动力密集型技术。
幸运的是,深圳现在正在快速形成一个以高端技术和资本为核心的产业链,并且向周边地区扩散。如果整个大湾区、杭州湾、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等区域,都能形成具有自身的特质的产业链,不仅能留住自己的优质资本,而且吸引优质外资,那么无疑有助于中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并且维持在稳定发展的经济水平。
而这需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如同其他社会,政府必须处理好劳动关系,实现“做大饼”和“分大饼”之间的平衡。对企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法治建设。简单地说,法治就是一个“基于规则之上的秩序”。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知识产权,无论是财富的创造还是保护,无论是资本的扩张还是流动,都需要规则。
不管如何,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经济提升为发达水平,政府不妨下沉到企业个体层面,看看企业需要什么?看看国家是否能够为企业做些有益的事情?看看国家不应当对企业做些什么?观察思考清楚了,自然会出现有效的政策,“中等收入陷阱”也会自动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