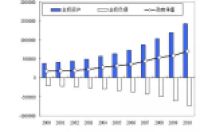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农业生产呈现农户小规模生产经营的特质。尽管农业的农户家庭经营通过赋予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有效地解决了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劳动监督和劳动计量问题,但是,这种超小规模的农户家庭经营存在土地经营规模偏小、土地分散且细碎等缺陷,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资本和劳动也难以在有限的土地上发挥效率,导致农业生产低效率(张瑞娟、高鸣,2018)。为此,中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创新农业经营主体形式、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以提高农业效率,保障粮食及农业产业安全,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①。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大力扶持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积极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努力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②。为了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农业部专门下发《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③。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鼓励发展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鼓励承包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要采取多种奖励、补助办法扶持家庭农场,加大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培训力度④。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特别强调,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启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建立健全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⑤。
在中央政策的强力驱动下,中国家庭农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业农村部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共有13.9万户家庭农场,2015年激增到34.3万户,2016年进一步增加到44.5万户,2017年全国家庭农场总数达到54.9万户⑥。众多的研究表明,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比,家庭农场突出地适应了农业自然与社会属性,实现了农业生产特点与家庭特点的高度契合(朱启臻等,2014),是中国现代农业经营的重要模式选择(高强等,2013)。然而,尽管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势头良好,但家庭农场的发展质态仍有待改善。其一,家庭农场发展速度减缓。2014年至2017年间,尽管家庭农场数增加了41万户,但2015年后增速逐年下降。家庭农场环比增长速度2015年为146.8%,2016年为29.7%,2017年进一步下降为23.4%。其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单一。我国家庭农场主要以种植业经营为主。家庭农场的类型大体可划分为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种养结合和其他类型五大类型。农业农村部的调查数据显示,各类型家庭农场占比2014年分别为61.2%、23.2%、4.8%、7.8%和3.0%,2015年分别为61.9%、19.2%、5.9%、9.0%和4.0%,2016年分别为60.8%、19.5%、5.6%、9.9%、4.2%,2017年分别为61.4%、18.3%、5.5%、10.8%、4.0%⑦。其三,家庭农场数量偏少。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6年我国的农业经营户为20743万户⑧,家庭农场数量仅占我国农业经营户的0.2%。由于家庭农场的效率直接影响到家庭农场的发展质态,因此,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和功能,有效地提升家庭农场的效率,进而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有效提升家庭农场的效率,就必须准确估计家庭农场的效率并离析出影响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关于家庭农场的效率问题,理论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家庭农场效率水平的高低,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孔令成和郑少锋(2016)运用DEA模型对上海246户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的计算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具有较高的效率;曾玉荣和许文兴(2015)运用SFA模型对福建省187户多元化经营型家庭农场的计算结果表明,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较高;姜丽丽等(2017)对江苏省306户家庭农场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的效率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家庭农场经营中存在较高的土地租金和农用机械成本;Imori et al.(2012)运用随机生产前沿和低效率效应模型对比分析巴西家庭农场和商业农场的效率后发现,家庭农场的效率低于商业农场的效率;Madau(2015)分别运用了SFA模型和DEA模型测算了意大利柑橘种植农场的效率,结果表明,SFA模型估算的技术效率与DEA模型估算的技术效率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SFA模型测算得到的规模效率高于DEA模型测算出的规模效率。关于影响家庭农场效率的因素,研究人员发现,制度安排、要素投入、经营者特征、经营模式等都有可能影响家庭农场的效率。张悦和刘文勇(2016)认为,家庭农场经营中存在的土地产权不明晰、生产成本高、规模过大、议价能力低等,导致家庭农场效率缺失;陈军民(2017)的研究发现,土地产权越不稳定,家庭农场经营者越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家庭农场效率就会越低;Mugera和Langemeier(2011)研究了经营规模和农场类型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农场的效率会因其经营规模而异,但家庭农场的类型对其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高雪萍和檀竹平(2015)的研究发现,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与家庭农场的投资规模之间显著正相关;Latruffe et al.(2005)和曹文杰(2014)的研究表明,经营者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升;周炜(2017)、曾玉荣和许文兴(2015)的研究发现,随着家庭农场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家庭农场效率反而有所下降。原因在于,多元化程度的提升会对家庭农场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家庭农场管理水平不能随着多元化程度的提升而得到相应地提高,就会降低管理效率。不仅如此,多元化程度提高会带来资产专用性的增强,资产专用性的增强又可能会降低资产使用的规模效应;Larsén(2010)的研究发现,参与农机合作比没有参与农机合作的家庭农场的效率高,并且合作形式越广泛的家庭农场效率越高;曹文杰(2014)的研究则认为,家庭农场经营品种的多样性会对家庭农场的效率有正向刺激作用;孔令成和郑少锋(2016)、梅运田等(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补贴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农场的效率。因为补贴能够给农场主形成稳定的收入预期,调动家庭农场主生产经营的积极性;Zhu和Lansink(2010)的研究则发现,农业补贴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农业补贴一方面能够提高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使经营者因为获得额外收入降低其提高效率水平的努力;姜丽丽等(2017)的研究发现,家庭农场效率的提升离不开信贷资金和农业保险的支持。关于如何提升家庭农场的效率,理论界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建议。一些学者认为,应防止家庭农场规模的无效扩张,鼓励适度规模经营(陈金兰、胡继连,2019;冀县卿等,2019);一些学者认为,应注重土地、劳动、资本投入的合理配置,避免土地成本过高、劳动力投入冗余,促进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曾福生、高鸣,2012;张岳,2019);一些学者认为,应重视家庭农场人力资本的提升,采取合适的方式加强对家庭农场经营者进行培训,提高家庭农场主的经营管理水平(王丽霞、常伟,2017);一些学者认为,应完善针对家庭农场的补贴政策,鼓励家庭农场参加农业保险,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以改善家庭农场经营的外部环境(McCloud and Kumbhakar,2008;刘同山、徐雪高,2019;陈金兰、胡继连,2019)。
现有研究关于家庭农场效率的研究结论之所以不尽相同,有的研究结果甚至大相径庭,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尽管现有研究在测算家庭农场效率时所选用的研究方法有所差异,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计算结果都会受到选取的研究样本和选择的计算指标的影响。就选取的研究样本而言,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抽样调查数据,由于各地之间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较大,或由于各地之间家庭农场类型不一,亦或由于抽样调查可能存在的信息损失和偏差,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家庭农场效率估算的准确程度。就选择的计算指标而言,现有研究大多将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投入等几个有限的指标纳入到计算模型中,这样的处理尽管极大地便捷了对家庭农场效率的计算,但有限的几个指标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全部的投入和产出,并且由于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投入和产出存在极大的差异,不加区别地选用同样的计算指标显然并不合理,这同样会导致家庭农场效率的计算结果有误。
基于以上的考虑,为准确计算家庭农场的效率并离析出影响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采取了以下措施:其一,样本选取上,以上海松江区作为研究区域,选择上海松江区2017年在册的943户全部家庭农场作为研究对象;其二,指标选取上,尽可能使所选择的指标涵盖943户家庭农场2017年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投入和产出;其三,考虑到松江943户家庭农场类型具有多样性,既有纯粮食种植型,也有种养结合型、机农一体型、三位一体型,本研究选择可考量多投入、多产出的DEA模型计算全部家庭农场及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效率,并从农业要素投入特征、家庭农场主特征、家庭农场特征、环境特征四个方面考察其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运用Tobit模型离析影响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第三部分,运用DEA模型计算和分析943户全部家庭农场及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效率;第四部分,从农业要素投入特征、家庭农场主特征、家庭农场特征、环境特征四个方面考察其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并运用Tobit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计量检验,离析影响全部家庭农场及不同类型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第五部分,简要的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1 数据来源
上海市松江区位于黄浦江上游,上海西南部,面积为604.67平方公里。在民国时期,松江由江苏省管辖,解放后松江仍属江苏省,直到1958年11月才划归上海市管辖。松江农业生产普遍采用“稻麦连作”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农业生产水平较高。
上海市松江区是全国较早探索发展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地区(封坚强,2013),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松江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逐步将家庭农场作为松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方向。进入本世纪后,松江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农业产业边缘化,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2007年,松江非农就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高达90.28%,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占比仅为6.6%(封坚强、王晶,2017),如何在高度工业化、城镇化下,保持农业不衰败、不消亡,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刘守英,2013)。早期,松江一些乡镇曾试图通过兴办集体农场、引入工商资本租地经营、委托代耕、土地外包等模式稳定粮食生产,但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出现“非粮化”、“非农化”、环境污染等问题(赵鲲等,2015)。2007年,松江区政府发布《关于鼓励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意见》,明确将家庭农场作为农业经营组织的发展方向,大力鼓励发展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松江家庭农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松江家庭农场数量持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质态明显改善,农业生产初步实现由传统的兼业小农向规模集约的现代农业的转变,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截至2017年,松江区家庭农场共有945户,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占全区粮田面积的95%⑩。945户家庭农场中,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724户,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43户,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166户,三位一体型家庭农场12户⑪。
松江按照“流转自愿、农场自耕、规模适度、租金合理、择优选择”的原则创造性地构建“承包农户——村委会——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模式,成功地落实了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了土地承包权,搞活了土地经营权,有效地实现了农村土地产权的三权分置。松江发展家庭农场的主要做法大致可归纳如下:
(1)承包农户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地流转委托书,委托村委会流转承包地。松江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权归被确权的农户所有,承包农户委托村委会流转承包地时严格遵循自愿、有偿的原则,如果农户不愿流转土地,则尊重其选择权。本村村民委托村委会流转土地时需签订《上海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委托书》。为促进承包农户转让承包地,松江对男年满60岁、女年满50岁的转出土地者额外给予每月150元的奖励性补贴。
(2)村委会组织家庭农场经营者竞标。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村委会成立由村干部、农户等多方组成的小组公开招聘家庭农场主;村民自愿报名竞聘;经民主评议、公示后,竞聘成功者确定为家庭农场经营者。松江明确规定,竞聘者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本村农户家庭且常年务农人员在2人及以上,特殊情况下,可以是具有本区户籍且常年务农人员2人及以上;必须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完成家庭农场的主要农业生产活动;农场主年龄必须为男性25~60周岁、女性25~55周岁(如果竞聘人员不足,年龄可适当放宽);农场主必须具备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掌握必要的农业生产技术,具备一定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松江在发展家庭农场时,基于家庭劳动力耕种能力、家庭务农收入、政策补贴、生产成本、规模收益等方面的考虑,将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规模确定在100~150亩之间(封坚强,2013)。据测算,按户均2~3个劳动力、农忙雇用1个劳动力测算,每个家庭最多可经营300亩耕地,如果土地经营面积为100~150亩,家庭农场年收入可达5~6万元(封坚强,2013)。这一土地经营规模有利于实现现有生产条件下劳动力与耕地的合理匹配,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务农收入水平,有效地调动起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积极性。
(3)家庭农场主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并获得土地流转补贴。村委会将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并签订《上海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家庭农场经营期限初期多为3年,后调整为5年,有的甚至为10年;土地流转费初期固定为600元/亩,后调整为以每亩250公斤稻谷为基数、以当年稻谷挂牌价格为标准,折算成现金支付。为促进家庭农场发展,初期,松江区政府给予家庭农场每亩200元的土地流转费补贴,2013年起强化对家庭农场茬口安排、田间管理、秸秆还田、粮食交售等方面的考核,并将土地流转费补贴调整为考核性奖励补贴,最高限额不超过200元/亩。
(4)家庭农场经营者的退出与续包。如果家庭农场主超过规定的年龄限制或家庭农场以雇工经营为主者或家庭农场转让土地经营权或家庭农场年度考核结果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或连续三年考核基本合格或新家庭农场试用期内考核不合格,将取消家庭农场主经营资格。如果家庭农场经营状况良好、经营期内年度考核均合格且符合村委会规定的家庭农场经营者条件,家庭农场主则具有优先续包权。
鉴于松江家庭农场的发展之于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着典型性意义,2017年4月,扬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审计大学部分师生到松江进行了预调查,走访了松江相关职能部门和部分家庭农场。在预调研的基础上,课题组设计了访谈提纲和调查问卷,并于2017年8月和2018年3月在松江进行实地调研。在正式调查期间,调研人员走访了松江区农委办公室、种植业管理办公室、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农机管理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获得了关于松江家庭农场的发展背景、主要做法、取得的成绩等相关信息。家庭农场问卷调查主要是对松江区叶榭、石湖荡、新浜、泖港、车墩、佘山、小昆山、洞泾、新桥、永丰、工业区等11个镇(地区)84个村945位家庭农场主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2017年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基本情况、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面积、家庭农场经营中的各类投入以及家庭农场各类收入。剔除2户家庭农场无效的调查问卷,共得到家庭农场有效样本943个。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三位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样本量只有12个,样本量太小,本文在研究时对这12户家庭农场进行了如下技术处理:在研究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时,去除三位一体型家庭农场的生猪养殖投入与产出数据、农机服务投入与产出数据,将其归入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组,这样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样本量增加为735个;在研究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时,去除三位一体型家庭农场的农机服务投入与产出数据,将其归入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组,这样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的样本量增加为55个;在研究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时,去除三位一体型家庭农场的养殖投入与产出数据,将其归入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组,这样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样本量增加为177个。
(一)DEA模型设定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效率可以看作是某一生产单位达到投入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的程度,是对生产单位资源配置、技术运用和成本控制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价。本研究在评估家庭农场的效率时,采用Leibenstein(1966)关于效率的界定。Leibenstein认为,效率可视作在一定投入约束下,生产单位的实际产出与要素最优化配置可能达到的最大产出之比。为计算家庭农场的效率,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DEA通过运用线性规划方法构建观测数据的生产前沿面,进而计算出生产单元相对于该前沿面的比例即效率。参照Charnes、Cooper和Rhodes(1978)构建的CCR模型,考虑到家庭农场在生产过程中只能控制和调整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而无法自由地调整产出量,本文选择投入导向的DEA模型(Coelli et al.,2005;Cooper et al.,2007)。具体模型见式(1):
在计算家庭农场效率时,将每一个家庭农场看作是一个生产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简称DMU),n个家庭农场记为(j=1,2,…,n),被评价的家庭农场记为。式(1)中表示家庭农场的3种投入,分别代表土地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y代表家庭农场的产出;为DMU的线性组合系数;和分别表示的投入和产出向量;模型的最优解代表的效率值。
CCR模型假设所有被评价DMU均处于最优生产规模。但在实际生产中,许多家庭农场并没有达到最佳规模的生产状态,因此,利用CCR模型计算出来的效率既包含了实际生产水平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差距即纯技术效率,又包含了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的差距即规模效率。为此,本文进一步采用Banker、Charnes和Cooper(1984)构建的BCC模型,将家庭农场的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具体模型见式(2)。
在借鉴已有关于农业经营主体效率研究的基础上(黄祖辉等,2011;杨万江、李琪,2016),从松江家庭农场经营的实际出发,本研究选取的投入指标主要涉及土地投入、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产出指标主要涉及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农机服务收入及各级政府各类补贴。
土地投入是指家庭农场实际经营的土地面积。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既包括家庭农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承包的土地,也包括家庭农场从村集体转入的土地。劳动力投入是指家庭农场在粮食生产、生猪养殖、农机服务中的劳动力投入,包括家庭劳动力投入和雇佣劳动力投入。家庭劳动力投入按《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规定的办法进行折算:家庭农场农村常住人口中,男16~60岁、女16~55岁的人口,以及男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且从业3个月以上人口计入劳动力范围。其中,16~17岁以及男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劳动力资源是半劳动力,其他是整劳动力。雇佣劳动力投入按家庭农场全年雇工费用除以当地当年雇工年平均工资水平折算成标准劳动力。资本投入是指水稻和二麦生产中投入的化肥、有机肥、农药、购买农机作业服务费、排灌费、运杂费、开沟和深翻费,生猪养殖中投入的水电费、保养修理费、取暖焦炭费等以及农机服务中投入的燃油费、保养维护费、修理费、水电费等⑫。
家庭农场产出指标用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衡量。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包括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农机服务收入、补贴收入等。家庭农场投入、产出描述性分析见表1。
表1中,2017年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平均土地经营面积为9.58公顷,初步实现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其中,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面积达到11.74公顷,高于全部家庭农场的平均水平。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面积为8.86公顷,略低于全部家庭农场的平均水平。从家庭农场的劳动力投入来看,平均家庭劳动力为1.86人,平均雇佣劳动力为0.7人。相比较而言,种养结合型和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劳动力投入较高,高于全部家庭农场的平均投入水平。从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来看,纯粮食种植型和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的平均投入水平低于全部家庭农场的平均水平,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投入水平则高出全部家庭农场的平均水平。与其他类型家庭农场相比,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有机肥投入较高。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费用和开沟、深翻费较低,但农机投入较大。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中有一小部分农场持有少量的农业机械,但他们并不对外提供农机作业服务,而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持有较多的农业机械,他们不仅为自家家庭农场提供农机作业,而且对外提供农机作业服务。所以,相比较而言,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农机投入较小,而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农机投入较大。松江家庭农场平均收入为38.36万元,家庭农场收入主要来自于种植业收入。相对而言,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收入最高,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次之,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收入最少。从表1中可以看出,松江家庭农场发展坚持了家庭农场家庭经营的本质特征,符合国家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要求。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以农民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利用家庭承包或流转土地,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
(三)计算结果与分析
利用Stata13.0软件对投入指标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检测的结果表明,VIF均小于10(见表2),满足VIF不超过10的要求,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利用Stata13.0软件对投入与产出指标同向性进行检测的结果表明,投入与产出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2),满足“同向性”要求。
松江家庭农场的效率计算结果见表3。表3中,运用CCR模型测得的全部家庭农场效率均值(TE)为0.3841,这一数值较小。尽管DEA模型测度的效率为相对效率,是被评价生产单元相对于“领先”生产单元的效率,但这一计算结果表明,松江大多数家庭农场的效率水平距离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较远,家庭农场效率有着极大的提升空间。运用BCC模型将家庭农场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全部家庭农场的SE为0.5595,这意味着,松江家庭农场效率较低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较低。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松江家庭农场只有27户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高达912户家庭农场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另有4户家庭农场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状态。松江家庭农场的PTE为0.7048,这表明松江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有着一定的提升空间,大多数家庭农场应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状况,提升技术应用水平。
表3同时呈现了各类型家庭农场效率的计算结果。从表3中可以看出,三种类型家庭农场中,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效率水平最高,TE值达到0.7757,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都处于较高水平,分别达到0.8518和0.9136。相比较而言,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和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效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上。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率低于纯技术效率,其规模效率值仅为0.5358,高达731户的家庭农场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因此,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更需要注重调整经营规模以提升家庭农场的效率。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和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均低于规模效率,这表明,这两类家庭农场更需要注重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
(一)模型设定
通过DEA模型计算得到的家庭农场效率值范围为0~1,属于截断数据,若采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会有偏,因此,本文在计量检验相关因素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时采用因变量受限的Tobit回归模型(李政、杨思莹,2018)。
另外,为了减少异方差的影响,对主要农业要素投入变量取对数(Wang et al.,2013),构建半对数模型。具体模型见式(3)。
式(3)中,表示第j个家庭农场的效率。表示家庭农场的农业要素投入变量,表示家庭农场主特征变量,表示家庭农场特征变量,表示环境特征变量。为常数项,为待估计系数,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择与预期方向
(1)农业要素投入特征变量。农业要素投入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农场土地经营面积、劳动力投入以及资本投入。通常认为,土地要素投入与劳动要素投入、资本要素投入的不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生产要素间协调效率(许庆等,2011;谭淑豪等,2006),因此,农业要素投入变量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方向具有不确定性。基于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研究者特别关注土地经营规模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周曙东等(2013)认为,土地经营规模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不能简单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向还是负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考察土地经营规模与家庭农场效率之间是否存在曲线关系。如果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可能不利于农业机械作业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如果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过大,又有可能超过家庭农场主的经营管理能力,因此,预期土地经营面积与家庭农场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冀县卿等,2019)。
(2)家庭农场主特征变量。家庭农场主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农场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及务农年限。一般认为,家庭农场主年龄越大,农业生产经营经验就会越丰富,越有利于提高家庭农场的效率(Dhungana et al.,2004)。但是,家庭农场主年龄越大,也可能在意识上更为守旧,不利于接纳新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新的生产技术。因此,家庭农场主年龄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通常意义上,男性在体力上优于女性,更富有创新和冒险精神,但女性更加心思缜密,更擅长于细节管理,因此,家庭农场主性别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王则宇等,2018)。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其吸收和应用新知识、新技术,预期家庭农场主受教育年限对家庭农场效率有正向影响作用(Bojnec and Latruffe,2009;Khai and Yabe,2011)。家庭农场主具有农业从业经历、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越长,其对农业生产特性就会更加了解,因此,预期家庭农场主具有农业从业经历、务农年限越长,越有利于提升家庭农场效率。
(3)家庭农场特征变量。家庭农场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农场经营年限、经营权合同年限、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以及绿肥种植面积占土地经营面积比例。一般认为,家庭农场经营年限越长,家庭农场应对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预期家庭农场经营年限对家庭农场效率存在正向影响作用。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越长,产权稳定性越强,越有利于家庭农场经营者形成稳定的预期,因此,预期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对家庭农场效率有正向影响。农业生产中需要使用农业机械,农机作业或由家庭农场自身提供,或通过购买机农互助点、农机合作社、村集体服务队的农机作业服务。本研究将家庭农场购买农机作业服务设为1,将农机作业由家庭农场自身提供设为0。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可以节省农机购置费和农机日常维护费等,且专业化的农机作业队伍可以提供更高效的农机作业服务,但如果在购买农机作业服务时不能解决农机作业中的偷懒、监督问题,又会导致农机作业质量不高。另一方面,家庭农场自身提供农机作业服务解决了农机作业中的偷懒、监督问题,但又存在农机购置投入大、日常维护成本高、不利于发挥农机作业专业分工的优势等缺陷。因此,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种植绿肥能有效地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增加土地有机质和氮磷钾含量,有利于培肥地力、减少化肥的施用和增加土地产出,因此预期绿肥种植面积占家庭农场土地经营面积比例越大,越有利于提高家庭农场的效率。
(4)环境特征变量。环境特征变量主要用家庭农场合同期内经营权是否稳定、政府补贴、家庭农场经营中是否发生借贷款行为来刻画。家庭农场合同期内经营权是否稳定设为虚拟变量。如果家庭农场主认为合同期内经营权不会被收回,设为1;反之,则设为0。经营权越稳定,越利于调动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积极性,因此,预期合同期内稳定的经营权会对家庭农场效率产生正效应。政府对家庭农场进行补贴一方面有助于改善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状态,激励家庭农场投资,但也可能会减弱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努力(冀县卿等,2019),因此,预期政府补贴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家庭农场经营中是否发生借贷款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资本信贷市场的发育程度。家庭农场经营中如果发生借贷款行为设为1,反之设为0。家庭农场经营中如果能便捷地获得信贷支持,会使得家庭农场的预算约束线外移,有助于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购置农机设备,获得规模收益,因此,预期家庭农场借贷款能对家庭农场效率产生正效应(王向楠,2011)。
(三)计量结果与讨论
表5汇报了利用Tobit模型对全部家庭农场及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和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效率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表5中的模型1是对松江全部家庭农场效率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就农业要素投入特征变量而言,家庭农场土地经营面积及劳动力投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1中,家庭农场土地经营面积一次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土地经营面积平方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相对于土地经营规模较小的家庭农场来说,土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具有更高的效率(Ahmad et al.,2002;Cornia,1985;Villano and Fleming,2006),同时表明,土地经营面积与家庭农场效率之间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家庭农场效率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与家庭农场效率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向或负向的关系,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高。家庭农场劳动力投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松江区已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社会化服务。例如,从2007年开始,松江区由政府负责农田水利排灌设施、生产辅助设施和设备等农田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松江区建立了机农互助点、农机合作社、村集体服务队的农机作业服务网络,家庭农场可以极为便捷地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农场经营中投入过多的劳动力反而不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高。就家庭农场主特征变量而言,家庭农场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农场主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家庭农场主受教育水平越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越高,有助于其灵活应对生产环境并做出更有利于优化要素配置的决策(Bojnec and Latruffe,2009;Khai and Yabe,2011);家庭农场主具有农业从业经历,意味着家庭农场主能够在“干中学”中不断积累丰富的农业生产经营经验(邓宗兵,2010),从而有利于提高家庭农场的效率。就家庭农场特征变量而言,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为正,说明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越长,家庭农场效率水平越高。这进一步证明了家庭农场经营权的稳定性对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性。叶剑平等(2006)的研究也表明,稳定的土地经营权有利于家庭农场适时调整规模,刺激投资。家庭农场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这一变量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反而不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升。可能的原因在于,购买的农机作业服务可能存在农机作业质量不高、农机作业监督缺失的问题。研究者在松江实地调查时,家庭农场主也多次反映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与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相比,自购农机有助于家庭农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曹卫华、杨敏丽,2015),并且能够通过提供农机作业服务增加家庭农场收入。绿肥种植面积占土地经营面积比例这一变量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表明绿肥种植面积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培肥地力,对家庭农场效率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就环境特征变量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而言,政府补贴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说明政府补贴能够显著地增加家庭农场的收入,有助于家庭农场改善生产经营结构,调动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这也验证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性(李谷成等,2008)。
表5中模型2为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效率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土地经营面积一次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土地经营规模较大的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具有更高的效率。家庭农场劳动力投入、家庭农场资本投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松江家庭农场劳动力投入及资本的投入会导致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效率的损失。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经营中不需要投入劳动和资本,而是因为松江家庭农场发展有着特殊的背景。为保证松江粮食生产,松江地方政府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例如,通过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签订服务协议,实行订单式作业,为家庭农场提供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粮食生产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粮田机耕率和机收率基本达到100%;建立良种繁育供应基地,水稻良种实现区级统一供种,水稻良种覆盖率100%;提供粮食收储、烘干等全程服务,水稻收割后直接进入粮食收购点,解决了家庭农场晒粮难的问题;每年对家庭农场主进行分级培训,针对家庭农场的需求,设置不同的培训课程,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现场培训,在茬口安排、品种选用、施肥用药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技术指导。这些措施有效地实现了对家庭农场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替代,提升了家庭农场的盈利水平,降低了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经营中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投入过多的劳动力和资本,反而不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高。家庭农场主受教育年限和家庭农场主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分别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家庭农场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农业从业经验越丰富,越有利于提高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效率。这意味着,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背景下,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有足够数量的既具有丰富的农业从业经验又接受过较高程度教育训练的农业经营者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从事粮食生产。家庭农场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这一变量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这一方面表明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农机作业主要依靠购买农机作业服务会阻碍家庭农场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机作业服务供给者需要进一步改善农机作业服务质量。绿肥种植面积占土地经营面积比例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绿肥种植面积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效率。因为绿肥种植与还田,有利于改良土壤,提高粮食单产水平。政府补贴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各级政府补贴对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效率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表5中模型3为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效率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土地经营面积一次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土地经营面积平方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土地经营面积与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劳动力投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劳动力投入越多,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的效率越低。可能的原因在于,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除从事粮食生产外,还从事生猪养殖。就生猪养殖而言,松江家庭农场的生猪养殖有其特殊性。松江生猪生产龙头企业和农民家庭农场组建成上海松林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受合作社委托进行生猪代养,合作社为家庭农场提供苗猪、饲料和技术指导,农场负责代养,养殖粪尿就近还田利用。这样的生猪养殖模式不需要也不宜进行过密的劳动投入。家庭农场主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家庭农场主曾经的农业从业经历对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的效率存在正向影响作用。家庭农场经营年限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可能是因为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在生猪养殖中形成的粪尿还田是对农田的长期投资,较长的经营年限能够激发家庭农场改良土地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家庭农场的效率。政府补贴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各级政府补贴正向影响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的效率。
表5中模型4为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效率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模型4中,家庭农场劳动力投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劳动力投入过多同样会对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资本投入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效率随资本的投入而显著提高。这是因为,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不仅从事粮食生产,而且从事农机作业服务,当且只有当购置农业机械等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才能在农机作业服务时产生规模收益。家庭农场主年龄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家庭农场主受教育年限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相比较而言,家庭农场主年龄较长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对家庭农场效率的贡献率较高,会正向影响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效率(金福良等,2013)。可能的原因在于,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由于购置和使用大型农业机械,对农场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为正,说明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越长,其效率水平越高。家庭农场购买农机作业服务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这表明购买农机作业服务会降低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效率。原因在于,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自身拥有较多的农业机械,购买农机作业服务不仅增加了家庭农场的支出,而且降低了自身拥有的农业机械的利用效率。家庭农场合同期内经营权是否稳定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经营权稳定对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效率具有正向作用。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由于花费巨资购买大型农业机械,对经营权稳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稳定的经营权安排可以使经营者更加放心地做长远打算的投资和经营决策(钱忠好,2002)。政府补贴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农业补贴对提高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效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4 简要的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式的创新,大力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以实现中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家庭农场因其具有的特殊组织优势,业已成为政策推崇的重点。由于效率之于家庭农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上海松江区为研究区域、以松江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利用943户家庭农场2017年的数据,运用DEA模型估计家庭农场的效率并运用Tobit模型从农业要素投入特征、家庭农场主特征、家庭农场特征、环境特征四个维度考察其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离析影响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层面上,全部家庭农场效率不高,无论是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效率均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影响家庭农场效率的诸多因素中,家庭农场土地经营面积与家庭农场效率之间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高;家庭农场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农场主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绿肥种植面积占土地经营面积比例、政府补贴正向影响家庭农场效率;劳动力投入、家庭农场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负向影响家庭农场效率。就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而言,家庭农场类型不同,其效率及关键影响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相比较而言,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效率最高,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和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效率较低,且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率低于纯技术效率,种养结合型和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低于规模效率。影响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土地经营面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家庭农场主受教育年限以及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家庭农场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绿肥种植面积占土地经营面积比例和政府补贴。影响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土地经营面积、劳动力投入、家庭农场主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家庭农场经营年限和政府补贴。影响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家庭农场主年龄、家庭农场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家庭农场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家庭农场合同期内经营权是否稳定和政府补贴。
从本研究中,可以发现,尽管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已成为政策推崇的重点,但是,即使在松江这样一个家庭农场已有十多年发展历史、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家庭农场效率也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有着极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如何有效地提高家庭农场的效率实乃家庭农场发展之关键。为此,需要基于家庭农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离析出影响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并据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和功能,有效地提升家庭农场的效率。不仅如此,由于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效率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各地需要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本地实际的、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家庭农场类型。现阶段,需要特别注重做好以下几点:第一,要选择合适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尤其是要优先选择有农业生产经营意愿且具有农业生产经营经验的农户家庭经营家庭农场,要重视家庭农场从业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对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职业培训。第二,要基于家庭实际,合理确定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土地、劳动、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都要适度,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家庭农场经营的风险。特别地,不要盲目扩大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第三,要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切实保障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权,稳定家庭农场经营者的预期;政府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对家庭农场发展的资金、政策等扶持力度。
(作者单位:钱忠好,扬州大学商学院;李友艺,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http://www.gov.cn/test/2008-10/31/content_1136796.htm。
②参见《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http://www.gov.cn/jrzg/2014-01/19/content_2570454.htm。
③参见《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6-05/22/content_5075689.htm。
④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5-02/01/content_2813034.htm。
⑤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19/content_5366917.htm。
⑥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⑦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⑧参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_1563539.html。
⑨数据来源:松江区农业委员会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
⑩数据来源:松江区农业委员会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
⑪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是指家庭农场仅仅从事水稻和二麦的生产;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是指家庭农场除从事粮食生产外,还从事生猪养殖;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是指家庭农场除从事粮食生产外,还从事农机社会化服务;三位一体型家庭农场是指家庭农场既从事粮食生产,又从事生猪养殖和农机社会化服务。
⑫松江区建有完备的良种供应体系,政府每年4月底免费给家庭农场供应优质良种,良种覆盖率达到100%,所以,在计算家庭农场资本投入时没有包含种子投入。
参考文献
(1)曹卫华、杨敏丽:《江苏稻麦两熟区机械化生产模式的效率分析》,《农业工程学报》,2015年第S1期。
(2)曹文杰:《基于DEA-Tobit模型的山东省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山东农业科学》,2014年第12期。
(3)陈金兰、胡继连:《粮食生产类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4)陈军民:《制度结构与家庭农场的运行效率及效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5)邓宗兵:《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影响因素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6)封坚强:《松江家庭农场的探索与发展》,《上海农村经济》,2013年第4期。
(7)封坚强、王晶:《松江区家庭农场的回顾、展望与思考》,《上海农村经济》,2017年第7期。
(8)高强、刘同山、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经济学家》,2013年第6期。
(9)高雪萍、檀竹平:《基于DEA-Tobit模型粮食主产区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5年第6期。
(10)黄祖辉、扶玉枝、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7期。
(11)冀县卿、钱忠好、李友艺:《土地经营规模扩张有助于提升水稻生产效率吗?——基于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7期。
(12)姜丽丽、仝爱华、乔心阳:《基于DEA-Tobit模型的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对宿迁市宿城区的实证研究》,《江苏农业科学》,2017年第12期。
(13)金福良、王璐、李谷成、冯中朝:《不同规模农户冬油菜生产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随机前沿函数与1707个农户微观数据》,《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4)孔令成、郑少锋:《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及适度规模——基于松江模式的DEA模型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5)李谷成、冯中朝、占绍文:《家庭禀赋对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冲击——基于湖北省农户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实证》,《统计研究》,2008年第1期。
(16)李政、杨思莹:《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效率》,《管理世界》,2018年第12期。
(17)刘守英:《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调查》,《上海农村经济》,2013年第10期。
(18)刘同山、徐雪高:《政府补贴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改革》,2019年第9期。
(19)梅运田、陈永富、陈宝明、王文奇:《浙江省诸暨市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湖北农业科学》,2017年第14期。
(20)钱忠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第6期。
(21)谭淑豪、Nico Heerink、曲福田:《土地细碎化对中国东南部水稻小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中国农业科学》,2006年第12期。
(22)王丽霞、常伟:《我国家庭农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差异》,《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23)王向楠:《农业贷款、农业保险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来自2004~2009年中国地级单位的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10期。
(24)王则宇、李谷成、周晓时:《农业劳动力结构、粮食生产与化肥利用效率提升——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与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25)许庆、尹荣梁、章辉:《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基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
(26)杨万江、李琪:《我国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分析——基于11省761户调查数据》,《农业技术经济》,2016年第1期。
(27)叶剑平、蒋妍、丰雷:《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基于2005年17省调查的分析和建议》,《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4期。
(28)曾福生、高鸣:《我国粮食生产效率核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BM-Tobit模型二步法的实证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12年第7期。
(29)曾玉荣、许文兴:《基于SFA的福建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实证分析》,《福建农业学报》,2015年第11期。
(30)张瑞娟、高鸣:《新技术采纳行为与技术效率差异——基于小农户与种粮大户的比较》,《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5期。
(31)张岳:《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三阶段DEA的实证分析》,《南方农村》,2019年第6期。
(32)张悦、刘文勇:《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与风险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5期。
(33)赵鲲、赵海、杨凯波:《上海市松江区发展家庭农场的实践与启示》,《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12期。
(34)周炜:《多元化经营背景下家庭农场水稻生产效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实证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5)周曙东、王艳、朱思柱:《中国花生种植户生产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19个省份的农户微观数据》,《中国农村经济》,2013年第3期。
(36)朱启臻、胡鹏辉、许汉泽:《论家庭农场:优势、条件与规模》,《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7期。
(37)Ahmad, M., G. M. Chaudhry, M. Iqbal and D. A. Khan, 2002, “Wheat Productivity,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A Stochastic Production Frontier Analysis”,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41(4), pp. 643~663.
(38)Banker, R. D., A. Charnes and W. W. Cooper, 1984, “Some Models for Estimating Technical and Scale Inefficiencie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anagement Science, Vol. 30(9), pp. 1078~1092.
(39)Bojnec, Š. and L. Latruffe, 2009, “Determinants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rop and Livestock Farms in Poland”,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Vol. 21(1), pp. 117~124.
(40)Charnes, A., W. W. Cooper and E. Rhodes, 1978,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ol. 2(6), pp. 429~444.
(41)Coelli, T. J., D. S. Prasada Rao, C. J. O""""""""Donnell and G. E. Battese, 2005, An Introduction to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 Springer Publishers.
(42)Cornia, G. A., 1985, “Farm Size, Land Yields an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 an Analysis for Fift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13(4), pp. 513~534.
(43)Cooper, W. W., L. M. Seiford and K. Tone, 2007,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 Comprehensive Text with Models, Applications, References and DEA-Solver Softwar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44)Dhungana, B. R., P. L. Nuthall and G. V. Nartea, 2004, “Measuring the Economic Inefficiency of Nepalese Rice Farms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Resource Economics, Vol. 48(2), pp. 347~369.
(45)Khai, H. V. and M. Yabe, 2011, “Technical Efficiency Analysis of Rice Production in Vietnam”, Journal of ISSA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outheast Asian Agricultural Sciences] (Philippines), Vol. 17(1), pp. 135~146.
(46)Imori, D., J. J. M. Guilhoto and F. A. S. Postali, 2012,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Family Farms and Business Farms in the Brazilian Regions”, Mpra Paper.
(47)Latruffe, L., K. Balcombe, S. Davidova and K. Zawalinska, 2005, “Technical and Scale Efficiency of Crop and Livestock Farms in Poland: Does Specialization Matter?”,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32(3), pp. 281~296.
(48)Larsén, K., 2010, “Effects of Machinery-sharing Arrangements on Farm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Swede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41(5), pp. 497~506.
(49)Leibenstein, H., 1966, “Allocative Efficiency vs. X-Efficien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6(3), pp. 392~415.
(50)Madau, F. A., 2015, “Technical and Scale Efficiency in the Italian Citrus Farming: Comparison between SFA and DEA Approache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view, Vol. 16(2), pp. 15~27.
(51)McCloud, N. and S. C. Kumbhakar, 2008, “Do Subsidies Drive Productivity?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Nordic Dairy Farms”, Advances in Econometrics, Vol. 23(8), pp. 245~274.
(52)Mugera, A. W. and M. R. Langemeier, 2011, “Does Farm Size and Specialization Matter for Productive Efficiency? Results from Kansa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Applied Economics, Vol. 43(4), pp. 515~528.
(53)Villano, R. and E. Fleming, 2006, “Technical Inefficiency and Production Risk in Rice Farming: Evidence from Central Luzon Philippines”,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ol. 20(1), pp. 29~46.
(54)Wang, L., X. Huo and M. S. Kabir, 2013, “Technical and Cost Efficiency of Rural Technical and Cost Efficiency of Rural Household Apple Production”,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Vol. 5(3), pp. 391~411.
(55)Zhu, X. and A. O. Lansink, 2010, “Impact of CAP Subsidies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rop Farms in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and Swede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61(3), pp. 545~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