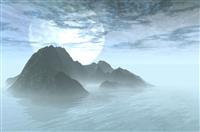男,1956年出生,湖南长沙人。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
著作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 。
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对立,而更可能是一种互补。社会成为公民和国家间的中介,在许多方面,国家通过社会对公民进行管理;同时,社会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国家的不正当侵犯,公民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社会这种渠道合法、平稳地表达,而不会也不必通过过激的方式表达。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体制内”的沟通,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可以说,中国30余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逐步开始了“社会重建”。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1周年。101年前的那个午夜,没有人会预料到,汉口新军仓促之下的一次起义,竟然会让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
其实,清王朝的覆灭早现端倪。从鸦片战争起,这个古老的国度首次遭遇另一个文明世界的现代性挑战,而清王朝显然无力解答这道历史难题。时至今日,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仍在蹒跚中前行。
知名历史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在这些年的历史研究中不断提及这个主题。本周六(27日)下午两点,应主办方邀请,雷颐将担当湘江大讲堂的第七期主讲嘉宾,给株洲市民们带来一场主题为《晚清变局——改良与革命》的讲课。
21日晚间,本报记者对雷颐先生进行了专访,在讲课开始前,跟他一起聊聊中国在现代性转型的道路上的种种。
1、“晚清史”之所以热,是因其对当下中国转型仍有启示意义
记者:雷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邀请到您担任“湘江大讲堂”第七期主讲嘉宾。您本次讲课的主题为《晚清变局——改良与革命》,最近几年,史学界对晚清这一段的历史似乎特别青睐,您这次要讲的这个主题,也是近年史学界经过长期“论战”后形成的共识。您觉得,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晚清热”?
雷颐:一位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说,当一个历史事件失去当下的参照意义,不成为当下人们的“心理投资”后,就会脱离社会论战的领域而回到学者的纯书斋中。反过来说,当一个历史事件仍给现实社会以启示或借鉴意义,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学者的书斋,而会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因为中国目前的现代性转型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与晚清相当类似,所以,这些年形成晚清热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记者:鸦片战争后,中国古老的国门被西洋文明的坚船利炮被迫打开,乃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来应对,但当时的主流却将此视为大逆不道之举。放在今天来看,学习他人的长处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时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大的阻力呢?
雷颐:因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认为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夏文明才是文明、文化,其他的都是野蛮世界。所以,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相当强的力量认为“师夷长技”就是“以夷变夏”,所以主张师夷长技的林则徐才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
记者:同样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在去年热映的影片《赛德克.巴莱》中,导演魏德圣借剧中主角莫那鲁道的口说道:“如果你们的文明是叫我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见识见识野蛮的骄傲。”这引发不少人的讨论,将之移植到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朝野之间的“论战”,似乎能为“主战”一派找到内在的合法性,您又是如何看待这句话的呢?
雷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并非屈膝投降,并非“主和”。还是要提到林则徐,他是标准的主战派,但又主张向敌人学习。人们往往容易把主张学习敌人长处者认为是主和,甚至认为是投降派。
2、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有其自身道路,但基本原则和价值是相同的
记者:相比洋务派孜孜以求于西方先进的“器物”之道,严复则第一个系统地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引进中国,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举足轻重。而辛亥之后,严复在思想上开始“回归”中学,对以往他所摒弃的中国传统思想大唱赞歌,甚至成为鼓吹君主立宪的“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严复这种前后矛盾?最近,也有学者提出“儒家宪政主义”的理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雷颐:西方文明,或者说现代性并不是没有缺欠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极大缺欠的。当严复后来对西方文明或现代性文明的缺欠有相当认识后,他有了反思,不过,他不是想以中国传统来补其弊端,而是想取代现代性。所以,后来他才会成为筹安会的发起人。
当年,康有为一心想建构儒教,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就公开反对。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儒学时期,梁对乃师的再造的“儒学”大为折服,随后就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更是依老师康有为之说,积极主张奉孔子为“教主”、“圣人”,主张立儒学为国教,以此作为变法的最重要理论根据。
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思想进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脑质”为之改变。他脱离了维新时期以“托古改制”宣扬改革的中国传统话语,而更多地以“西学”词汇、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而同样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此时仍坚持“托古改制”理念,并在海外更为积极地进行以孔子为国教的“保教”活动。对此,梁启超渐生歧意,终于在1902年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国教”,与乃师大唱反调。开篇他即声明:“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他承认,自己曾是“保教”大旗下之“一小卒徒也”,但现在之所以反对,首先因为“教非人力所能保”。他认为各种宗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竞争发展。
面对各种几乎是势不可挡的“新学”,当时的“保教”论者亦有人力论可以用现在的新学说、新理论重新解释孔子,对此,梁启超大大不以为然:“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但这其实是“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他认为孔子所见或有与今日新学理暗合之处,然若一定要将二者一一比附纳入,这种思维的实质还是因真理与孔子暗合才接受,“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而对那些不能与孔子暗合的学理,“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也不敢接受、遵从,结果是阻碍真理在国人中的传播。为此,梁启超专门给老师康有为写信,反复陈说自己反对保教的理由。
读史观今,梁氏的观点对今人仍有启发意义。
至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其发展之路与形式每个国家都不能脱离自己的传统,都有各自的道路与各自的形式,但基本原则和价值则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