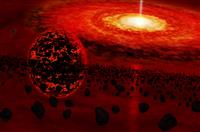高难度的头卡项目
“把最难啃的骨头给你们”
一般而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NGO需要综合考虑社区的状况和项目的难易程度,通过选点来提高项目的成功机率,以便产生示范推广作用,蜀光最初也是这个思路。
但2004年底选择头卡,有些不按“常理”出牌的味道。当时,为实施蜀光和国务院扶贫办外资中心牵头进行的4省5县“NGO承担政府扶贫任务”联合试验项目,蜀光去小金选点,县里特意要将新桥乡头卡村交给蜀光来做。
“当时我很忙,是杜玲去选点,她比较感性,看到那里比较困难,也就答应了。”蜀光负责人韩伟回忆当时的选点过程。后来,蜀光在村里不断遇到麻烦,项目推进一波三折。村民开会动不动就撂挑子,还当着乡书记和蜀光人员的面打架,蜀光这才意识到自己啃到了一块最硬的“骨头”。
蜀光的项目负责人杜玲转述当时的小金县扶贫办熊主任的话说,“参与式那么好?好在哪里?那就把最难啃的骨头交给你们。”其实熊主任当时还埋下了一个伏笔:将投入同等规模的扶贫资金、采用传统方式进行新村建设的新民村,和引入参与式的头卡村进行对比。这是小金县头一回在扶贫领域引入NGO和参与式。
“头卡特能整。”杜玲说。这个小金藏族自治县中的汉族村,据说是乾隆打金川的军队后裔,解放前就以“枪多,匪多,鸦片多”、民风“刁悍”闻名于外。由于山高地形险,沟壑纵横,土地产量低,村民依靠种地、挖药、打工等多种营生,生计困难,726人的村就有200多人在外打工。由于长期积压了大量难以化解的矛盾,一位走马上任的乡长就曾表态:要力争当一个不挨村民揍的乡长。
韩伟说,由于头卡的复杂性,使蜀光在该项目上的运行成本起码增加了1/3。不过,拿了这块“烫手”的山芋,蜀光最终还是知难而上。“歪打正着的头卡是一个大炼炉,是蜀光熔炼和提升机构能力的机会,我们收获特别大。”
事实上,正是在头卡以及后来在小金开展的其他项目,为蜀光打开了空间。2009年,小金县扶贫办委托蜀光在40个村全面推行社区互助基金。现在回想起来,其中的曲折仍然历历在目。
村两委和管理小组
自2005年蜀光正式进入头卡村,也就介入了村内复杂的矛盾漩涡。当时的村主任有能力但很自私,在任期间打了很多欠账白条,村民担心他赖账,换届时还不得不选他连任。而村书记70多岁,年事已高, “不理朝政”,任由村主任主导村务。
实施项目的第一步是动员村民公选成立项目管理小组。公选后,村两委主要成员没能选进项目管理小组。村主任觉得自己权力旁落,制造了很多障碍。韩伟讲述了一个挖挖机(推土机)的故事:工程建设需要雇用挖挖机,对挖挖机的掌控是村建工程的一种权力表现。按照协议,请挖挖机是管理小组的分内之事,但村主任避开管理小组自己到县上雇回了挖挖机,价格高于市价不说,还谎称县上的扶贫款是他拿两头羊换来的。村主任一方面以此显示自己的权力,同时也给选出的管理小组出了道难题。后来,他又在村里散布,说扶贫资金能不能够到村还是个问题。他的系列动作一度使管理小组陷入被动。
第一代管理小组
管理小组的成立和“改朝换代”也颇有曲折。2005年4月,为抢在洪水爆发前抢修河道,要公选一个临时性的河堤管理小组(临时小组)。“大家都在观望,不愿意站出来。”现任村书记魏新品回忆,第一次公选时大家心里没有底,得票多的一些人不愿意进入临时小组。魏新品和张君永都是当时得票最多的人,因为怀疑资金能否真正兑现,怀疑临时小组是不是真正有权力,加上家里缺乏劳动力,不愿意参加临时小组。之前,抢修河道的资金使用出现一些小问题,村民对以村两委成员为主的临时小组缺乏信任。
同年5月,抢修河道完成后,临时小组结束了使命。在选举正式的管理小组时,大家总算动了真格,魏新品、民兵连钟连长和张君永入选,这次他们站出来承担起责任。魏此前曾担任过11年的村主任,选举时已是“平头百姓”。2007年7月项目结束后,第一代小组的组长魏新品成为头卡村村书记,张君永成为村会计。
第二代管理小组
汶川地震灾后的2008年12月,蜀光在香港社区伙伴支持下,又投入10万资金搞灾后重建,其中5万元用于建立社区基金。结果矛盾又出来了。
尽管引入了严格的公示制度和参与制度,部分村民仍然对第一代管理小组不满意,怀疑小组在财务上有什么猫腻。似乎部分是出于排斥村两委的心态,村民们再次提出重新公选小组来管理新的项目,产生了第二代小组,梁明富为组长,原来的小组成员退出。
当时,面对复杂的矛盾,选上的人也有畏难情绪。蜀光在社区进行了动员并帮助设计了公开透明的制度。
2009年1月15日,经过反复讨论,项目小组公布了社区基金管理方案,内容非常详细,预设了很多可能遇到的难题和应对方法,操作性很强。韩伟说,长期的矛盾冲突,导致大家防范心理重,反倒对可能产生的含糊和漏洞提前想到了应对之策,方案实际上体现了社区内各种复杂的制衡关系。头卡记录草案的大白纸据说就用了7张,是进行社区基金方案讨论最繁杂的村。
从蜀光的角度,实际上第一代小组运行得不错,没有必要改选,但蜀光尊重了社区的选择,尽力“引导新小组站在老小组的肩上”,搞了几次相关的培训交流,还通过一些微妙的“小动作”发出暗示。例如,蜀光进村和小组开会,第一次在新小组长家开,以后在老小组组员家开。设法利用蜀光在社区的信任和影响,促进新老小组之间合作,传承经验。
此外,作为“外来的和尚”,蜀光极力调和村委和小组的关系,利用乡政府的支持,理清两者关系:乡上授权管理小组,实施项目以小组签字认可为准;两委的角色是按照小组提交的投工投劳方案组织动员和协调,并行使验收和监督职能。蜀光与乡政府保持着流畅的沟通和协调。
“现在村两委对新小组支持力度大,跟得上趟,我觉得轻松很多了。”杜玲说。
参与的力量
公选的小组为村民自我管理提供了舞台。第一代小组成员张君永清晰地记得,在2005年5月24日,也就是他被公选进入管理小组担任会计的第二天,蜀光在村里搞参与式培训。“一张报纸上站人,学习少花钱多办事;两人一组蒙眼走路,帮我们思考如何解决冲突矛盾,给了我们很多智慧”。
后来,参与意识被村民们发挥得“淋漓尽致”。挖挖机在前面挖,管理小组就带着村民跟在后面干,节省了10万元工时费。物资采购也是多方询价,采购的物资比其他村质优价廉。
最后,头卡村用这47万元,完成了河堤、公路、学校、村两委会议室、卫生站、电力、桥梁改造等多项工程,还用结余的钱资助村民购买了太阳灶。而作为对比的新民村,采用传统的方式花50万资金,只完成了修路和建学校两项,村民对村两委很有意见。时至今日,头卡的管理小组和村民们对此还颇感自豪。
县政府开始的时候也觉得参与式很麻烦,抱着试探对比的心态放手给蜀光,结果让政府看到这种方法对改进乡村治理的价值。
蜀光进入头卡,使村里的状况发生了改观,但这个过程远非完美。在扶贫新村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过重大的安全事故。二社实施架设高压线路时,社长因私心和各户发生冲突很难协调。后来在架线的时候,由于对安全问题重视不够,在搭线的过程中触电导致一死两伤。
在韩伟眼里,现在的头卡仍然是一个千头万绪,充满复杂矛盾的地方,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慢慢改变,参与式在头卡的路还很长。
牧区草场管理和社区基金
(一)丹巴县牧业村
2009年12月24日一早,丹巴县半扇门乡四面的群山在晨曦中露出皑皑白雪,空气中透着清冽的寒气。调研小组来到乡政府,见到了头一天从山上走了3~4小时下来的牧业村草场管理小组和村长一行。乡长郭太和副乡长扎波等人也一同挤在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大家围坐在简陋的电炉边交谈,说起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出现前后的情况。
牧业村的草场资源一直很贫瘠,和外界想象中的草原大相径庭。当地人称为草山的地方,毒草多,沙化石化严重。由于坡高山陡,每年都有牲畜不小心摔死。更糟糕的是,由于长期过载和乱牧,草场开始退化,村民们忧心忡忡。
“外乡的牛乱放,本村也乱放。你喂100头,我就想喂200头。 (沙化严重),泥巴都要啃一回。” 村长牟光全描述当时放牧中的混乱情况。
项目负责人杜玲说,蜀光进入社区之前,牧业村各组之间,与外村、外乡甚至外县之间边界不清,放牧时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尽管牧民们深知控制牲畜量的必要,也试图做出改变,但由于社区组织化程度低,村规民约不起作用,乡上的减畜政策也得不到落实。
2008年,在蜀光支持下,村里公选了草场管理小组,4万元社区基金派上了用场。基金的借贷管理制度附加了草原保护的约束性条件。管理小组还利用福特基金会资助的1万元草场建设资金,以及2008年地震后的8000元灾后重建资金,由下辖的4个小组投工投劳用石头围栏和少量钢围栏划分了与外乡和各组之间,以及冬春草场的边界。大家按规矩定时转场,每年能使草场休牧几个月。控制载畜量的举措也得到落实,破坏性大的猪和羊已经全部弃养,全村的牛从2000头减少到1600头。
管理小组组长杨天华解释,过去作为传统,外面有6~7个农业村的村民一直都来牧业村放牧或寄养牲口,现在严格限定了条件,只有耕牛可以寄放,而且规定了每户最多能寄放的数量。
社区还组建了饲草实验兴趣小组,在草科院专家指导下在沙化地上试验种草。经过多方比对,确定了产量高的草种,由政府和蜀光投入资金帮助购买草籽,每户两亩割草基地基本能解决冬饲社区大会杜玲摄料的问题,有效减少了牦牛的冬季死亡。乡上还资助引入良种牦牛,在保持收入的前提下,草场沙化的情况也初步得到遏制。
基金的使用也是有章可循,并以民主透明的方式决策。大家讨论定下了贷款年息(6%),贷款额度(每户2~3千),以1年为期。管理小组会计尹正刚拿着账本给大家报账:截至当日,放贷13户,初步收回了9户,当年利息收入达到1400多元。尹正刚脸上透着满意的神情,他估计这一轮借款全部收回后,利息所得会超过2000元。按照基金的管理规定,如果每年利息收入500元以上,就可以抽出100元做办公费用,并给小组成员每人每年补助100元,这使长期垫支工作经费的小组成员们松了一口气。
进入牧业村的缘起
现在,牧业村的社区基金声名在外,邻近的阿坝、甘孜的牧民纷纷前来学习取经。按村长牟光全的话说,牧业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乡长郭太对此表示赞同,他2006年底调来半扇门乡。细数乡上的22个村,牧业村是唯一的纯牧村,平均收入低于其他农业村。由于乡财政一直拮据,郭太对牧业村的发展有心无力。
2007年选择草原试点村的时候,杜玲从小金县城过去,看地图发现以农为主的丹巴半扇门乡还分布着小草场。有着扶贫背景的杜玲凭借直觉认为,这很可能是个被“遗忘”的地方,跑到乡上一打听,果然如此。这是一个“独独的纯牧业藏族村”,当时乡上干部刚刚换届满一年,村路还没有修通,从乡上到村走路单程就要7个小时,只有一位包村干部上山去过两次。十几年来,这个村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支持,不过是铺设了2公里的水管,以及50多斤草籽。
“乡上财政难,社区基金就像救命稻草。开始的时候觉得(蜀光的做法)很新鲜,自己也不懂,但觉得可以试一试。”郭太很爽快地同意了蜀光这个外来的“和尚”进村帮助改善草场管理和实施社区基金。
副乡长扎波说,“引入社区基金,对政府来说是一种观念和工作方式的转变,政府容易着眼于修房修路等当前的变化,缺乏长远的技术支持,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考虑不足。社区基金的运行是对政府工作的深化。”在扎波眼里,蜀光提供的参与式理念和技术,正是政府所缺的短板,这是项目运行至今扎波得到的体会。
保持轮牧的传统
牧业村围栏划分边界,并不是要放弃传统的轮牧。头脑清醒的村长牟光全说:“4个组界限清楚了,再围就‘刹车过灵了’”。他的意思是,围栏是为了划分边界,制止过载,并使冬春草场得到有效的休牧,使本村范围内能够保持轮牧的传统。村里不会像政府资金投入大、干预强的其他草原地区那样将产权划分到户,搞成定居和围封。这个村的围栏,在功能上和四川的若尔盖、红原等地大片草原的围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听说当地政府规划要加大投入,建设牧民新村定居点。蜀光负责人韩伟对此产生了忧虑。这些主流化的政策,由于投入的资金量大,有可能扭曲现有的轮牧带来的草场平衡。
除了这方面的担忧,总体上牧业村的社区基金运行尚好。不同于头卡这样的汉族社区,藏族社区由于文化上的影响,矛盾冲突较小,所缺乏的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机制。在外来力量的辅助下,有了好的机制,自己就能运行起来。蜀光结合藏族传统文化中的村规民约,将草原保护与社区基金的运行捆绑,恢复强化自然保护的传统。在这里,社区基金主要不是融资手段,而是基层组织化建设的工具。草场管理小组同时也是社区基金管理小组,这为牧民们创造了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机构,带领大家长期有效地管理草场。
“多此一举”的交接仪式
蜀光在推动社区基金的时候,“处心积虑”强化社区民众的参与意识。社区基金是村民共管共受益,是全村村民的共有资产。为了强化村民对社区基金的拥有感,虽然可以通过培训和文本形式对这种权属关系加以固定,但对初涉其中的村民来说,似乎还是有些抽象。蜀光在牧业村出了一招:将资助款4万元带到社区,安排了一个看上去“多此一举”的交接仪式。
社区基金的成立现场摆放了两张桌子。一张旁边坐着蜀光的人,将4万元平分到户,由各户签收领取,这些钱进了村民兜里,就等于从资助方的钱变成他们自己的钱。旁边一张桌子旁,则坐着选举出来的管理小组成员,各户将拿到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交给管理小组签收,意味着村民拿出自家的钱,委托小组进行管理。这两个环节之间,村民们自发想到,男村民要抽一支烟,女村民吃一颗糖。杜玲说,这样的交接仪式,是希望将资金的权利关系具象化,使村民强化参与的权利意识,加大贷款管理的监督压力。后来,这样的仪式被复制到其他的试点村上,效果不错。
(二)两河乡前锋村大沟
同是藏族牧业村,拥有34户牧民的小金县前锋村大沟,也引入了福特基金会资助的4万元社区基金,从2008年10月开始正式运营。另外投入1万作为草场建设资金,29万元地震灾后重建资金。
“大沟17万亩草地,沙化退化严重,有的地方成片的像扫把扫过,看不到草,露出黑压压的一片。”村书记老唐一席话,不由使人联想到丹巴县牧业村,两村的草场退化大概不相上下。
和丹巴县牧业村一样,前锋村大沟同样采取了围栏划分边界、减少载畜量和贷款种草,改良品种等多种措施。管理小组金会计说,村里围绕社区基金达成的共识是,牛的配额是每人20头,羊全部取缔,每户马不超过4匹。
大沟村民在2009年行动起来。现在,3个组已经全部淘汰了羊,并按照计划减少牛的数量,以质量换数量。由于一头牛的价格抵得上三头羊,把破坏性大的羊减下来,加上草场变好,减少了牛的死亡数量,收入并未下降(以前每年冬季要死亡500头左右)。
管理小组成员老罗说,4万元基金除留下3000元应急,其他全部贷出。今年大家贷款都是修理地震破坏的房子,到明年就要开始发展生产了。金会计说,还款情况非常好,目前已取得利息1025元,很快会进入第二轮借贷。
同样是藏区社区,大沟的内部冲突也不大,社区关系较为和谐,加上家族信用的纽带,有了社区基金这个可行的机制,很快就触发了村民的行动,使各种措施落实到位。2009年有一户人家不遵守轮牧制度,违反约定提前从春牧场赶牛下来进入冬季牧场,结果管理小组以每天50元的标准进行罚款,村规民约不再像以前那样停留在纸面上。
推广的效应
紧邻大沟的前锋村牛场沟,是40多户的大组,福特基金会给了4万灾后重建款修房子,但村民觉得钱花完就完,也要效仿隔壁的大沟搞社区基金,细水长流。据说牛场沟的人来大沟取经,两边的人喝着酒摆谈一番,回去就动员起来。
后来,小金县政府拿钱在更多的村里面推广社区基金,蜀光为首批13个试点村举办培训,牛场沟和大沟都有人去现身说法。
蜀光看好社区基金这种扶贫方式,认为社区基金由公选的村民小组进行管理,围绕基金的运作可以对社区能力建设产生持续的影响,是一种能够持续滚动发展的模式,符合蜀光的“推动村民团结合作,共建家园,创建和谐农村”的宗旨。而为其他特定项目成立的特殊小组,则容易在项目结束后人走茶凉。当然,蜀光的项目负责人杜玲也指出,社区基金的运作形式受参与人员以及具体环节设计等诸多因素影响,运行时间也不长,还需要时间去观察。
现在,NGO参与扶贫的格局在小金已初露端倪。除了蜀光在这里默默耕耘的努力,也与2000年以来政府开始推行参与式村级扶贫的背景高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