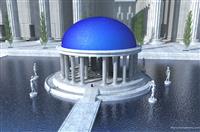2014年8月29日,腾格里额里斯镇,腾格里沙漠深处,数个足球场大小的长方形的排污池并排居于沙漠之中,周边用水泥砌成,围有一人高绿色网状铁丝栏。其中两个排污池注满墨汁一样的液体,另两个排污池是黑色、黄色、暗红色的泥浆,里面稀释有细纱和石灰。陈杰/摄
我很庆幸,当初不仅没有挨打,而且从L先生那里管窥到很多行业历史的断面。他如今在创业,试图研发出一套真正节能环保的工艺。我期待他个人成功,以及整个行业的变革。
这是一场奇异的交情。三年前我做记者时,报道过十几家企业在西北干旱地区非法排污的故事。结果是这些企业全被环保部挂牌督办了。其中遭殃的一家公司老总L扬言,如果再见到我,要把我抓起来打一顿——半年后真的见到了。我去当地回访,采访这些正在整改的企业,开始了解一条从沿海向内地高污染化工项目转移的链条。这件事开启了我对中国精细化工行业历史及其环境影响的探究之旅。
2017年10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一个农药化工行业高端论坛上,我又碰到了L先生。他说他辞职创业了,我有些吃惊。毕竟他已50多岁,看起来健壮,但身体并不好,每天晚上要吃好多种药。我问他去干嘛了。他说,在大西北沙漠里头的工业园区折腾实验,想利用某种革命性新技术,生产几种重要而紧俏的化工原料。这种新技术不仅生产成本低,而且他特意强调,“污水排放量非常小,节能环保。”
他这么说,是有苦衷的。他曾在江苏一家化工企业担任副总,2010年后东部沿海省份不少工厂纷纷西进,看上的是西部土地、原料和能源价格低廉,以及“环境容量大”的优势。当地政府正好大力招商,一拍即合,审批环保工艺和设备时,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不少高污染项目落户到了西北地区。L先生当时供职的企业也到西北某省区设立分厂,一年之后,因为排污问题被督办,我们不打不相识。
L在农药行业干了近30年。上世纪80年代末,他是一家农药厂里少有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从车间主任做起,40多岁便成为公司的副总。他的故事差不多是中国农药产业的时代缩影——国营工厂时期,创业者们埋头苦干,抢建国外农药品种,尽力满足国内农业发展的市场需求;企业改制之后,经营得力的企业家们逐渐致富。然而与财富积累并不同步的是技术和环保的升级,直到遭遇最近几年的环保风暴,他们才真正直面压力,不少企业因此而搬迁或倒闭。
L先生的工作经历,是该行业上世纪80年代至今飞速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我过去总认为,精细化工行业废水量大,污染重,是因为政府实质上放弃了监管。但从他的故事中,我找到了另一个原因,国内整个精细化工行业的基础研究仍十分落后,而环保工艺是依附于整个产品研发和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如果化学品基础研发没有突破,所谓的环境表现便只能同监管者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当然,也可以说,归根结底还是监管问题,用当前一句流行的口号来说,便是用环境管理倒逼产业升级。
不打不相识
L先生是主管生产的公司副总,在2013年阔别太太和年幼的小儿子,带领一部分员工随工厂搬到了西北沙漠地带。冬天最冷时低于零下10度,海拔1400米,气温、气压同江苏很不一样,需要慢慢地调试生产装备。投入生产还没多久,就被媒体曝光,然后停产整顿。
2015年3月,我见到L先生时,他正被环保督查的事搞得焦头烂额。他曾说,如果有一天再见到我,要把我抓起来打一顿。
我是他当日接待的第四批访客。之前有西北某省区的环保厅、市环保局和市人大督察组的官员。因为工业园区好几家企业排污,被中央督办,市里政治气氛骤然紧张,先是开了全市环保动员大会,然后多个政府部门齐上阵,轮流盯着。企业早已停产,忙着处理危机。
2014年8月31日,腾格里额里斯镇,腾格里沙漠深处,数个足球场大小的长方形的排污池并排居于沙漠之中,周边用水泥砌成,围有一人高绿色网状铁丝栏。陈杰/摄
我算是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五个月前,我在供职的媒体发表了一篇报道,点名若干企业在西北沙漠地区将污水排到挖好的大池子中,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没想到影响很大,三个省区的多家企业被环保部挂牌督办,停产整顿。L所在的公司就是倒霉者之一,他们不得不花几千万去买新的污水处理设备,把以前排出去的黑臭污水抽回来,重新处理。
之后,当地市委宣传部邀请我回访工业园区,采访整改进展。L先生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他办公桌上放着药瓶,烟一支接一支地抽。那天,我们一行人头戴安全帽,参观车间、污水处理站还有惹事的污水池。
走到池边,L先生弯下身,用手一把一把刨开埋土,揪出里面一层厚厚的土工布,有点激动地对我说,这下面的确是铺了防渗膜的啊,而且有好几层!
那天走访了四家企业,每位老总都愁眉苦脸。我发现个有意思的情况,这些化工企业都来自江苏。交谈间,有些人的口音我听着吃力。在塞外沙漠的初春,大风不时吹来,沙子扑面迷眼,听着一串串吴侬软语,有种时空错乱的恍惚感。
他们偶尔流露出对家乡的思念。毕竟从江南来到这里,环境差异太大,任谁都不适应。
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化工厂多布局在东南地区的市区边缘的河流旁边,都是长期土法生产,污染严重。直到2000年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早日的明星企业、利税大户,逐渐成为遭人嫌弃的污染大户,被政府要求搬迁或关停。
由于地价飞涨,政府将厂区土地收回后,亦有足够的钱来补偿企业搬迁,于是在化工业发达的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企业纷纷踏上搬迁之路。2005年前后,很多苏南的中小化工企业搬到苏北沿海地区,利用靠海的天然优势肆意排污。2010年后又有一批企业搬到更远的西北地区,那里荒漠广布,环境容量大,不用担心异味扰民。
他们从野蛮生长的年代走来,当时不会想到往荒无人烟的沙漠里排污,后果会有多严重。故事发展有出人意料的戏剧性。2014年园区里多家企业被媒体曝光,2015年开始整改,斥巨资修复土壤和地下水。企业只能半死不活地勉力维持。期间还被一家公益组织告上法庭,提出环境公益诉讼(然而当地两级法院均以非常荒诞的理由拒绝立案,原告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在其支持下获立案,后来还被最高法院列入中国十大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17年11月16日,第一批中央环保督查问责情况公布,称该园区多家企业由于污染问题“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强力整改”,一批市级官员被问责处分。
沙漠“零排放”神话
更早之前,在西北沙漠地带的工业园里流传着污染“零排放”的神话。2014年秋天,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内蒙古、宁夏和陕西三省区采访调查,试图弄明白真相。
简单来说,这些地区煤炭资源丰富,地方政府想把煤用起来,发展GDP,遂鼓励发展煤化工项目。加上近十来年东部高污染项目逐渐往内地搬迁,西北高污染工业项目越来越多。
然而这些项目面临着一个致命问题,沙漠里没有河,黄河早就严格限制新建排污口,污水上哪儿去?更何况化工废水含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严重,难以自然降解。于是一种叫“零排放”的工艺应运而生,大意是,将污水层层处理成浓盐水(盐是无法去除的),然后排到一个做了防渗处理的池子里,西北气候干旱,水分晒干后,再把余下的盐拿出来,就实现“零排放”了。
国内最早搞“零排放”的,是国企神华集团。不过,其位于鄂尔多斯的煤制油项目,用于“零排放”工艺的蒸发塘曾被国际环保组织调查发现,排入处理池中的所谓“浓盐水”实为污水,含多种有毒有害物质,甚至还有污水被偷排到沙坑中。
口子一旦打开,其他企业也找到了上马的理由,纷纷在西北沙漠地区搞高污染项目。明知无法真正实现“零排放”,地方政府照批不误。在后来面对媒体采访时,被罚的企业主们颇为委屈地拿出环评报告,说,这些都是当时拿到政府批文的。
有人这样对我形容,地方政府对待招商来的企业有三招,即扑克牌中的“JQK”——先把你勾过来,再圈住,最后尅(揍)你,隐隐地表达对地方政府“不负责任”态度的不满。他们说,当时允许企业来投资建厂,对这种污染处理模式是默许的,各种审批文件一应俱全。然而当更高一级的政治压力下达时,挨刀的只是企业。
当时,我一点点摸索,找到100多个疑似排污池——从谷歌地图上找沙漠里又黑又大的池子,并不困难。然后挑选其中一部分,到实地去核实。当时我到西北某省区的一个城市,打车前往工业园区,途中出租车司机抱怨说,这一片工业园区建在荒滩上,以前是坟场,当年为了盖工厂,强行迁坟,如今污染又严重,老百姓很不满意。
到达目的地后,才打开车门,就闻到随风扑鼻而来的阵阵臭气。我走到排污池边上,用手机拍照取证。很快,池边两个穿军绿色棉大衣的保安发现,飞快跑过来,拦住去路,要求删照片,并且已打电话汇报,等领导来处理。
那是漫长的半小时。来了几个头戴安全帽、和颜悦色的中年人。看起来非常客气,问我何所来。我谎称是某大学的学生,出来做荒漠生态调研。对方说,我们现在很紧张,就怕是记者,那就麻烦了。寒暄一阵,便放我走了。
不知道L先生当时是否也在其中。我后来没有问过他,毕竟当时场面狼狈,不愿再追想。后来L先生双手有些哆嗦地把一份追究法律责任的司法文书呈在我面前,我是有些后悔的。当年刚从大学毕业一年半,内心澎湃,如今发现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就这样在某个人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疤痕,心里生出深深的烦恼,但又不知如何消化。
后来那次回访结束的时候,L先生让他的司机送我回酒店。路上,司机说,之前有一个女孩子来过我们这里,但她说自己是学生,不是记者,那个人是你吗?我坐在副驾,眼睛直直看着前方的路,说不是我。
那次的报道影响很大,当地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和副市长跑到北京拜访我的单位,热情邀请我前去回访。对于记者来说,自然是很好的机会,可以当面去问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污染困局如何形成,就像能解一个未了的谜。
回访的时候当地气氛依旧很紧张。园区管委会和市环保局的人还住在企业宿舍。因为环保局局长被免职了,我只能采访到副局长。刚聊几句,他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另一家媒体。他语气疲惫地告诉对方,现在所有人都在园区驻守,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挂了电话,他翻下手机说道:“打了20分钟电话,22个未接来电。”末了他说,“我们再也受不了舆论方面的打击了。”
那几天,我见到的所有人,都仿佛在刀尖上行走,一步一小心,见到我尤其紧张。对于L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我怀有无法释怀的歉疚之心。在回访结束离开的当晚,我给L先生的司机发去一条短信,向他道歉,说那个人是我,而我对他说了两次谎。
14年出不来一部排废标准
两年半后,我和L在上海重逢,他拖着一大一小两只行李箱,里面塞满了衣服。10月下旬,他穿着羊毛衫从西北回来,一下飞机就显得热了。他说,我四个月没回家了,这次回来,把冬天衣服打包带走。
从上海回到他老家,我们一路聊天,还同行坐了一趟地铁,出地铁站,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两口,环顾四周,说,几年前,带手下兄弟去西北建厂,每次给下属批假,不敢超过一周,趁他们还没回过神来,好回去继续上班——呆得再久些,难免心思生变。
“现在是吃蟹的季节,再等些时候,公蟹的膏就出来了。”他说,不理解为什么西北那个城市的菜那么贵,随便炒一盘菜都要20多块钱。而在老家,一笼蟹黄汤包才18元,能看到货真价实的螃蟹肉。
也是在此时我才知道,当年的沙漠排污事件没有平息。涉事企业的地下水修复工程还在持续,追究法律责任的司法程序仍未终结。这颗石头,两年多来一直这样沉甸甸地压在L先生的心上。
我问他,你们这些做农药的,怎么看待农药工厂废水对环境的污染,不觉得痛心吗?
他说,你知道多菌灵吗?这是中国很少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品种,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想仿制美国的苯菌灵,结果苯菌灵没做成功,中间一步做出了多菌灵,发现这是好东西,广谱杀菌,所以起名叫“多”。现在国外用的多菌灵,都是中国出口的。
多菌灵是由沈阳化工研究院和原化工部规划司的人研制出来的。这是中国农药工业史的辉煌时刻之一。L先生掰着指头给我历数国内几家主要的农药品种研发机构,全部只做农药研究,不做环保研究,他说农药的环保问题一直不受重视,或者无力顾及。
比如环嗪酮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中国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提出抢建18个农药品种。即在加入WTO之前,将18个重要的、尚在知识产权保护期内的国外农药品种研发生产出来。L先生们便“抢”了其中一个,环嗪酮。这是杜邦公司的产品,在巴西的甘蔗地等地方广泛使用,能杀死灌木,可以用于维护森林防火线、清除铁路旁杂草等,效果很好。
环嗪酮生产中号称“17:1”,即拉进17吨原料,出1吨产品,剩下的16吨全是废料。L先生说,在当年,能拿出这1吨产品,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至于说吃干榨净剩余废料,没人去考虑。排放到环境后,这些物质会以怎样的形式进入植物、动物,最后至人体,更是无从知晓。另如生产1吨阿维菌素,相应排出400吨废水。农药行业废水不仅污染物浓度高、难降解,而且毒性大,很多含剧毒物质,具有致癌、致畸或致突变效应。
2003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要制定专门针对农药行业的废水排放标准,因为1996年的综合污水排放标准已经过时,而且只是对一些常规污染物做了限定,并没有包括农药行业特有的、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质。但是,如今14年过去了,这个标准草案几易其稿,至今还在征求意见阶段。
农药工业蛮荒时代
L先生对于农药化工行业是有深厚情结的。1989年,他大学毕业刚入苏南那家化工厂时,厂里只有四间破旧的办公室,厂长办公室墙上挂着八个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厂里有10个本科生,在全市都算有名了。
90年代早起,厂里普通工人的月收入接近200元,比公务员要高。后来工厂顺利改制,企业上市,L先生由于业务能力强,早早当上高管,成为公司上市的受益者。如果他的从业生涯暂停在他去西北之前,这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人生赢家的故事。类似的财富故事,那时候的江南化工行业里有不少,只是,没有多少人去计算这些财富积累背后的环境代价。
有一家农药上市公司的高管告诉我,1997年公司进口一种杂环类原药,价格200万人民币一吨。只有原药基础完备,才能制造出各种成品农药,大部分国家是不具备农药生产能力的。后来他们公司花了400多万和本省农药研究所合作,研制出来的进口替代产品,成本一下子降到35万一吨,后来又降到十几万一吨,导致外国公司直接放弃该类原药的中国市场,转而从中国买入产品。
当然,农药行业的人也都承认,之所以国内公司造出的原药价格如此之低,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没有计算环境和健康成本。
另外一个现实是,中国的基础化学品的研究还很落后。举个例子,目前国内登记的有35000多个农药产品,每年新增3000多个,但只有50个左右是真正自主创新的农药品种。
也就是说,连农药产品本身的创制能力都还薄弱,相关的环保技术研发更是奢谈。在仿制国外农药的几十年过程中,往往是“只知其然”地照搬已有配方,只要拿出产品就足够了。
L先生回忆自己刚到农药厂上班时,一个土法生产光气的故事。生产光气需要触媒活性炭,那时候每逢厂里大修,更换活性炭,都要搞好大一番阵势。清晨5点多起来,工人们每人领一套劳保用品,先是焊一个直径两三米的大铁锅,锅架在火上,两个工人开始翻炒锅中的活性炭,就像农村红白喜事上炒大锅菜一样。每半小时换一次班,一天下来要用几十个工人轮班。非要炒到活性炭冒了火,再用干铁桶盛装到反应器里,盖好,通一氧化碳,三天,再通氯气,得到光气。炒完活性炭当晚,为了庆祝这一番苦劳,厂里领导还要安排工人吃一顿。这成了多年不变的仪式。
L先生那时才二十多岁,由于大学本科毕业,专业知识过硬,又善管理,年纪轻轻便当上了车间主任。他觉得这没道理,为什么要炒活性炭?老工人说是怕活性炭受潮,要去掉水汽。为什么不直接在炉子里加热呢?L先生请教了一番专家,下决心破掉旧法,直接将活性炭投入炉子,加热,通一氧化碳1小时,一切顺畅,大大缩短了制取光气的进程。
这在当时算得上壮举了。因为光气有剧毒,吸入体内有潜伏期,没人敢在制取光气的步骤上对前人的工艺做丝毫改动。当年,很多农药厂都发生过同一个版本的故事,工人在车间不慎吸入光气,回家后一夜之间便死了。
L先生的农药化工梦
L先生对农药化工行业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热爱。我们聊着天的过程中,他会突然把手机打开,给我看一大串我根本看不懂的中间体名称和分子式,以及他过去一年做的成百上千个实验报告。他还一直在劝学金融的儿子改学化工。
有次去江苏常熟的一家法国独资公司交流,L先生回来感慨万分地说,人家的安全管理,比我们的上档次多了。比如进厂先学习注意事项,当场考试,通过了才能入场,发放个人必需品、安全帽和面具。进入厂区,有绝对明显的道路标识,司机卸货时也必须呆在驾驶室,以防有情况,好随时开走。
最让他感触的,是对方给他看的资料,一些化学原料高温分解后,形成蘑菇云样,厂方专门拍下来,保存研究。“我们国内哪家有?我们只会照抄。”他说到这里激动起来,“我们做的好多中间体,只说高温会爆炸,但实际上连熔点、沸点是多少,根本都不知道。”
L先生还没去农药厂工作时,当地农药厂发生过一起光气事故。光气在缓冲罐里,变成液体,淌了出来,当时没人知道流出来的那水其实是光气。中午温度升高,光气挥发,导致周边居民也中毒了。“当时人的素质不行,连光气8度以下会变液态都不知道。”他提醒我,别忘了那是1982年,跟现在不一样,大多数人都找不到一本书看。
对于国内行业现状,他是有些怒其不争的。同样做二甲基二硫,国内企业做出的产品奇臭无比,而法国公司做出来的是“香”的,价格是国内企业的两倍多。他至今想不通成分到底差在了哪儿,仿制了国外农药几十年,差距还是那么大。
L先生现在每次从西北回家都只是匆匆小住,然后带上一箱换季衣服就回去了。我对他因我的报道而起的职业生涯变故,始终怀有复杂的歉意。他倒反过来劝我不必在意,反正自己已经辞职创业去了。虽然旧案羁绊仍在,但他现在一门心思放在新化工产品的实验中,如果成功,废水量大幅减少,而且成本极低。
这个产品他琢磨很久,也该放手一搏,亲自去开发一项“革命性技术”了。他说,虽然自己上了些岁数,但还能通宵不睡,琢磨产品。有时候躺在床上,任思绪天马行空,想到一个好点子,翻来覆去,能想得衣服湿透,痛快淋漓。
我不知道他这次创业的前景怎么样,但我希望他成功,最好能给这个行业带来变革,不枉我们如此相识一场。
(作者孔令钰为环保公益组织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本文写作得到该中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