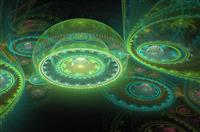
过去一年,在中国的高校中接二连三地爆出了一系列性侵女生和劳役学生的丑闻。让很多人慨叹的是,中国高校对学者的评价制度难道可以完全不考虑师德二字吗?
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的北大,4月8日宣布将在教师管理办法中新增“师德一票否决制”的措施。
尽管逝者已矣,二十年的等待无法不让人觉得这一切改变姗姗来迟,但改变的出现总比包庇、回避和退缩要好得多。可以预计在跟着下来的一段时间,中国高校之中会有更多行为不端的教师被揭露,但在揭露与回应的这些往还之间,人们有理由从悲哀中看到希望: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对于高校师德败坏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反映的是权利意识的一种进步,讲到底是中国人的文明标准在提升,中国社会在进步。
风清气正,总是要在击退污浊之后才能迎来,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师德”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诸如“师德一票否决”这种措施,又是否真的抓对了问题的本质?
在当下的背景之中,提师德,防的主要是师生恋中出现的性侵行为。那么我们不妨先从师生恋这个问题切入。十几年前笔者还是个留学海外的博士生,在学院安排我当助教执教鞭前一天,我的导师很郑重地跟我讲了注意事项。他说,绝对不可以跟还在上我课要被我打分的学生有“感情瓜葛”(英文原话用的字眼是affair),否则必遭清退(sackable)。导师接着跟我解释,师生恋也可能是双方自愿的,且不一定有性侵,但它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原因是权力不对称:因为当我与一个学生处于一种评价与被评价关系时,彼此地位并不平等,当老师的拥有凌驾性权力,在此结构下展开追求,学生的自由将失去保障。结果,就是当老师的滥用(abuse)了权力。我的导师最后补充,如果感情关系是在学生毕业后才开始确立,程序上才算没有问题。
因此,从本质上讲,师生恋的不当并不在于有否违反含义不清的“师德”,而是滥权。道理和医生不能用不尽力救治来威胁病人接受其追求,警察不能用拒绝就抓人来威迫性工作者发生关系类似,这些在文明社会都是常识,也是公众的共识。回到校园问题上,教师对学生指导与评价的权力并非天赋,而是来自教育行业的学术规范,要遵守严格的职业操守。
讲得再具体一点,不同岗位的教师,其指导与评价学生的权力均有相当明确的边界。例如学工老师有权管学生的生活与纪律,但是无权干涉专业课成绩,打分写评语甚至保研面试,都只能留给专业老师来做决定。研究生阶段的导师,实行的是师徒制,但这种权力仅仅适用于学术研究的范畴,在此范围之外的事项导师均无权力对学生提要求。由是观之,要学生叫自己做“亲爸爸”,或者要端茶倒水、买菜做饭、接送小孩,全部都超出了导师的权力范围,均为滥权之举。
从师生恋谈到劳役学生,本质其实都是滥权,相比起近期被揭露得相当多的极端案例,在中国的高校之中,其实更普遍也最应该被揭露的是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工。在欧美的高校之中,即使是拿了全额奖学金,一个研究生应该承担多少教学任务或为导师的科研团队做什么贡献都是有清晰的协议指引的,一般会有可测量的客观指标,例如课时数与实验数等。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不但要师生双方愿意,并且时薪必须高于最低工资。但是在部分中国高校,研究生给导师做项目,有不少人天天熬夜但拿到的劳务连当地最低工资都不如,部分甚至一分也收不到。说句不好听,遇上个缺德的导师,这些研究生的遭遇连讨薪农民工都不如:有冤也不能诉,连劳动部门都管不了。最近两年,有些高校声称为了更好培育人才要把硕士课程从两年延至三年,当中高调地支持的那些大教授们,有多少真心为了培养学术新星,而不是为了让这种滥权的剥削进一步延期,就不好说了。
对于高校中的行为不端的教师的确应该一票否决,但这里的依据不应使用一个定义不清、界定不明的民俗术语“师德”,而是应该明确使用“违反职业操守”和“滥用权力”这种在特定行业都有明确可测量标准的措辞。尤其在代表着知识与良心的高等学府,越是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就越要体现出自己的识见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