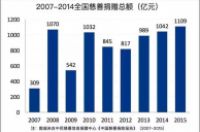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发生了三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以及2019-2020年的新冠肺炎。在政府主导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除了检验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之外,应该还要着重观察社会治理思路与社会整体发展情况之间的关系。
社会多元力量参与政府主导的救灾,是现代公共治理的要求和表现之一。参考过往的情况,以此次全国抗疫为主要观察对象,其折射出的社会治理思路与社会现实环境、条件是否是相匹配的?表象的矛盾与冲突根源何处?新的时期,政府应该给多元发端的社会力量提供怎样的空间?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中,这些问题未必被主流声音充分讨论,但却贯穿抗疫始终。围绕这些问题,《社会创新家》专访了多次参与地震等灾害救援的的资深公益人李劲。
李劲,毕业于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先后任职于国际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等。
▲▲▲
1⇒冲突的根源
《社会创新家》:新冠肺炎疫情已有两三个月,从抗击疫情的角度来总结,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最初参与救援时工作看上去都有些混乱,你的观感是什么?
李劲:我觉得用“混乱”来描述是不准确的。在灾害初期,一定程度的“混乱”不可避免,但不能用以概括描述整个疫情应对工作。我认为此次疫情是个“棱镜”,整个社会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是“冲突”。
《社会创新家》:冲突的两端是什么?
李劲:表象上的冲突有很多,我们简单做下梳理。从政社关系角度来看,最开始显露出来的是官方慈善和公众观感的冲突。官方慈善机构拿了资源,但是没有能力处理资源;公众有很高的热情,民间公益机构和志愿者社群具备相当的物资动员和疏通能力,但是政府通过防控指挥部、当地卫健委以及五家机构主导的工作,没有充分调动民间力量,非常可惜。
当然更应该从全局来看。比如武汉政府班子的水平、能力与民间期望值之间的冲突。中央也对当地班子做出了必要调整。这里不展开。
还有就是官方和民间叙事上的冲突。官方语境整体上与民间话语有错位,而这种错位已经形成了矛盾。比如3月6日武汉市委领导提出要在全市开展“感恩教育”,引起了舆论波动。官方话语也很快做出了调整,新的说法是“感谢武汉市所有居民”。同时,官方媒体的“宣传”和比较独立的市场化媒体如《财新》《三联》《人物》的报道,甚至包括更多的“自媒体”,在舆论中也形成了某种话语冲突。更关注个体苦难的“方方日记”,在民间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力,其本质,也是官方和民间叙事上的冲突。话语背后是体制,是政治文化,是理念和观念。
《社会创新家》:为什么说是“表象”,根源是什么?
李劲:如果把这次疫情作为棱镜,在它折射出的冲突、矛盾背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根源性的问题,也就是当前“统筹”的社会治理思路与整个社会多元发端的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冲突。
多元发端的社会力量在成长,这其中包括社会组织、志愿者、自媒体等等,也必须认识到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同时,虽然中国对境外的信息有所管制,但信息渠道没有彻底断掉,尤其是对中等收入群体来说,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多资讯。进一步开放、增加社会活力,这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大的趋势,全球化、信息化是不可逆的。而“统筹”的治理思路,与多元发端的社会力量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当然也就会出现冲突,尤其在重大公共事件的时候会凸显。
《社会创新家》:谁应该做更多妥协?是治理者还是多元发端的社会力量?
李劲:两面看,我们不能脱离国情。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党领导的,这是个前提,也是个现实,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现实。在这个前提上,需要看到的是,多元力量成长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新挑战同样是不能忽略的。社会的治理不应该固化,但我们现在有固化的倾向和表现。
我的观点是,政府和社会都要实事求是,政府要看清社会力量的多元发端不可回避,社会也要承认中国的实际情况。
多元发端和成长的社会力量,好比武侠小说中虚构的武功——人体任督二脉,身上的“真气”就是活力。如果“真气”没有顺着经脉运转,会变成有害的力量,应该让这些“真气”走到经络中去,成为国家发展力量的一部分,成为建设性的力量。
党和政府更有主动权,可以更主动一点去做调节。
《社会创新家》:你认为包括政府在内,整个社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李劲:我没法回答。你问有没有认识到,I really don’t know。从汇集款物到官办慈善机构,到李文亮的相关事件和调查结论,到官员提出“感恩教育”,到官方媒体和自媒体叙事的错位……我只能说值得观察。
▲▲▲
2⇒应该更全面地观察“社会成本”
《社会创新家》:这次抗击疫情中国模式成为“典范”,不止简体中文互联网上出现流行语“抄作业”,在国际互联网上,要求学习中国模式的声音都很多。在中国模式取得了阶段性效果之后,我们也希望去全面地去评估代价,现在我们对代价认识充分吗?
李劲: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制度环境下,中国“统筹”式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有明显优势的,当然也存在不同的意见。
应对这场疫情,中国模式短期看更有效,但要加入一定的时间维度来考量。长期来看,还需要更全面地考虑社会成本,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分析。
关于集权和分权的效率,是个老问题了。我们姑且笼统地说分权就是民主的一种表现,这种制度,在应对紧急状态时,短期内效率一定是相对比较差的,但一个社会不会永远处于紧急状态中,长远来看,也未必就差。
紧急状态下,谋求高效率,它是以个人自由和个人福祉为代价的,比如武汉居民。我们没法用一句“武汉人民为全国和世界做出了贡献”去带过他们付出的代价。在中国,很多人不认为自由是必要的,不认为别人的自由和福祉跟自己是相关的,对自由的价值认识也不同。比如我们在北京,如何能体会到湖北、武汉六十多天以来的痛苦?但个体的福祉真的不重要吗?
我在读书时,有一次上课让我印象特别深。案例是要建一个水坝,经济学教授说,我可以把所有的社会成本“现金化”,包括经济成本、材料、能耗,也包括搬迁带来的社区的动荡、治安的恶化等等,甚至包括垂钓者的福祉都考虑进去。修水坝之后鱼不来了,垂钓的快乐是钓鱼人的福祉,这些也要算进去,折算成现金。方法对不对可以讨论,但把钓鱼人损失掉的快乐当做成本的一部分,这很重要。
《社会创新家》:我们听到一种观点,当然也有从疫情开始至今的观察,也就是基层政府的权力被过度放大了,执法边界模糊,甚至谁才有执法权这个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小区物业就可以封门,社区就可以上铁链。这是否也是应该被考虑进去的“社会成本”之一?
李劲:小区物业的权力从何而来?区政府、市政府有授权吗?是街道出的什么文件?如果授权的来源清晰,所谓“过度放大”就是不存在的。反之,它可能成为一个惯性,权力的特征就是只会集权不会放权。
以北京为例,事实上政府发布了很清晰的临时措施。无论是澳洲回来那位不按规定自我隔离的女士,还是隔离中要矿泉水喝的留学生,这两件事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片段,但在片段中,我们的执法者都比较少“援引”法律法规。这体现出了我们法治文化的不足。依据什么执法,我得到怎样的授权来约束和规范对象的行为,“援引”其实是法制观念的表现。
现在很多公益组织在考虑湖北、武汉的社区重建问题,包括个体心理的重建,包括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包括个体、家庭与社区、跟物业的关系,这些都需要重建。这些也都是社会成本。
中国传统语境下,我们大一统的国家只有“人民”这样的大概念,没有个体。现代化的特征,我认为就是个体的独立。“人民”这个词可能越来越没有价值,“个人”反倒会越来越有价值。
▲▲▲
《社会创新家》:从社会力量参与抗疫这个角度来看,冲突最开始集中体现在归集款物到官办慈善机构。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民众公益热情的“井喷”至今,重大公共事件已经发生过多次,这次政社合作模式有哪些不同?
李劲:整个疫情应对工作,体现的是官方主导的应对机制对民间公益力量的态度。这与最近几年的社会治理思路是一致的,不意外。但是,有以前这么多次的经验和教训,从2010年玉树地震到2013年雅安地震,再到2014年鲁甸地震,包括2017年湖北水灾,官办慈善和民间慈善之间、政府和社会力量之间,彼此的合作机制应该已经通了,这次又大幅收缩,而且搞出这么多问题,这是我作为行业人士的一个不满。
之所以是不满,而不是不解,因为我了解背后的原因。我只是非常意外,这次居然真的会这样做!
《社会创新家》:据你观察,在此次抗击疫情的政社合作上,相较于此前玉树、雅安地震救助的整体应对机制,此次更为封闭保守了?
李劲:2010年玉树地震,当时也是要求“款物归集”的。在我看来,玉树州行政级别没那么高,所以力度相应也不是很大。虽然当时发出了类似通知,但并没有不由分说地去贯彻执行。当时青海省民政厅很开放,我们到玉树做灾后援助,当地非常欢迎。
到2013年雅安地震时期,政府根本就没有大力地去收缩,反而是往相反的方向做。实际上,今天的“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就是在雅安灾后援助时建立起来的。当时四川省政府已经把这条路蹚出来了。
2014年鲁甸地震期间,云南省政府起初也比较谨慎,但还是给了空间,民间的物资也好,志愿者也好,还是会放进去的。
这次发了“归集款物”的公告,我开始也不是很在意,我认为公告必然会这样发,但执行上会给民间公益机构留有空间,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大的执行力度。官办慈善的瓶颈效应暴露得很明显,加上平台媒体、自媒体、普通网民又接连曝光一些救灾不力的“证据”,加剧了冲突。
▲▲▲
《社会创新家》:有学者提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救助、支援工作需要枢纽平台,用来衔接政府系统和民间公益力量。如果不是半政府机构来充当枢纽,你认为民间公益力量当下有能力自己组建类似的平台吗?
李劲:我认为很难。雅安地震灾后援助时有一个好的成果,也就是“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它是个组织,至今7年了,每年都开会。针对此次疫情,这一平台在2月2日也正式启动响应,成立的社会力量协助网络。至于民间公益力量当下是否能建立起一个枢纽平台,我认为有困难,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长期以来,我们的政策环境不太支持公益行业的联合,现有的联合都很松散。相比于基金会中心网、基金会发展论坛这两个平台,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已经是最业务导向的行业联合平台了。基数太小,难以奢望出现能力足够强的联合体。
第二,现在整个公益行业的“市场化”取向也是重要原因。我说的“市场化”,并不是说用市场方式运营或者用企业方式管理公益机构,而是说公募资格开放以后,募款的市场化导致基金会之间竞争的诉求高于联合的诉求。这次“社会组织疫情应对协作网络”差不多到了疫情应对的第二阶段才形成,也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反应。不过疫情应对是一个长期的事,期待这个网络有所成就。
《社会创新家》:在过去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中,都是以官办组织为主体。但是后来壹基金突出重围,成了参与救灾的新力量。你曾担任壹基金的秘书长,为什么壹基金当时可以突围?这次会有类似的机构出现吗?
李劲:壹基金并不是灾害救援中唯一出色的一家民间机构,也有很出色的其他机构。但壹基金是在历次大灾上锻炼出来的。当然也有其特殊禀赋,比如品牌的、成功企业家的等等。
2008年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中,实际上是政府管不住,因为范围太大,公众的公益热情又很高;而这次疫情以武汉为中心,比较集中,所以武汉红十字会卡在咽喉造成了物资“堰塞”。另外,2008年时政府还没有建立管理民间力量的经验,所以机会比较多。
对于机构来说,能力是综合性的,我们指望一家基金会,甚至指望湖北的官办慈善机构一夜之间具备应急救援的能力,这完全没可能。
▲▲▲
5⇒政府与社会都需要反思
《社会创新家》:这一次公众的公益热情很高,这也让我们想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公众的公益热情被描述为“井喷”。然而,十多年来,公益界、行业媒体做出的一些努力,在大众话语中没有看到相应的积累和留存。你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李劲:问题的根源也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在中国,市场都是从属,社会力量更没有被当作一支独立的、可以和应该影响社会的一种力量。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公众力量聚合的最基本要素已经具备,近些年财富的积累也好,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好,都给民间力量的生长提供了好的土壤,但土壤中的力量是乱的。
《社会创新家》:从媒体的角度观察,公众之所以没能对公益加深了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公共话语空间收缩,一些问题不再有讨论的基础,而教育体系没有提供必要的内容。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人,普遍对公共事务和“第三部门”缺少认知。
李劲:当下中国,个体有很充分的成为公民的条件,比如有独立的收入,有较为多元的知识、信息来源。只要想去获取,信息并不少,但这些信息没能成为系统的知识结构,没有成为思想。加上知识分子的消散、媒体的溃败等等,个体有了形成公民社会的这些要素,但是缺少塑造力。
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完全过去以后,到底我们的国家、政府如何看待多元发端的社会力量,社会力量参与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究竟是建设性的力量还是破坏性的角色,政府需要反思。我们收获了哪些经验,经历了哪些教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些问题,不止政府要反思,整个社会也要反思。END
采访 ▏肖泊
编辑 ▏宋厚亮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