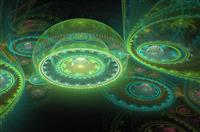
从生殖正义角度看避孕技术史
■武夷山
(发表于2020年10月15日《中国科学报》)
2020年4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女学者Donna J.Drucker(唐娜·J.德鲁克)的Contraception:A Concise History(本文作者译为“避孕简史”)。该书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基本知识丛书”中的一种,丛书旨在对当代一些重要议题进行概述,从而促进“对世界的原理性理解”。德鲁克过去已经出版了两部著作,一是《性之分类:阿尔弗雷德·金西和知识组织》,一是《性研究机器:技术与认同政治学,1945—1985》。
在本书中,德鲁克采用生殖正义的框架进行分析。本书采用的“生殖正义”概念,取自女性问题专家及女权活动家Loretta J.Ross 和历史学家及女权活动家 Ricki Sollinger合著的著作《生殖正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7),其含义是:女性有权利决定要孩子,或是不要孩子,有权利决定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抚养孩子。
本书描述的从古到今五花八门的避孕手段:1882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节育诊所采用的子宫帽;蓄奴时代加勒比海地区用普列薄荷制作的、用以调节月经的草药茶;上世纪70年代古巴“避孕派对”上发放的鱼线制作的宫内节育器;避孕套;杀精子软膏;安全期避孕法;21世纪的加拿大和德国大都市中出现的机器人妓院,等等。
作者德鲁克的意图,是从生殖正义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避孕技术史。于是,产生了一部对避孕技术史进行生动概括的著作,该书将权力关系置于避孕技术之开发、使用和拒用的中心。德鲁克写道,“避孕从来就不是一种中性的技术”,有很多社会政治因素调节着人们的避孕方式。
比如,荷兰女权主义者、医生Aletta Jacobs(阿莱塔·雅各布斯)于1882年率先在阿姆斯特丹开设节育诊所的举动,就深受新马尔萨斯主义运动的影响,该运动主张采用避孕器件来控制人口增长。
德鲁克写道,避孕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该技术使女性获得了免除怀孕的自由,增强了她们的性快感和满足;另一方面,某些政治势力基于其种族主义立场和阶级立场,又可以利用避孕技术来限制某些群体的生殖自由权利。
德鲁克较细致地叙述了雅各布斯的早期贡献,也是为了打破传统的避孕技术史叙事中美国和玛格丽特·桑格(1879—1966,妇女节育运动的先驱之一)等美国人物处于中心支配地位的格局。德鲁克写道,当年,桑格去阿姆斯特丹向雅各布斯求教时,雅各布斯冷淡地让桑格吃了闭门羹,因为她觉得桑格不是医生,没有资格搞节育。
后来,桑格学习荷兰的做法,在美国女性人群中大规模安放和分配子宫帽,搞得风生水起。那时,美国国会1873年通过的“科姆斯托克法”仍然有效(直到1972年,该法的不合理规定才被终止),该法禁止传播避孕信息和物品,连医生都不允许,因为该法将避孕视作淫秽活动。因此,桑格的努力实属不易。
通过这类叙述,读者对影响着避孕手段之利用的复杂的权力关系就心中有数了。另外,女权运动的兴起与某些避孕器件的应用之间并无直接的线性关联。德鲁克说,一方面,现代避孕技术改变了两性关系,另一方面,它也是扎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学环境和医学标准化过程的。
避孕技术史上的分水岭是上世纪60年代口服避孕药的问世。德鲁克对口服避孕药推广史的研究表明,避孕药的推广并不必然地会催生“性解放”(这是一种通行的看法),甚至都不一定与“性解放”过程相重合。事实上,避孕药产生的影响因地而异。比如在美国堪萨斯州的劳伦斯,医院诊所只给已婚妇女提供避孕药,这种做法持续了十几年。后来,当地的女性健康活动家组织了静坐示威,提出未婚女性亦可使用避孕药的强烈吁求后,情况才逐渐改变。
书的最后,德鲁克还展望了避孕的未来:现有避孕方法将进一步改善;将会出现新的避孕药具分发方法;支持人们方便地获得避孕药具的种种努力将持续下去。
《中国科学报》 (2020-10-15 第7版 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