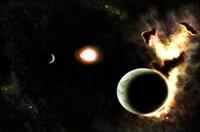一次,和做教师的朋友争执起来。
他说,好教师,当然是学问第一,严谨第二,要在讲台上站得住,在知识传授上毫不含糊,而后,才谈得上爱心、方法和其他。
朋友的话我不完全同意。这个标准,放在几十年前,无可辩驳。那时候,老百姓钦敬知识,仰视先生(教师),尊重读书人……对教师,有无条件的信任。做教师,只要你有学问,或有点学问,就会被认同。但现在世道大不同,“百度”、“谷歌”已经与“先生”分庭抗礼,并且,这些网络先生们的无限可能性,让学生有了“怀疑”的态度,甚至让学生暗暗地瞧不上老师,“他不就只知道那么点儿吗?”总之,教师不再是被无限信任的那个人。在这样的情形下,拥有什么样的品质才能帮为人师者挽回阵地?我以为,广博的知识固然重要,广博的趣味则更关键。
但朋友有雄辩之才,我不跟他争,我花开两朵,另表一枝,怀念起我的小学数学老师。
小时候,我在子午岭脚下一个小林场里念小学。那学校真小真破,沿山下的大路走好久,拐上一条之字形山道,上到一个高台上,才是学校。数学课最乏味,刚开始太简单,不就是掰着手指头算数吗?后来不简单了,要学珠算,要认时钟,要换算千里、公里和里。数学老师课上得本分,整节课要么低头看教科书,要么在黑板上写写算算,要么叫几个孩子上讲台板演,一直绷着个脸,无趣得很。但我们都不打瞌睡不开小差,耐心而神圣地盯住他刻板没有表情的脸……原因也简单,数学老师是个好手艺人,做得一手好木工活。我们下课有棍操,每人一根“金箍棒”,两头红中间白,就是数学老师课余时间一根根做出来的。后来,又有了哑铃操,一手一只,这哑铃,也是数学老师又是刨又是旋,用了传统木工中的榫卯工艺,将手握的短棒跟两头的木球套合在一起做成的。上学我们总要去早一点儿,放学总要回家晚一点儿,就是为了看一块块木头在老师手底下怎么变化的,一地木屑,满屋木香,老师的脚埋在一堆蓬软的刨花里……那时候,学校里十几个老师,包括校长,都比不上我们数学老师可爱。
我那振振有辞的朋友被我的怀想触到柔软处,也慢了语速,缓了语气,讲起他的一个老师来。
他记不得那个老师到底教什么课,只记得每天下午四点以后,老师带他们上山去挖草药。那老师懂的东西真多,柴胡、当归、黄连、厚朴、甘草……还顺带着给他们讲了扁鹊和孙思邈。他们那时还上小学,但已经知道中学生教科书里才提到的故事,扁鹊为齐桓公诊病啊,华佗的刮骨疗伤和五禽之戏啊,哦,还有,是张仲景发明了中医的“坐诊”,从前,中医可都是走街串巷的……
他讲完,意犹未尽,嗟叹有声。我正要借机“四两拨千斤”,他摆摆手,说:“我明白你要说什么,几十年后,我们记得的,不是老师教的知识,而是老师身上与知识无干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将这两位老师身上与学问无关的东西称之为趣味。我们大多数老师都很“专”,所谓术业有专攻,很少跨界。所以,物理老师不懂历史,化学老师辨不清地理中教的飞机从这里飞到那里方向怎么变的问题。我记得念中学时,一天下雨,体育老师守着我们在教室上自习,一同学偶有一题不会,老师竟三言两语点拨到位,全班同学顿时震惊并仰视。而我儿子上学也有类似经历,一天一进家门就兴冲冲地对我讲:“妈妈,我们化学老师对世界历史才通呢,一会儿横向几个国家比,一会儿纵向跨几个朝代比,直接把我们班同学震翻了!”
我觉得,这些没有框囿,不断跨界的老师,就是有趣味的老师。一个人在知识之外的趣味,形成了自己具有无形引力的气场,魅力于是产生。无趣难欢,无味不乐,做教师,何不添点趣味,先做一朵兀自清香、招人倾慕的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