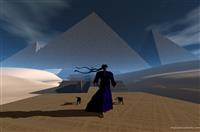
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他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铺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能提高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老舍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老舍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所取得的巨大突破。
一、文化批判视野中的“市民世界”
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执着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他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显示了老舍对这一阶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老舍在观察表现市民社会时,所采取的角度是独特的。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不同,老舍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他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的蜕变。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个视点决定了老舍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不能得到主流派文学阅读时尚的欢迎,但这并不妨碍老舍艺术上的成就:在文化批判视野中所展开的市民生活的图卷是独创性的,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对国民性的探讨也是独特的,在他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中,老舍还格外注重为现代文明探索病源。
老舍用“文化”来分割他的市民世界,其中不同类型的市民形象分割体现着老舍对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批判。他的市民世界中,活跃着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各式人物的性格构成往往都在阐释着某种文化内涵,老舍写“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
老舍写得最好的是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老舍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现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
早在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长篇《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老马,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这样一个角色,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 因为就是为落后的国民勾划灵魂,两者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阿Q 生活在“老中国”的乡村,老马则是华侨,旅居国外。老舍有意把老马放到异国情景中去刻划,试图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中更明显地突现落后国民性的背谬之处。另一部写于1939年的长篇《猫城记》反映了作者当时反主流思想情绪,其政治观点是不适合历史主潮的,然而其作为一部寓言体小说所构设的荒诞世界中那些“猫民”的种种保守、愚昧、非人性的性格,分明也映射着“老中国儿女”落后的国民性。这两部小说艺术上都比较粗糙,而且并非直接写市民生活,但其写作旨意很能代表老舍创作中所显示的“文化批判”的指向。
老舍非常注重将市民生活方式中所体现的人生观及其文化根蒂加以展示。在他塑造的老派市民形象系列中,除了《二马》中的老马,还有《牛天赐传》里的牛老四,《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祁天佑,《离婚》里的张大哥等等。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离婚》中的张大哥。这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陈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变”。小说一开头就用夸张的笔墨介绍:“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对张大哥来说,“离婚”意味着既成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张大哥这一套由婚嫁观念为基点推衍的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离婚》所描写的张大哥的家庭纷争及其危机,可视为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的危机。小说辛辣地揭示了张大哥的“哲学困境”。这位张大哥对待人事的准则是:“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连小说中另一位“马虎”先生都嘲笑张大哥的生活态度就是敷衍,而且是郑重其事的敷衍。作者以现实主义的严峻态度,写出了这种受传统知足认命的人生观支配的旧派小市民的生活态度在“乡土”中国往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过程中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在遭到不幸时张大哥竟至毫无所为,因为他的“硬气只限于狠命的请客,骂一句人他都觉得有负于礼教”。张大哥成了悲剧角色,只会绝望地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老舍以幽默的笔法,真实地写出了张大哥这类市民社会“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地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在他看来只消准备一些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都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不过是平头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地分了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地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向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地领受“训示”;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不同的是,作家在批判祁老太爷这种保守苟安的生活哲学的同时,没忘记时代环境的变化。当祁老人发现了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作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地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祁老人的孙子祁瑞宣大致也属于老派市民系列,不过他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在他身上集中了更加深刻尖锐的矛盾。他受过现代的教育,有爱国心,甚至也不无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又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大家族的长孙,他身上体现着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与困扰。在民族危难的时刻,祁瑞宣虽然终于“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然而小说所着力表现的是他的性格矛盾和无穷的精神苦恼,其中显然也在表现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小说正是通过祁老人、祁瑞宣思想、性格的刻划,深刻地反映了北京市民乃至整个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
老舍和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不同的是,在批判传统文明落后面的同时,对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持非常谨慎甚至排拒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对“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画式描写上。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过那种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了人格的堕落人物。其中既有兰小山、丁约翰之类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老舍一写到此类角色就使用几乎是刻薄的手法,不忘记给他们描画可笑的漫画式肖像。《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这种“德性”:“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园的广告。”总之,这是一种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一类被嘲讽的“洋派青年”,不过更令人恶心的是其“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老舍笔下的这些角色因为嘲讽的意味太浓,刻划却不算深入,有类型化的倾向。老舍所写的老派市民显然带有悲剧意味,而在给新派市民画漫画时,鄙夷不屑之情便溢于言表。就所描写的道德失范、价值混乱而言,老舍的批判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然而这种比较浮浅的嘲讽或批评里头,又包含着对西方文明的反思。老舍作品中的思想内涵是比较复杂的,批判传统文明时的失落感和对“新潮”的愤激之情常常交织在一起,并贯串在他的多数小说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表现底层市民命运的作品里,也贯串着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中篇小说《月牙儿》便表现了这主题的特色。这篇小说写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故事,在两代人生活道路的离散与相聚背后,隐伏着精神上的离散与合一。小说展示了母亲从生活中得来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这一带有原始残酷性的生活经验,与女儿从“新潮”中接受的“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之间的矛盾。耐人寻味的是,在老舍的笔下,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母亲的生活真理向女儿的新思潮靠拢,而是相反;老舍力图向读者指明:正是母亲的生活真理能够通向真正的觉醒。这样,老舍就对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判断。他站在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下层城市贫民的立场上,尖锐地指出:在大多数穷人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爱情就只能是买卖,“自由婚姻”、“爱情神圣”云云,不过是骗人的“空梦”(老舍在《骆驼祥子》里也说过类似的话:“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精神’只生在大富人家”)。老舍对于西方个性解放思潮的质疑与批判,在《月牙儿》所描写的范围内,无疑是深刻的;然而,在老舍全部作品的描写中,这种批判或多或少地表现为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而将封建宗法社会东方文明美化的民粹主义倾向。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潮,在中国这样的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小生产方式与闭锁的生活方式占优势的文明古国,是特别有其土壤的。
与老派的和新派的市民形象系列相比照,老舍的笔下又出现正派的或理想的市民形象。显然,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迁与分裂的图景时,还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况且老舍的创作很注重社会的教化功能,他写理想的市民是为了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发意义。不过,老舍常常带着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性格。老舍早期作品中的理想市民——无论是《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赵景纯,还是《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里的丁二爷,都是侠客兼实干家,这自然是反映了中国传统小市民的理想的。这些小说大都以“理想市民”的侠义行动为善良的平民百姓锄奸,从而获得“大团圆”式的戏剧结局。这不仅显示出老舍的真诚,天真,也暴露了老舍思想的平庸面:中国的现代作家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时时显示出思想的深刻性,而一写到理想,却常常表现出思想的贫弱,这个现象颇发人深省。随着生活的发展,老舍的生活也在深化。特别是抗战时期所写的《四世同堂》里,自觉地从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的力量的挖掘中,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老舍在小说中明确地指出,传统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去了“灰土”,“剩下的是几块真金”,这种“真金”,就是“真正中国文化的真实的力量”,虽然也是“旧的”,但“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在小说中,天佑太太、韵梅这两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平时成天操心老人孩子、油盐酱醋,民族危难一旦降临,她们就挺身而出,坚毅沉着,而又忘我地成为独立支撑的大柱。在战时生活的艰难磨难中,她们看到了四面是墙的院子外面的世界,把自己的无私的关怀与爱由家庭扩展到整个国家与民族。
诗人钱默吟战前“闭门饮酒栽花”,“以苟安懒散为和平”,残酷的战争打破了他生活的平静,儿子的壮烈牺牲与自己的被捕使他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身上爆发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杀身成仁的民族骨气与操守。在老舍看来,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所唤起的这种坚韧不屈、勇于自我牺牲的民族精神是可以成为建设新民族、新国家的精神力量的,这瞩望于未来的眼光,标志着老舍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骆驼祥子》: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探讨
在老舍笔下除了老派、新派与理想市民几种形象系列,还有一种属于城市底层的贫民形象系列,在老舍的市民世界中占着显著的位置。这里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拳师沙子龙、剃头匠孙七、妓女小福子、艺人方宝庆、小文夫妇,等等。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如果说在对旧式市民与新派市民的描写中,喜剧的色彩往往构成主调,那么刻划城市贫民形象的作品就更具有浓重的悲剧性。《骆驼祥子》就是写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在老舍全部创作中是一座高峰。通常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功在于其真实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了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作品描写的生活情状及主要人物的典型性而言,这部作品的确有助于人们认识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黑暗图景。然而如果更进一步探究,会发现这部小说还有更深入的意蕴,那就是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这部作品所写的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
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卖力气能吃饭的事儿几乎全做过了”。他把买一辆自己的车作为生活目标,幻想着有了车就如同在乡间有了地一样,能凭着自己的勤劳换取安稳的生活。经过三年的艰辛,祥子终于买下一辆新车,不料才半年就被匪兵抢去。他虎口逃生,路上捡到三匹骆驼,卖了三十元钱,准备积攒着买第二部车,不久又被孙侦探抢走。车厂老板刘四爷的女儿虎妞喜欢祥子,祥子虽然讨厌她又老又丑,却也防不住性诱惑的陷井,不得不与她结婚,并用她的私房钱买下第三部车。不久虎妞因难产死去,祥子只得买掉车子料理丧事。老舍以极大的同情描写祥子的不幸遭遇,“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祥子“作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善良愿望的毁灭,是有社会原因的,小说所写的“逃匪”、“侦探”等的欺压,都印现出二、三十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背景,使得祥子的悲剧有了社会批判的内涵。但作家同时揭示和批判了祥子自身的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嫌钱,“不得哥儿们”。“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哪怕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这就决定了他的孤独、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一步步走向堕落深渊。小说最后写祥子完全变了个人,他变得懒惰、贪婪、麻木、缺德,他打架,使坏,逛窑子……“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么毁灭个人”,他真正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正是对祥子小生产者个人奋斗的思想、性格悲剧的深刻刻划。老舍在下层城市贫民身上所发现的不敢正视现实、自欺欺人的幻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个人奋斗道路破灭以后的苟且忍让,他认为这是“老中国的儿女”的弱点,是落后的经济文化的产物。这样,《骆驼祥子》中对城市贫民性格弱点的批判,就纳入了老舍小说“批判国民性弱点”这一总主题中。
祥子似乎注定被腐败的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他想向命运搏斗而终于向命运屈服,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为泡影,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性。这种表现是出于对城市文明病如何和人性冲突的问题的思考。老舍说他写《骆驼祥子》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这个“地狱”是那个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沦落的社会,也是因为金钱所腐蚀了的畸形的人伦关系。像虎妞的变态情欲,二强子逼女卖淫的病态行为,以及小福子自杀的悲剧,等等,对祥子来说,都是锁住他的“心狱”。小说写的祥子的一个个不幸遭遇,蕴含着一个不断向自我的和人类的内心探究的旅程结构。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幻想当一个有稳固生活的劳动者,他的人生旅途每经过一站,他都更沉沦堕落一层,也愈来愈接近最黑暗的地狱层。无论是祥子刚来乍到就看到的那个无恶不作的人和车厂,还是在他结婚后搬进去的杂乱肮脏的大杂院,或者他最后走向那如同“无底的深坑”的妓院白房子,小说都是通过祥子内心的感觉来写丑恶的环境如何扭曲人性,写他在环境的驱促下如何层层给自己的灵魂上污漆,从洁身自好到心中的“污浊仿佛永远也洗不掉”,最后破罐子破摔,彻底沉沦。祥子被物欲横流的城市所吞噬,自己也成为那城市丑恶风景的一部分。小说直接解剖构成环境的各式人的心灵,揭示文明失范如何引发“人心所藏的污浊与兽性”。老舍对城市中“欲”(情欲、财产贪欲等)的嫌恶,对城市人伦关系中“丑”的反感,都是出于道德的审视。人们从《骆驼祥子》阴暗龌龊的图景中,能感触到老舍对病态的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伤害的深深的忧虑,在三十年代,像《骆驼祥子》这样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又试图探索现代文明病源的作品是足标一帜的。
三、老舍作品的“京味”与幽默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这画卷所充溢着的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方面。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迥异于有更浓厚的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安,廉和、温厚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划、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老舍作品处处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亦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北京人多礼,《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张大哥儿子从监狱里放出来也要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讨好刘四爷更需送礼;《四世同堂》则直接详尽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习目染跟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这不仅是一种习俗,更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四世同堂》第一章就写到: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就连大字不识一、二的车夫小崔也熏染了这种北京“礼节”: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当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与女斗”的“礼”!这种“北京文化”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市民知识分子,《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就是这样一个衰老的北京文化在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性格。小说写了一个细节,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他十分振奋,但他没有“高呼狂喊”:“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是专当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穆不允许狂喊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祁瑞宣因此而感叹自己缺乏那种新兴民族的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不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去牺牲了性命。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描写,是牵动了他的全部复杂情感的:这里既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赏、陶醉,以及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至若有所失的怅惘,同时也时时为“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衰败而惋叹不已。对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由其现代命运引发的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使老舍作品呈现出比同时代许多主流派创作更复杂的审美特征。老舍作品中的“京味”正是这种主观情愫与对北京市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客观描绘的统一。
老舍性情温厚,其写作姿态也比较平和,常常处于非激情状态,更像是中年的艺术。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深深地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老舍说“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什么叫严肃”,“北平人,不论是看着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都只会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会落真的眼泪”。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总之,是借笑声来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一些。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润滑剂。这样,老舍作品中的幽默就具有了两重性:当过分迎合市民的趣味时,就流入了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说得严重一点,有点类似北京“京油子”的“耍贫嘴”)——这主要表现在老舍的早期作品中,老舍曾为此而深深苦恼,以致一度“故意的停止幽默”;经过反复思索、总结,从《离婚》开始,老舍为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健康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意味,谑而不虐,使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可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使幽默成为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而又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与分寸感。老舍创作逐渐失去了初期的单纯性质,产生了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读其小说往往不仅使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掩卷深思。
老舍的语言艺术也得力于他对北京市民语言及民间文艺的热爱与熟悉。他大量加工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制的美(这也是北京文化的特征),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这也是“京味”的重要表现。老舍称得上“语言大师”,他在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创造与发展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