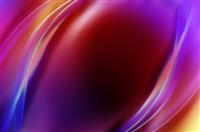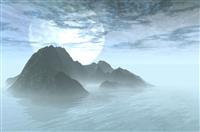对于明代后期不同之士人群落,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应该给予如何之评价,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同一个人、同一群落之看法,不唯千差万别,甚至天玄地远。作为明亡过来人的王夫之,对于明代后起之新思潮,就表现出极端之厌恶。他说:“阳明天泉付法,止依北秀南能一转语作胡芦样,不特充塞仁义,其不知廉耻亦甚矣!”他的意思是说,阳明思想,不过禅家者流,而妄谈仁义。因之他就给了极严厉之批评,说是不知廉耻。他对于李贽及其相近之士人群落,更是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方密之“特其直斥何心隐、李宏甫为刑戮之民,则允为铁案;绝无关系处,以身试灯油而恣其意欲。无知轻躁之徒,翕然从之,其书抵今犹传,乌容不亟诛绝之也!”又说李贽在任云南姚安知府时,“恣其贪暴,凌轹士民,故滇人切齿恨之”。
关于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贪暴之事,并无确凿之证据,只不过由于对李贽思想行为之否定,从而亦信有关李贽贪暴之传闻。王夫之对于万历时任情纵欲之士人群落,同样持否定之态度。他说:“潘之恒以纳赀入太学,用淫媟术事宾尹,施施以兽行相矜,乃至纂撰成编,列稗官中,导天下恶少年以醉骨。而袁中郎、钱受之、钟伯敬辈争推毂之恒,收为名士。廉耻堕,禽风煽,以使神州陆沉而莫之挽。”[这是说,潘之恒、袁宏道他们亦负有神州陆沉之责任。与之相反,也是明亡过来人的钱谦益,则称李贽为姚安太守时“政令清简”,且对其人格备加称赞:“卓老风骨棱棱,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语皆刀剑上事。”他视李贽为异人。他也并不否定袁宏道与潘之恒。他说袁宏道为吴县令时,“县繁难治,能以廉静致理”。[3]他对于潘之恒,也只用了一种中性之叙述:“好结客,能急难。晚而倦游,家益落,侨寓金陵,留连曲中,征歌度曲,纵酒乞食,阳狂落魄以死。”也是明亡过来人的张岱,则把东林党人看作败国亡家之祸害。他用了四十余年完成《石匮书》,有人批评说书中没有拥载东林,不合时宜。他为此有一大段议论:
弟闻斯言,心殊不服,特向知己辨之。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为始终。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载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线索甚清,门户甚迥。作者一味模糊,不为分。……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今乃当东林败国亡家之后,流毒昭然,犹欲使作史者曲笔拗笔,仍欲拥载东林,此其所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所谓不合时宜,就是说,明亡后有一种肯定东林之普遍倾向,而张岱与之异样。但是张岱之看法,亦自有其理由之所在。他是从东林士人群落内部之复杂,从党争之实际效果说的。他亦没有否定东林首事者多为君子。我人知道,称许东林士人群落者多肯定其以程、朱理学反阳明心学。是则张岱并不注重其思想之倾向。
明亡之后,反思明亡之原因,自有种种之看法,有称亡于君,有称亡于党争,有称亡于民乱,有称亡于阉党,有称亡于王门子弟之清谈,有称亡于外族之强项,有称亡于政之腐败、世风之败坏等等,不同之视觉,不同之论断,无虑数十种。上述涉及士人之不同看法,其实多是反思明亡因由之衍生物。
对明代后期不同士人群落之不同评价,自有评价者思想倾向、素养、爱憎之不同,但亦存有对明代后期社会之复杂性应如何看待之问题。
影响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走向的,有政权之运作与生存状况,思潮之发展变化。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风尚之变化等诸多因素。而此种种之因素,又各各呈现为复杂之面貌。对于每种之因素,很难用是与非作简单之划分,往往是非交错,是非并存。此一种之复杂性,正好说明明自嘉、隆以来,思想与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很大之变化,富可敌国与民无立锥之地;歌吹宴饮与饥民流徙;商业的发展与贿赂公行;连绵的水旱灾伤、民变;边境战争不断;皇权的高度集中与政府之瘫痪;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佛、道各种思想并存、纠结;淫乐、争斗、享乐、四面楚歌。整个一副末世景象。士人处于此种环境中,心态之变化自然受其影响。
自生活环境之变化言,我人都知道,明代后期商业有很大之发展。商人以其积聚之大量财富,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有儒商之出现,有可儒可商之人群,儒与商之界线逐渐淡化。商业之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生活趣味与生活追求,影响浸透社会生活之各层面。崇尚享乐,唯利是图正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渗透到社会生活之各个角落。我人常常注意商人之儒商之一面,而忽略商人之另一面。商人之本质是谋利,谋利而取之有道,于经济之繁荣、社会之进步自有其意义所在。但是随着商业发展而来的,不仅有儒商,还有奸商。而且奸商在明代后期社会生活中之影响,其实并不亚于儒商。造假、欺诈之行为,在笔记小说中有大量之记载与描写。而更为重要的是奸商之掺入政治生活,与官场之腐败连在一起。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江西按臣秦大夔奏:
豪商假借部批,夹贩木植,僣称上用,掘官陂,役乡夫,委难轻贷。
没有买通地方官员,此事决难实现。
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奏:“奸商张泽等侵冒军器钱粮,乞行严究,以清库藏,以妨积毒。
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吏科右给事中姚宗文言:
如城守所须盔甲火器、弓矢刀仗等项,查库内及成造衙门见存有几?堪用有几?其不敷者立为创制。如硝黄为火药急需,而奸商内珰相倚为奸,半土半盐,久尽化而为土,宜领价耑官别买,以便制造。
这年的三月,辽左大败,殒将覆军,京城危在旦夕,而奸商置国家危亡于不顾,竟然以土与盐冒充火药!能够经营军输兵器的多是与官府有勾结之巨商。至于常时借着政府南粮北运之机,买通漕运官员,搭载私货;官商勾结,贩卖私盐等等,更是常事。政府之各项工程,商人亦从中渔利。叶向高在《摄工愚见序》中说,留都城垣廨署舟梁器械之维修,一年十馀万也就够了,“顷非时宣索,动至钜万,府藏为竭。而中贵人督金钱者犹项背相望,是上糜也。兼之法久弊兹,人情弛废,物料工作,百不如曩日,报竣未几,圮坏随继,岁岁耗县,官无已时。甚至上供诸物,贾人子辄夤缘为利,旁侵私割,无不尾闾。是下糜也。”上是宫中之索取,下是商人之私割,侵吞的是国家财产。商人可用金钱买官,是公开容许的。而官商勾结之行贿风气进入官场,买官卖官,亦成其时官场习见之现象。云南巡抚傅习,让仆人送了两罐金宝给桂萼,希望内转为京官。其时桂萼正负责铨选,他就收了金宝,不到一个月,就将傅转至南京任职。
张居正那样严厉整顿吏治,行贿者照样络绎而至。《张太岳诗文集》中拒贿之书信就有好几封,其中刘虹川还两次行贿,第一次被张居正退了回去,第二次又来。张居正就写信给他说:“若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货贿,仆不得已必将扬言于廷,以明己之无私,则仆将陷于薄德而公亦永无嚮用之路矣。”我人不是说张居正不受贿,他是疎者拒而亲者收的;而是要说明,从张居正拒贿的这些书信中,可看出当时官场公然行贿之情状。此种之现象,到万历后期更为严重。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二月,云南道御史史学迁言:“楚事方兴,万万金钱遂入都中沈一贯、朱赓、司理监田义、东厂陈矩、通政司沈子木、科臣钱梦皋,当日餽遗之单目可证,过送之姓名可问。此等奸贪隐情,皇上知之乎?”“楚事”,指楚王案。史学迁此疏揭发的是楚王案中自首辅沈一贯至科臣接受楚王贿赂之事。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后,叶向高为首辅时,就惊叹救弊之无法可施,“年来世路淆浊,贿赂公行,责在揆端,真难自逭。”贿赂到了公行之地步,也就无法可施了。不是说官场买官卖官、公然行贿之责任全在商人,而是说唯利是图之观念正以一种无可阻挡之势,冲决道德之堤防,进入社会之各个角落,亦进入官场,进入士人之内心深处。
至于享乐观念之改变着社会风尚,更是不争之事实。此种风尚之形成,与商业之繁荣、与商人之挥霍关系至大。商人之豪奢生活,不仅导引着商业、服务业之发展,亦导引着城市生活之风尚。此一种之生活风尚,亦直接带到士人群落中来。叶向高在《送大司成兼宇林先生之任留都序》中提到商人子弟把享乐、任侠习气带到太学来的情形:
今之太学,赀郎所托径耳。教于何施,急绳之何益?虽然,此为北雍言也。南则异是。南之习汰于北,诸生多贾人子,易与为非。小之而平康狭邪之游,大之而扞网使气之事,衔辔不严,则佚而散矣。
向高作为首辅,对将要到南京任国子监祭酒的刘宇兼重加嘱托,要他对那些商人子弟严加管束。从其时之小说中,亦能看到商人之生活情趣对市民社会影响之广泛而且深刻之生动影相。当然,奢侈生活风尚并非只有商人才有,官场亦广泛存在着。官员之奢侈,连深居宫中的万历皇帝也清清楚楚。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他下了一道圣旨:“近闻在京庶官概住大房,肩舆出入,昼夜会饮,辇毂之下,奢纵无忌如此。厂卫部院一并访缉参究。”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陕西道御史赵文炳上疏,称:“未有小民奢侈而不困窘者,亦未有居官奢侈而能清介者。迩来繁华僭逾,风俗大坏,则去奢崇俭,诚救时急务。但大臣不行,何以表百官;京师不行,何以示天下,则皆宜身先节约以为众庶倡。”我人知道,明代之官员薪俸极低,能够过奢侈生活,除家中原本豪富者外,必靠不明之财产。而此种不明之财产,除非法所得外,必无他途。因之官员之崇尚享乐之风尚,又与官场之腐败连在一起。奢靡享乐,作为观念,作为趣味,作为时尚,在社会之各个角落漫延。叶向高曾用一句极简洁的话加以表述:“淫诡成风,四民如一。”这是社会生活环境,是士人心理趋向之现实基础。
自思想之发展言,明代后期亦处于巨大之变动中。自发展脉络之大体言,明前期是程、朱理学,中间是阳明心学,最后又回归程、朱理学。但这只是大体,其中之交错纠结,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思想之大的变动,应该说是阳明心学之出现。明亡之后,反思者归罪于王学,而不知王学之出现,乃是思想史发展之必然现象。对于程、朱理学之解读与践履走向僵化之时,王学自理学之内部抽绎而出,对儒学统系作一更新,乃是自然之事,此其一。王学之出现,目的是要从内心寻找出路,提升道德境界。敏感之思想家,已经预感到士风世风行将到来之衰败,阳明一再说致良知以改变士风世风就说明此一点。此其二。商业之发展,重个人之观念正在悄悄的到来,王学中重自我之理念与此不无关系。虽然阳明倡人人皆可为圣人,本意在于完善个人道德之修持,但既回归自我,回归本心,则重视自然人性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于是王门后学发展此一题中应有之义至极至时,也就走向任由个性之张扬与欲望之放纵。一种原本在于追求道德修持、重在从内心深处进行道德自我约束之哲学,却不知不觉走向摆脱道德约束、走向自我之放任。而此种与其初衷相背离之走向,其实正反映着社会生活发展之一种新趋向,是一种合乎时宜、应时而出之新的思想潮流。此其三。此三点,可说明王学出现之必然。
王学的出现事实上并没有取代程、朱理学之正统地位。即使在阳明于征战平叛中弦歌讲论创立此一学派的声望极高之时,在王门子弟四处讲学,王学之发展声势浩大之时,亦未曾动摇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之地位。除了徐阶为首辅的很短一段时间王学公然进入朝廷之外,王学一直以在野之姿态存在着,无论它当时在士人中有多么大之影响。我人只要看《明实录》中记载的屡屡反对王学之事实,即可说明此一点。
其实王学建立之初,只是儒学之一支,它实质上并未背离儒学之方向。正如阳明之弟子黄绾所说:阳明之良知说,出于孟子之性善论,致知出于孔子。阳明只是对儒家学说作出新的解释而已。
他甚至要把自己的对儒家学说之理解,说成与朱子并无矛盾,为此而选出《朱子晚年定论》。王学后来发展之所以逸出孔孟思想之范围,乃是思想史发展之自然结果。任何一种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要保持其纯而又纯之性质,几乎是不可能的。思想史足可说明,各个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之现象,此其一。任何经典,后来者作出不同之解读,已为思想史公认之事实。即使解读者声明自己是正统,他亦未必就是正统。此其二。正是此两点,也就可以理解阳明学说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思想之融合。
阳明思想已有禅学之成分,虽然他一再解释他的思想与禅学之根本差别所在。后来甚至到了黄宗羲,也解释此种之差别,大要说是一入世,一出世。到了阳明后学以及王学后来之跟随者,他们谈论王学之某些论题时,是禅佛,是王学,往往已难分辨。
明代后期,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禅佛与道家道教各种思想并存之局面已然形成。此种思想多元并存之局面,已没有任何力量所能改变。虽然朝廷可以禁讲学,毁书院,但是讲学与书院照样存在下去。虽然朝廷可以杀离经叛道者如李贽、何心隐,可以杀僧达观,但是李贽之著作照样热销,禅佛照样成为士人之普遍信仰。
政权之力量已经无法改变此种思想多元之局面。这就是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走向之思想环境。
社会生活环境、生活风尚之巨大变化,思想之多元化,士人之心态走向亦呈现为多元并存之格局。
我人看到,商业之发展为士人提供更为宽阔之生活出路,一部分士人或儒或商,自由进出。他们一部分人以己之所长、以一种特殊之方式进入商业领域。他们卖诗卖文卖书卖画,甚至进入古董买卖市场,他们自我边缘化于政治之外。
随着社会生活风尚与新思潮之出现,一部分士人走向自我。重自我之思想之出现,乃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值得重视之一新亮点。如王阳明、李贽辈之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独立思考,破除思想之禁锢,从而走向思想之多元。此种现象,虽时日不长,但在我国之思想传统里意义重大。此种思想之进一步张扬发挥,与世俗社会追求奢侈享乐风尚相结合,此一士人群落便亦走向放纵,任情纵欲,追求人生之舒适快意,追求情欲与物欲之满足。但是,此一部分之士人,并不像我人所想象的那样,是重情思潮之产物;也并非我人所想象的那样,为晚明思潮之主流。他们之内心,远比我人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情与欲交错。他们有的亦纯情,有的却是发泄欲望而已。自发泄欲望言,他们回归没有道德约束之自然本性。
明代后期的这一部分士人,是入俗最深的一群。在反假道学上,他们展示了人性之真、之美;在纵欲上,他们又流露出人之自然本性中兽之一面。他们追求快意,而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存在着忧虑。他们迷惘,在纵欲之时或之后,常有一种无所归依之感。于是他们皈依仙、佛,以求得心灵之着落处。屠隆、冯梦祯、王稚登、袁小修辈都如此。情与欲,既联系而又有别。我人考察明代后期社会重情、欲现象时,常发现有纯为赤裸裸欲望只发泄者,亦有纯情者,亦有情欲一体者;或人各不同,或同一人而处不同时地、面对不同对象时表现情、欲之不同状态。学者从汤显祖《牡丹亭》看到真情之圣洁,为情可生可死;从冯梦龙情教说看到情之教化力量。然我人亦无须回避,明代后期确有一种纯为纵欲之行为。我人往往亦误认此种纵欲之行为为情之觉醒。此一类纵欲,上自达官、豪富,下至市井无赖,所在多有。而对于士人之此类行为,却往往难以定位。如袁小修少年时代之纵欲,我人将他此一类之行为,与他所描写的王回之纵欲行为相比,要从其中找出区别来,就实在不容易。屠隆之纵欲,王稚登之纵欲,亦有类似之情形。
情与欲,一直是一个不易弄清的问题。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朱熹说:“七情是气之发。”气是形而下的,是天生的。七情是气的表现,七情便是与生俱来的。他又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理、知是性,恻隐是仁的表现,羞恶是义的表现,辞让是礼的表现,是非是知的表现,四端皆是性之表现。是则此四端又具有道德判断之性质。情有无道德内涵,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孟子说性其情,是则当情未为性所约束之前,它是没有道德内涵的。王阳明说:“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它是人心合有的。当七情有着时,就是欲。欲,才是良知之蔽,才须去蔽而复良知之本体。欲,是贪,是过分。阳明主张情应中和,不可过分,过分就应该反对。问题是:何谓过分?若情具道德内涵言,则情自当有高尚、庸俗、卑下之别。若情为自然人性所本有,本身并无道德之内涵,作为社会人,自当受社会道德之约束。然则以何种之道德、何种之尺度方具公正、公平、公信力,一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明代后期重自我、重情,以至纵欲之思潮与风尚,从反对假道学的层面说,它是进步的。假道学把人变成假人,反对假道学就是要把假人还原为真人。培养假人,乃是一个民族败亡之最大祸害。我人或者可以把重自我、重情称之为自我的发现、人的发现。一个假人充斥的社会,终将走向反面。走向反面就是走向另一极端:极度的放纵。极度的放纵又会把人变成非人,带着更多的动物性,泯灭人与动物之界线。最后又必然要回归假道学。
明代后期之此一士人群落,当其反对假道学、回归真我之时,未能找到人之自然本性与人之社会性之合理结合点,未能做到既保持真我,又有合理之道德约束;既能得到人生之舒适快意,又要承担社会责任。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亦如同晋人风流一样,稍纵即逝。我人似可把此一种之历史现象,看作自我发现成功与失败并存之纪录。晋人有过此种纪录,明代后期又一个此种纪录。是为历史之吊诡!
明代后期士人心态之另一重要趋向,是一种拯世情怀。这些士人之行为各各不同,思想之倾向亦异。但他们有一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具有士以天下为己任之传统心态。在思想多元化之明代后期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仍然秉承着士传统之此一核心理念。在这些地方,我人可以感受到传统之巨大力量。此一文化传统之基因,在不同之历史时期,都有它的有力的承传者。王阳明之倡致良知以改变士风世风,是此种情怀。杨爵、杨继盛、沈鍊、杨涟谏诤以死,是此种情怀。高拱、张居正之改革朝政,是此种情怀。东林士人之抗争,是此种情怀。此一种之拯世情怀,又都伴随着传统自身之弱点,伴随着士人自身之弱点,结果他们之行为都以悲剧而告终。
自传统之弱点言,士以天下为己任往往与忠君观念连在一起,从杨爵们到东林党人杨涟们,在临死前还从内心深处表示着对于皇上之无限忠诚。不管皇上是如何之荒唐,不管皇上是如何之昏庸,永远是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此一种观念之突破,要到黄宗羲出来才做到。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提出了对于君之认识,亦批评了臣之此种愚忠。他说:“后之为人君者则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黄宗羲显然是在反思明代后期皇帝误国之后,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设若杨爵们与杨涟们当年认识到此一点,则当是另一番景象。当然,士之执著于传统理念中以天下为己任之核心价值,于家国危亡之秋,亦往往表现为慷慨赴难,坚守气节。对此一传统基因之是是非非加以论断,亦非简单言语所能说清。此又一是非并存之事相。
此一部分具拯世情怀而他们之拯世理想以悲剧告终之士人,自身之思想性格与处事能力都有可议处。高拱、张居正之失败,与他们之权力欲,与他们张扬跋扈之性格有关。而东林士人之失败,则更具普遍之意义。他们长于讲论,长于道德之护持,而弱于政治运作之实际能力。他们是文人,以文章而入仕。政治非他们之所长。他们其实无法适应复杂变化之政局,更无能力驾驭此种复杂变化之政局。他们往往表现出书生气。不唯如此,有时甚且失之迂腐,于事无所助益。
考察明代后期士人之心态走向,我人可以看到在一个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思想多元化的社会里,士人之人生选择、价值观念亦多元化了。文徵明、唐寅、王稚登、潘之恒们之自我边缘化于政治之外;王阳明及其弟子们之醉心于讲学;东林党人之介入政争;当然还有士之道德沦丧者,从反张居正改革之李植辈,到为魏忠贤建生祠、既奸诈凶险又阿谀谄媚之一大批士人。思想多元化与士之分化,为明代后期之一大景观。
考察明代后期士人之心态走向,我人也看到,士之道德理想与现实政治常存在一种错位之现象。他们改变政治败象之良好愿望往往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此一点,除了他们缺乏参预政治之实际能力之外,政权之实际状况亦一原因,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原因。面对一位贪于钱财,不顾生民死活、疑心甚重、借助厂卫牢牢掌握着权力,而又不理政事,亦不让臣下有理政事机会的万历皇帝,任是有着怎么样良好愿望的士人,必亦一筹莫展。士在政权运作中之实际能力与影响,毕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