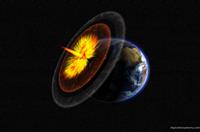长期以来我对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文化人怀着莫名的恐惧。虽然文字的事我也乐意做一些,但总想找个文字之外的职业,以便逃避这种恐惧。这种恐惧的主要根据就是我对于中国文化人的极度憎恶。在我和朋友们的交谈中,用为指代最丑恶最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国文化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最丑恶的东西总是在文化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现,而我们所做的文字之事又多少与文化人有点干系,作为自我批判精神强一点的人,自然要把最无情的批判指向自己及与自己相近一点的人。这种恐惧和批判中暗含着我对另一种人格形象的追求。需加说明的是,我这"中国文化人",并不是指所有的"中国的文化人",而是指全面地继承了中国旧文化,而没有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种文化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籍华人)。至于那些虽是中国的文化人,却较多地抛弃了中国旧文化的价值观,接受了西方现代意识并敢于坚持自我的人,则多多少少总会受到我的尊敬。当然,这种人在中国极少极少。
遥远的古人姑且不论,先说说虽已作古却并不遥远的郭沫若先生。他是有着较多文化成果的人。这成果是其追求真理的足迹,是其生命激情和生命意义的证明。稍有尊严和独立人格的人都会尽力捍卫这成果。可在文革阴风还没吹进他的院门时,他却来个先下手为强,主动宣称自己的作品全是毒草,你们可以全部烧掉。在那种非常时期说出那种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可是西方的一个着名故事却是另一种结局和意义。在宗教裁判所的铁窗里,布鲁诺对于自己的眼前亏看得十分清楚,可他却不想放弃自己的真理去做一个所谓好汉。
火舌终于舔上他的身体,他却骄傲地向那些罪恶者最后一次重申那个真理:"当你们烧死了我时,地球照样在旋转。"这实在是科学的胜利和宣言。在科学胜利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光辉人格的胜利。将这两个故事中的主角对比一下,究竟谁洒脱谁卑鄙,谁智慧谁丑陋,谁好汉谁痞子,谁维护了自己谁丧失了自己?
也许有人说这个对比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郭沫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鄙弃。其实无论拿哪一个中国的文化人跟布鲁诺相比,或跟别的什么西方人相比,何尝不可得出类似的结论呢。
艾青和丁玲是饱经患难备受尊敬的人。可当中国文坛刚刚输进一点新的艺术方法时,他们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当他们无力将其剿灭时,竟然玩起了政治手腕,企图借当权者来惩恶除邪,一旦精神污染扫除净尽,他们便可欣欣然地照当名作家,照当权威泰斗。这也不是艾青的发明,而是中国文化人的老传统,不过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为了自己能做最受宠的走狗,不惜张开狼一样的獠牙,将别的狗们一概咬死,40年来这样的丑剧哪一天停演过?又有几个中国文化人不是在争媚夺宠的倾轧中被咬死或咬伤的呢!
艾青的故事使我想起了一个巴黎的故事。当印象派画家们新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实践得不到官方认可和民众理解时,似乎并没有同行来乘机起哄或威压,倒是有不少文化人首先予以支持和尊敬。着名的左拉特地写出长篇评论,举荐印象派首领马奈的作品,另一些作家如阿斯特吕克、丢朗提等人,也像左拉一样经常参加画家们的讨论活动。他们一面相信自己是天才,一面十分尊敬别人的天才。倘若觉到自己并非天才,便忠诚地做天才们的泥土,共同培植人类精神的大树,而不是做那千方百计蒙住天才灵光的无赖似的"灰尘"(鲁迅语)。艾青在巴黎留学几年,而且是为学习美术而去的,难道竟然连这则左拉与马奈的故事都没听说过吗?
听过了又能怎么样呵,这些可怜的中国文化人!西方世界那么多崇高的人和事,哪样不为中国人所知呢。在课堂上滔滔不绝讲着它们的,把它们译成汉字编成书的,将它们一本一本买回家来的,以及拿了人民的钱远涉重洋去将它们写成博士论文的,不都是我们的中国文化人么?这一切又能怎么样呢?
再讲一个巴金与契诃夫的故事。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切丑恶都在巴金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但愿我的文字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对这位老人再剌伤一点点。当许多人都用恶意攻击和诬陷(也就是"咬")以置胡风于死地时,巴金的文章是那么温和,完全是为了敷衍过关。在人人都要表态的威压下,写点这样的文字算不上什么罪过,事后也很少有人引为自愧。可是在俄国,当沙皇因了高尔基的进步倾向而不批准他进入国家科学院时,契诃夫等人愤然宣布退出科学院,以示对政府的抗议。高尔基进不了科学院,只是少享受一项荣誉,契诃夫们却如此怒不可遏。胡风的被打倒,乃是关于一种文学理论和个人的(其实何止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大事,中国文化人们却如此随和,连最正直最纯洁的巴金也听任他人指使,去干落井下石的勾当,这种对比是何等鲜明。顺便说明一句,在俄罗斯和欧洲,契诃夫远不是猛鸷的英雄。可就是他这种较平和的人,也总是手握长剑,时刻守护在自由女神之前,一旦有罪恶前来进犯,他就不顾一切地挥剑而上,显出斗士的雄姿。
中国文化人呵,你已经完全没有了正义感,完全没有了自我意识么?连你的最优秀分子,也已经找不出一丝光辉来了么?
最最可悲的例子也许是那名噪一时,为整整30年的中国文坛提供了完美无缺的散文模式(至今仍占统治地位)的杨朔。这个人把中国文化人的丑陋和中国文体的丑陋都发展到了极致。那样地不敢正视现实,在尸骨遍野的一片死气中,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胜过天堂的蓬莱仙岛。文风上是那样矫揉造作,那样地充满八股气,那样地干燥,那样地无病呻吟,牵强附会,拿腔拿调,那样地千篇一律。每一个文字都充满了叭儿狗的媚笑和媚笑后的沾沾自喜。这几年来,每一次不得不在中学讲坛上大讲杨朔们的散文时,我就像进了地狱一样充满恐惧和绝望。这样罪恶的文字仍在流行,仍在腐蚀下一代的心灵,这是怎样难以容忍的罪恶,可是我不但容忍它,还帮助他们完成这样的罪恶,目的不过是求一口饭吃,我实在不能原谅自己的卑鄙和下流。至今想来还如此恶心,真想到卫生间去吐个三天三夜,真想到不沾中国空气的外国温泉去认真清洗自己。逃避那种卑鄙和下流的勾当,正是我现在弃职流浪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说,杨朔是个很有诗人气质的人,是个十分真诚的人。我完全相信这种说法。但正是这种说法的成立,使得他的悲剧更加深刻。如果纯粹是为了谋求私利,睁着眼儿求宠,我们呸他一口即可了事。偏偏他不是这样。他是不自觉地充当奴才的,他觉得为主子唱赞歌是一个文化人无需怀疑无需论证的使命。既然是以唱赞歌为先人之见,他当然就不需要自己的眼光,不需要面对真实,不需要为苦难和尸骨和罪恶和丑陋动一丝一毫感情,而只需要去看蓬莱仙境,只需要去看海蜃楼,只需要动用化腐朽为神奇的中国文化人的老伎俩,编出一篇篇粉饰现实的文字。即使是那些无法点化的纯自然景物,比如"香山红叶","童子面茶花",出于那种需要,也不得不勉为其难,强令他们像自己一样承担起歌功颂德的使命。连如此真诚的人都完全陶醉在罪恶之中自丑不觉,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正直和良知可言。
中国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恶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奴道主义。当西方畅行所谓神道主义时,他们的人性只是被神威所压,一旦解放出来即有光辉闪烁。而奴道主义则是一种内在的变质。人性的一切内容都已彻底腐烂。奴隶精神成了灵魂中唯一的内容。即使外部压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义的阴魂依然不散。何况那奴隶主的空缺,及时可以递补。因为我们是全民皆奴。广大的奴隶队伍乃是产生奴隶主的最好资源。每个奴隶都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当之无愧的奴隶主,正如每个农民都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忠于职守的皇帝一样。像杨朔的所作所为,不应解释为迫于外部压力,实是出于奴才的本性。这种人一旦晋升为奴隶主,他所制造的悲剧和罪恶,决不会逊色于我们已经认清了面目的那些奴隶主们。中国大地只有丑陋的奴格像死狗的腐尸一样遍野横陈,而绝对没有人格可言。
所有奴格的典型代表,无疑就是中国文化人。让自己去做这样的典型,岂能不感到恐惧。如果我一生的努力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郭沫若杨朔们的尾巴后边,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
现在我终于知道,做一个文化人乃是我不可逃脱的命运,也是我别无选择的选择结果。选择的同时我抱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坚持自我。我可以没有恩宠没有地位,可以没有名气没有桂冠,但我决不可以没有自我,决不可以没有独立的人格。
我一定要把自己与中国文化人区别开来,与一切中国奴格区别开来。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念,倘若人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时,便是这番寓意。同时我知道,我的灵魂早被奴隶的气息所浸透,要完全摒弃奴性哪是一个中国人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只有怀着战战兢兢的虔敬之心,按着自己的要求尽力去做。
最后再谈几句巴金先生。在十年文革以后,谁曾站起来承担过一丝责任?中国文化人固然没有,他们重新出山以后,除了哭诉奴才的委屈外,根本不懂得反省。那些非文化人呢?那些直接的责任者呢?又有谁反省过?我不是不懂得文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没法一点一点地追究个人责任,可是,如果谁都以此为自己开脱,那么,社会运动中人的主体性又作何解释呢?而且,那些应该由组织由民族所承担的集体责任,又有过真正的自审没有?倒是那个正直善良的巴金,在作着那样痛心疾首的反思和自审。他对于自己灵魂的苛刻,他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真诚,他对于人的尊严的虔敬的竭望和追求,使他高居于一切文化人和非文化人之上,成了鲁迅以后中国仅有的一颗良心。这个民族在经历了如此丑恶悲惨的历史以后,竟然毫不愿意拿出一丝勇气来作一份集体反思,却让这么一位颤颤巍巍的龙锺老人,独自背负着如此深重的忏悔,我常常因此而感到极度的窒息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