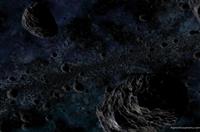
[摘要]重大的学术变革,多半是由“大问题”引出“大思考”。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明清江南研究“中兴”发展到今天,年年丰收之余,总感到缺少了天老地荒、披荆斩棘的刺激。当“反欧洲中心主义”破坏了原有的思考逻辑起点之后,钱穆当年说的民族发展“生力”与“病因”,就成为了求解明清江南发展与不发展的重大疑难。我们或许需要暂时地先把许多诱人却消化不良的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搁置一旁,不计较研究的结果,更看重研究的过程,让真切的实证求是取代名不符实的宏论。例如,明清江南“城市化”概念以及所谓比率的计算,因为勉强附和“现代化理论”,反而有整容与变性之嫌,妨害我们直面当时历史的真实。通贯地考察古代与近代江南变迁的有机联系,发掘与充分运用同一空间、变迁连续的江南近代史料,作为对勘辨析的重要参证,很可能会有利于突破旧思路,增强历史复杂性的认识,并修正原有的判断。总之,以关怀中国发展为指归,明清江南研究如何上下联动、“通古今之变”,理应成为未来方法论变革的重中之重。
在传统中国,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就像今天的“长三角”,地域的伸缩,随论者而定),发展到明清时期,呈现出少见的区域性“富态”,别具一种历史风味。因此之故,上世纪以来,明清江南俨若区域性研究的一座富矿,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发掘开采,到了世纪之交,赫然成为争锋于国际学界的一个话题。表面看,争论是由输入“大观念”而触发的,原先是围绕有否“资本主义萌芽”的疑点展开,待到“反西方中心论”的加入,阵势愈趋复杂化,无论是观察的角度,还是整体的评价,歧异似乎不是在缩小,反而渐趋扩张,至有弥合之难。大开之后怎样大合,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期待着冲出瓶颈,开出新境界。
如今的学术氛围,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甚多,然学问中人若不迷失其本性,多有不甘依傍、异中求变的精神。新的征兆或转机,忽隐忽显,“蠢蠢欲动”,似乎到了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谓的“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2]。众所周知,明清江南的研究思路,是在5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史潮发育下逐渐定型的,不管是欲用江南的史实肯定之,或以江南的事例反证资本主义在中国之不可能,异曲而同工。弗兰克、彭慕兰吸收了中国学者长时期积累下来的丰硕成果,为己所用,动而反之,将我们原来的思绪淆乱打翻,大声棒喝:用西欧英格兰作为评判明清江南的标准,本来就是一种前提性的错误[3]。冷静之后想来:弗兰克对江南思考路向的“反动”,不很有点像当年疑古派“伪书说”,于不疑处有疑,大胆放言:“‘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4]”?!或许经此重大刺激,真能唤醒我们中的一些人,起而另辟蹊径,开出一条建设的新路来?这时,我对李伯重从其最熟练的实证研究中走出,提出“早期工业革命”等等宏大话题[5],忽有所悟——他是对转变风气最早敏感、富有悟性的一位学者。
弗兰克对江南研究的冲击,并不在给出多么值得信赖的结论。应该感谢的是,他送给我们前所未知的英格兰历史另一面。但是,滔滔宏论,却人为地将江南断成两截,虎头蛇尾,把19世纪“分流”后的江南简单遗弃在一边,说明内心无意久留江南,更不打算越俎代庖。比之于结论,他们真正有意义的贡献,就是帮助我们“破坏”那种有可能压迫窒息创造生机的程式化思维,往沉闷的江南老屋上凿破一个缺口,放生活泼,重新尝试各种试错的实验。正像梁任公先生所说:所谓的“反动”,原是为了求建设的新思路而先专事破坏,是时建设未遑,条理不齐,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之中,弃取未定,恒驳而不纯。这种时候,陈述与证据之间露出若干龃龉破绽,毫不足怪。生活在旧氛围里的人,最容易计较或挑剔新论的粗糙,殊不知陈陈因袭、拾漏补苴,更看不到新生的曙光。
出生江南水乡的因缘,使我有幸见证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江南学术中兴”。经过了数代人的努力,明清江南研究的耕作总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新人辈出,也算对得住历史上“富饶江南”的名声。享受愉悦之余,有时不免也感到像是着了黄宗智“过密化”的魔咒,盘点连年高额丰收之后,总感到缺乏天老地荒、披荆斩棘的刺激。
任何一次重大的学术变革,都是由“大问题”引出“大思路”,而其表述或由若干新名词、新概念的创制,耸人耳目,方引起世人注目。当此之时,若心火稍为躁动,不用心参透另类深意,徒袭其形而暗伤其神,会变成又一场话语转换的游戏。明清江南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始终是与中国发展的前途与希望何在这样一个“大关怀”联系着的。且舍远而就近地观察,弗兰克等人的中文版序,明白展示了对中国当下发展金秋丰收充满着乐观的期待,希望能用以打破西方发展模式的霸权。持疑虑的中国学者,承受着亲历的诸多发展难题压迫,喜忧交加,不敢轻易放弃对自我历史的批判,心情要比弗兰克复杂得多。形似对立的两方面,“问题意识”应该说都是深切和真诚的。
是否-否是的轮番敲打,一再提醒中国发展之路自有独立脉络,须细心品味,才不致失其真意。一如钱穆先生所体验的,西史常因惊心动魄的事件划出清晰界线,如全本莎翁之剧;而国史亦间有纷乱牺牲,却无有此类冲动,反似唐诗宋词,常以舒缓的节奏,悄然中随景易情。[6] 纵看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内处其中,还是冷眼旁观,四千年以来,仍然迷雾重重——说发展,她无时不处在变动不居的流转状态,周秦一变,汉唐一变,唐宋一变,明清未尝不在变迁之中,近代更是急促地试验着各种不同的变革方案,死去也能活来。说不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当她变为“世界的中国”之时,却无力躲避踌躇于发达国家之后的严酷,千年的文明古国,历史的惯性不能嘎然即止,乍明乍暗,忽滞忽速,行走的轨迹常出意外,文王的神奇八卦也失了灵气。是不是我们已经到了峰回路转的境界——在我看,钱穆当年说的民族发展“生力”与“病因”两难,仍然是一个需要从现实到历史反复求解的多元方程。
这样重重叠叠的历史纽结与现实难题,实际也在严峻拷问江南研究,你感受到了什么,你已经做得怎样?可惜的是,我们比较习惯于辛勤地爬格子,过份的书斋化,不往“大关怀”上用心思考,感觉反不如弗兰克那样敏锐。长此以往,即使社会对江南研究变革的呼唤再强烈,也仍然难以叩开“新思路”的大门。
我真的不知道未来的突破将从哪里开始,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心中只有期待。假若还是回到“不满足”的话题上,却有许多的感触可以交流。在纷乱的思绪里,一次一次地责难自己,也苛求别人,浮现过大胆甚或有些粗暴的假想:我们是不是需要暂时地先把许多诱人却消化不良的社会科学概念搁置一旁,不计较研究的结果,更看重研究的过程,回到历史实况叙述上来,让真切的实证求是,取代名不符实的宏论?因为这种历史诠释的习惯,已经延续百年有余,时时妨害我们直面生活事实。“理论”牵着史料的鼻子,历史的真容不是变得更清晰,反而越来越像不断整容甚或变性后陌生的“她”。
就拿最近几年的事例来说,“城市化”的概念突然流行于明清江南市镇研究领域,计算城市化比率的各种数据,五花八门,不断被推出。尽管研究者心里也明白,都是“毛估估”,因为连续准确的数据,根本无从获取。为什么一定要如此执著于欧美的话语,附和“现代化理论”,不能平实地用心考订事实,回归中国的原初情景?
我觉得,生活比理论要更真实。回到常识,未尝不是一种摆脱“理论魔魃”的妙策。以我切身经历来衡量,这种“先锋派”的理论陈述,与实地感受是何等地隔膜。走遍江南的大小市镇,听到当地居民不约而同地发出疑问:城里人真是闲得发慌,小镇有什么看头,老远跑来,冤不冤?如同所有的城里人都把市镇来的指为“乡下人”;即使是市镇“乡下人”,面对城里来的,也有外人觉察不出的那种矜持,有强烈的疏离感,遗风至今犹存。此足见“城市化”概念完全来之于书本,活在真实情景里的人根本不领情;对旅游扰乱了往日静谧的小镇生活,心底却十分反感。再回头考察明清(—1840年)市镇实际生活史,固然它们与城市有某种物流的中转关系,但绝非是城市主动扩张的结果,相反却是由乡村经济生活的扩展,自然应运而生的中心地;远离城市,即使是穷乡僻壤,山间边道,也会滋生出类似集镇或乡市[7]。市镇紧紧依赖着周围的乡村而生存,盛衰相连,休戚与共,比政治与消费性的府县城更有自在的根底,乡音也纯淳得多,几不杂“官话”。浏览各代方志,府县志往往缺乏对乡市集镇的严格界限,除少数较大集镇外,市与镇的称法比较随意,相当数量的“镇”实与乡市相差无几[8]。雍正朝起,江南一镇之地,为二至三县所共管,上(塘)属某县集镇,下(塘)却划归某县农村,更是把这种景象凸显得十分清晰。这些都能说明是时江南市镇,仍然植根于农村,乡村包围市镇,两者的界线多数是模糊的,例外的事例有,但极少。
“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化(都市化?)是什么?西方的定义多有岐异,而且飘忽捉摸不定。回到中国,在工商贸易特大发展与消费人群密集的城市,例如江南的上海,最近的十多年,在生活视野中,才真切感受到了它的真实存在。我们一天天眼睁睁地看着,它如何吞噬乡村耕地,把乡村生活的自然空间变成城市的一个个行政区,一片片工厂群,更多高楼别墅林立的“新社区”,那里商业一时未见有同步的繁荣,日常仍得依赖邻近小镇供应,残存的村落成了“城市”中可怜的孤岛,零落破碎,朝不虑夕。苏州、杭州、宁波也在稍逊一筹地推进,至于某些县级市更多虚荣作怪,东施效颦,叫人哭笑不得。这样的“城市化”,且不去评论是非得失,即便是开埠后的上海,也未曾有过这样疯狂扩张的势头,遑论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有什么理由非把这种完全不同时段、不同驱动力、不同功能下产生的“市镇”,与“城市化”的外来语生硬联结在一起,似乎前者是后者的“始作俑者”,用这个来哄抬今日真真假假“城市化”扩张的正当性呢?江南原有的历史经历,能不能对城乡联动而非城乡一体提供一些比半生不熟社会学家更智慧的知识启迪呢?种种疑惑,论者大多置之事外,不愿深究,使“现代”工程师们的“城市化”创作越发无知无畏。
我们已经学会了把史料叫做“记忆”,叙述史学改换成“记忆史学”品牌,但不得不承认,随着亲历群体的消逝,愈远的文字记忆,越是零星与破碎。史料像一地鸡毛,散落在历史的大道上,一路检拾,缀合是何等地不易!明清江南的史料不可谓不富,谁都不敢自诩搜罗穷尽,一览无遗。然全盘衡量,明清江南的史料,一方面是极度丰富,开发远未穷尽,但单调重复使用却相当严重;另一方面又极度匮乏,有关下层民众的生活与感受,有价值的史料少得可怜,而乡风民俗的田园调查与利用,比之华南、华北同行,风气又较为淡薄,精确连续的统计数据更是付之阙如。在此种情景下,恕我直言,若要描述士人以上的生活境况与切身感受,尚有可能,而要实现向下俯视基层与民众的社会状态,甚至进而抬举到研究社会变迁的高度,冒险试验“计量史学”,就不能不显出心高而气促的窘境。另一重困难易被忽略,便是明清江南的文人习气极重,描述景象,偏好华丽词藻,一似山水泼墨潇洒任情;陈述感慨,不少溢美与危言,不离见识的局促。读多了江南明清文人作品乃至府县方志,恐怕所有人的感觉都是沉重的。离开文人的笔墨,我们几乎很难追寻历史的记忆。由他们书写的历史记忆,不知有多少偏差失真,史家若无可靠的依仗,极易坠入其中而不自觉。因为某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已经牢牢支配了我们研究的取向,对有些疑惑难信的史料,论说的需要放弃了必要的辨伪纠谬。为着论题的确立,举例式地以个别取代一般,以少数萌芽却长期得不到推广的“先进”,用以标识全局性的增长变迁,在我们的研究论著中间或有之。因此,重提以全面求证叙述为主,倡导考据与辨伪,并非自我降格,它或许真是对根治“以论带史”旧疾有益的一项传统健身运动。
综合观察过去的明清江南研究群体,有三个特点比较明显:(一)多数止步于1840年前,延伸至晚清不多,更少“入侵”到民国时期[9]。(二)多数偏好于狭小的太湖流域,江南成了只有“中心”而无层级、边缘推衍演变的“琼岛”,研究的整体意义大为减弱[10]。(三)主要以开发方志、笔记(附以少数文集)见长,以全“江南”、大时段的综合居多,各种专题分解不全(集中于城镇、经贸),较小单位(一县、一乡、一村)个案考察与区域内比较研究也相对薄弱,且没有形成扩散性效应,一定程度折射出目前存在史料取材重复、开发不足的缺陷,成了制约明清江南研究的瓶颈。没有这方面的显著突破,
新的局面就不容易打开。
在江南研究的前期,着力于总体概貌呈现与特征揭示,在当时既合乎情理,也确有其必要。文章总得先行破题,起承转合继之。今天看来,概论性的研究,重分析推理,归纳不可能完整,加以“进化论”的影响,极容易牺牲过程、细节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换取所谓“结构”、“增长”等等逻辑的圆满。这样,发展的不平衡与进退迂回的历史动态悄然若失,就很难克服百年来历史认识单线论与简单化的痼疾。何以后续研究亦逡巡于既定的“宏大”格局?分解性的,细部与个案研究难以形成大气候(这一方面华南研究成绩赫然,令人羡慕[11])?这都是值得深刻检讨的。
为了进一步申论上述意思,向江南同行推荐王庆成先生《晚清华北的集市与集市圈》一文[12]。论文的成功,除作者的学识功力外,很大程度上还依仗了史料来源的突破。最富关键性的史料,为李鸿章同治十年(1871)任直隶总督用心纂修《畿辅通志》时下属州县积累的许多“副产品”,其中《深州村图》和《青县村图》两种共载录有800余村的资料(另有《正定村图》残卷,作者无法亲见,从日人论著中转引)。由上述两种村图所载原始资料,州县集市的数目和分布情况及每集赶集村数的参差复杂,可以进行确凿可靠的考据,克服与纠正了由州县方志带来的记载缺憾;日本“满铁”调查以及著名的定县调查等实地考察报告,也直接间接地为这种深入考辨提供了参证。这就生动地证明,寅恪老所说“预流”确为史家必须掌握的学问要领:“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3]
由此勾起一段心情:长期浸润在1840年前的古代世界,均能体验到史料的不敷需要,用以精确分析的软件甚少,叫苦不迭。试问:华北、华南可以搜索到不少高品质的“另类”史料,江南就没有?因指导论文的缘故,这几年颇注意搜索寻觅各方面史料来源,发现晚清开“眼”以来,作历史记忆者毕竟视野有所开拓,观念亦已大为更新;入至民国,尤其是试验“地方自治”的阶段,不少县府都曾花力气进行过现代观念指导下的社会调查,而且还有“农村复兴委员会”与“乡村建设”积累的大量成果。以上各类史料存录的素材与数据,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较之以前含混笼统的文字描述,数量与质量均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日本“满铁”在江南的调查,工夫也了得。晚清以来基层政府的档案、文牍亦并非全数堙没,用力搜索多有存留,土改前后的调查材料更是不难获得。明清江南研究固守于定居的家园,划地为牢,不善利用这方面的史料参证,待读到王庆成的雄文,更是惋惜心痛。说实在,待到真有觉悟时,我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史家立论,最忌孤证、偏证,讲求的是资料积累博瞻与会通,尤须参证辨伪,征实求真。王国维倡“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立“三重证法”[14],更是因应史学的变迁,在史法、史术方面揭出一种新的境界。或许是专业分化过细的“现代性”,抑或习惯思维定式作祟,我们往往不敢轻易跨越1840年人为设定的界线。然而,在中国历史底层,在历史的深处,时间没有想象中那样尖锐淋漓,在社会机体上划出深深的鸿沟。是则以同理衡之,既然地下出土文物、古典文献资料、民族学人类遗迹、外国异族载录都可以成为相互参证对勘必备的多重材料,同一空间、变迁连续的近代史料,何以就不能成为明清(—1840)历史对勘辨析的重要参证?尽管此项工作极为繁重细琐,耗时费神,不少朋友都有共同的预感,有关人口、产量、生产率、消费水平、家庭生计,乃至涉及社会、经济结构的诸种复杂形相,上述丰富史料源待到我们广泛开发与利用,参证前此认识,正如王庆成成功实践展示的,不说长袖善舞,至少也不必再捉襟见肘,许多判断由此可能获得有力的丰富或修正,有些认识盲区也可能被打开[15]。
历史有渐无顿,无骤变之迹,更无骤变之理。在时间的连续中悄悄然无声小变、渐变,是历史的定力和常规。看似翻江倒海的事变,颇迷人眼球,潜在的规则却会在事后偷偷复活;人为设计的突变,历史的力量会把它拖回应处的位置。中国式的发展轨迹,确实是西方历史所不能类比的,有其自在的逻辑。虽无弗兰克提醒,我们自己也应有足够的体验。以关怀中国发展为指归,明清江南研究如何上下联动,“通古今之变”,理应成为未来方法论变革的重中之重。无论课题的大小,是综合还是分解,即或细微的个案,如能以历史为养料,传达中国发展的内在独特神韵,给国人予一种处理历史与现实的智慧,启迪现在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包括掌握“现代化”权力的官员,要十分重视历史深层与底部的分析,那么我们的江南研究,就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而不至孤芳自赏,读者面越来越窄小。
--------------------------------------------------------------------------------
* 编者注:此文原本是王家范教授为陈江《明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一书所写的序言,应本刊之邀,先行发表。发表前,作者又作了修改加工。
[2]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3] [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
[4] 其实当时较顾颉刚更激进的是钱玄同。他在《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书》中,对顾颉刚说: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古史辨》第1册,280页)
[5]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革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6] 参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引论”第12-13页。征引非尽为原文,乃笔者师其意而用之。
[7] 李世众的硕士论文,曾经以“深山中的都市”,向我们展示了浙西南少有人知的市镇——遂昌王村。我去过那里,深感历史的奇特,非书本所能尽揽。包伟民教授指导的研究生钟永民,以台州仙居皤滩为个案,作过实地考察与研讨。我有幸见过他的开题报告。这是一个位于仙居丘陵河谷之间,依傍永安溪而产生的市镇,亦少为人知。我对这个很不熟悉的市镇类型,饶有兴趣。不知成果已经发表否?江南市镇研究,敝人一度混迹其间。今天检查起来,自觉孤陋寡闻。例如由杭州沿富春江而下,市镇格局、农民上市镇的状态迥异于苏松嘉湖;从肖山往东或东南行,宁绍温台,溪川山谷丘陵萦绕,市镇的方位与布局,又是一番光景。再回头看旧文所说“结构”,全然是一隅之识,并不能覆盖全江南,只能以“小江南”自嘲。然检阅“小江南”边缘的上海浦东地区,又发现异样的个性。此项修正工作,陆续有所搜集,然一直未能了却心愿。天假以年,如能收敛浪迹天涯之心,或尚有机会。
[8] 这种情况,直到民国前期进行社会调查时,亦然如此。例如江苏吴县进行的社会调查,由综合“地方自治附市政设施状况”各区表格计算而得,全县19区竟有127镇,有的区多至9至10镇,有些大镇竟分划为3至4个镇,说明市与镇不分,当地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载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1930年编印:《吴县》。因此,我们必须将地方志和当地习俗所称“市镇”,与我们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的集镇,加以区分。市镇数量增长的描述,往往受此误导,又搀杂主观意图,仍需要花大力气比勘辨析,期与实情相符。
[9] 据笔者所知,在涉及近代方面,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等均作过艰辛努力,颇有创获。惋惜的是,他们似乎没有持续做下去,也缺乏学术群体的铺垫。此一情况,在江南几所高校,都有类似窘态。
[10] 据有关披露,日本学者现在致力于宁波地区的历史考察,非常深入细致。成岳冲源于乡情,曾做过很不错的细微考察,颇有心得,惜从政于宁波政界,也不再可能回归。李世众刚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选择了温州为对象,发现有不少与“小江南”同中有异的景象。诚望新生代学者多多往薄弱环节开发。
[11] 例如陈春声:《蓝鼎元与清初县政——〈鹿洲公案〉的研究》,以及有关潮州的系列论文,特别是《乡村神庙系统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为例》。郑振满、刘志伟等也有不少出色的创作。他们多着重于历史人类学的开发,但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内在的复杂性,提供了前此少有人注意的视界与第一手材料。
[12] 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文中利用华北(主要是直隶与山东)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参证近代以来的许多实地调查(如定县与“满铁”调查)、西人游历见闻等丰富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详尽的描述与各类数据复杂细致的对勘,统计图表用工俱精,心血不菲,证明华北各州县集市数量参差不一,甚至差距很大,集市数与州县人口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的关系,亦无有规则的比率。集市圈即集市与赶集村庄的空间构成,所包含的村庄多至近百村,少則二三村,甚至一村。由此对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较全面地提出有说服力的诘驳。王庆成论述的“问题意识”有鲜明的针对性。早于此前,日本的加藤繁曾经给出过清代州县村镇集市的“平均数”,施坚雅还比较过各区域此种“平均数”与增长速率的差异,进而大胆揭出分布“规律”及诸多理论假设,在当时实属不易。但先生清醒地认为:“平均数是研究概况的重要手段;但平均数不能显示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如不能推究平均数所包含的多样性,认识就可能流于空泛而不切实际。”
[13]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14] 王国维:《古史新证》,载《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
[15] 李学昌、董建波多年来一直从事于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的调查与研究,我是一直全力支持的。此项工作无十年之功,难以突出显示绩效。可喜的是他们有此耐心,不以目前少有人知而却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