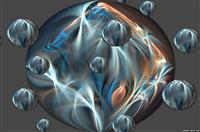对中国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学者来说,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这个名字早已就耳熟能详了,他的基本著作也大部分译成汉语出版,如其中期的扛鼎力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晚年的聚精杰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等,如今其早期著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1951)也即将付梓,这对于中国现代史及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史华慈,汉译也有史华兹、史华茨、施瓦茨等。但据笔者所知,“史华慈”才是他本人给自己起的正式汉语名字。作为当代最著名的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史华慈内心存在着热烈的人文关怀。他曾富有感情地说过:“有人喜爱中国﹐有人厌恨中国。但我尊敬她”。虽然史华慈大名鼎鼎,但知道他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笃信犹太教信仰的国人并不很多。一位才华横溢、治学严谨、分析入微的世界级著名学者如何能在“信仰”与“学术”之间荡漾,本身就是一件很难想象的费解之事。宗教是信仰,学术是科学,难道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可能性空间吗?然而,事实就的确如此。史华慈青年时期的研究兴趣其实并不在现实政治。20世纪30 年代末期他在哈佛大学本科主修南欧文学,其学士论文是《巴斯噶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心议题是人性﹑伦理﹑宗教。毕业后他曾想当高中语文教师,甚至曾一度有意做犹太教教士。他写的第一篇论著是关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可见青年时代伦理与宗教这些带有深厚内在人文倾向的问题,就已渗入到了史华慈“理解世界”之中,并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种种外在机缘,使他进入费正清主持的中国地区研究班攻读硕士学位。史华慈曾诙谐地说,那时恰好有一笔奖学金“由于金钱的引诱,我放弃了对中国古代佛教的研究,开始注意中国当代问题。”① 在此后的数十年时光中,他专注于中国问题的几乎所有问题,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每日都阅读《人民日报》,而且甚至不间断地写出大量讨论中国现实政局的时论文章,一直持续到晚年。这些文章分别收集在1968出版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和史华慈退休后1996年出版的《中国与其它》的两本论文集中。它们不仅成为史氏自身学术发展的忠实记录,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些论文涉及的问题十分宽阔,包括五十年代的中苏同盟,中国的百花齐放,反右,大跃进,中苏论战,文化大革命,等等。“从文章的标题上﹐很像一本通常的时事研究,或新闻分析论文集。但是它却提出了一系列新闻分析往往未能提出的远为深远的关切与议题。例如,史指出在比较具体的层面上,该书提出了什么是当今的共产主义?其走向是什么?中国整个社会走向何处?整个世界走向何方?在比较概括的层面上,它提出了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跨国界的意识形态之关系如何?当一套思想从自己的文化与历史的母体移植到另一个异质的文化与历史环境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当它一旦上升为这个社会的统治的意识形态时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它甚至提出并讨论了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社会行为)到底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而且涉及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的根本问题”。②
值得在此提及的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史华慈对自己的看法和定位至少与对研究对象的透视一样清晰,甚至更加明白。面对不可穷尽的大千宇宙和知识海洋,一个人所能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有限了。人们探索研究,透视分析,著书立说,只能是永无止境之思想对话的一个瞬间片段,用史华慈的话说就是“一个片面的﹑可能失误的微弱的声音”。他曾把整个非物质层面的文化比喻成一座储存人类经验与思想的“图书馆”。他说:“写书的人多半热切希望把自己的书放在图书馆未必就意味着从此他的思想就将死去。诚然,绝大部份的卷册可能再也无人问津,可是谁也不能保证这些书就此长眠不语。”③
在学术研究的方法和风格方面,史华慈提出了著名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s)命题,其核心语义是指人文研究领域中不大可能给出某种绝对判断行的确切答案,在众多研究者的结论中,必然体现出“富有成果之歧义性”(fruitful ambiguity)的张力。这是因为研究者所具有的视角,用史华慈常用的语言表达就是“关切”(concern)、“议题”(issue)、“预设 ”(assumption)等,除了具体时代背景的复杂性以外,同时与研究者自身的经历也不无关系。所以,如学者所论,他在方法论方面实际上试图超越经典的“观念史”与“知识社会学”之路径,而直接向“基始依据”(primary datum)展开问询。④ 史华慈认为,人类有一些“历久不衰,反复出现的共同关切(perennial common human concerns),往往构成某种人生的奥秘,它们是思想论说的原生点;这些原生问题之不同层面的反映,就成为“议题”。只有“关切”而没有“议题”则只是倾诉而不成其为学术;为什么共同的“关切”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议题”?这又涉及研究者立论时所持有的或已阐明或未明言的“预设”。诚如学者所言,由于不断提出比较深层的关切﹑议题﹑预设和问题意识,所以史华慈的著述,哪怕是一个简单的评论,都会“使它们具有通常时论所罕见的思想洞见和耐读性。”⑤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它是在史华慈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195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2年和1967年再印的两次,但没有修改。史华慈教授的这部专著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是由于它在西方学术界第一次提出并界定了 “毛主义”(Maoism)这一核心的分析范式,从而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走向“学术论证”的分界性标志。
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的创始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48年就曾断言,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了在中国最后使共产主义中国化的‘毛主义’的基础。”作为费正清学派的两大天才高足之一的史华慈[另一位是《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作者、英年早逝的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秉承师意,对费正清的这一论点作了全面的创造性发挥。史华慈认为,毛泽东革命的确不可否认地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实践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此笼统地概括,在理论和学术上并没有多大意义,而真正需要做的研究应当是提炼出“中国不同于苏联”,“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的独特内涵。如果说这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最早的“文本”,那么,它就应当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史华慈指出,毛泽东这部具有鲜明创独精神的中国政治名著,显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一种独特的倾向”,“它把农民当成革命运动的核心”,并把完成民主革命的70%的功劳归之于农民,而只给予“城市居民和军队”30%的地位,并把对于农民在革命中地位的评价“作为判断政治党派革命与否的价值标准”。史华慈说,读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人的印象是,它“或许既是出于一个俄国民粹主义者之手,但也是由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写。在这里,我们确实找不到那些贯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对农民独立革命作用的责难”。毛的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对整个共产国际路线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战”。因此,正是在关于革命的主要动力的认识角度上,“毛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重要的核心思想预见的“背离”,从而构成“行为的异端”。费正清学派的另一位学者布朗特(Conrad Brandt)也认为,“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有着明显的差异,毛所强调的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 ”(the revolution by the peasants but only for them)。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则只把农民利益当作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我们应注意的是,史华慈在这里所说的“背离”和“异端”都没有丝毫的贬义,而只是认为,相对于把现代产业工人作为革命主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毛泽东革命改变了行动的主体但却维持了原有的目标。所以,“异端”就意味着“独创”,“背离”则等同于“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史华慈明确指出,“毛主义战略实质上是把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因信仰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由完全农民所组成的群众基础之上”。“毛主义 ”语义学的核心是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建立在农民支持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其政治战略而言,它成为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传统的“独创性异端”。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一书中史华慈自问自答式地阐述了他关于“毛主义”性质的基本观点:“以某种信仰为基础的历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偏离其最初的基本前提而仍可保持它的特性呢?这当然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分化,形成各种不同的形式,“由此,我们主张在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毛主义在行动上的异端意味着这个分化过程中的另一个重大举措。…… 但是我们依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它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之完整而生动的理据”。
无论史华慈把“毛主义”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独创性异端”的概括日后引起了多大的争论,但都应当承认,这种概括和判断奠定了后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起点,甚至可以说,它至今仍然是西方这一研究领域内占主流地位的“传统”。在“史华慈模式”的影响下,这种“毛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异端”的说法,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和不断发展。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ellan)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就把“史华慈模式”作为分析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框架。麦克莱伦说:“毛主义是列宁主义与经济落后的中国以及某种传统中国思想的综合物”,并从五个方面对这个定义做了详细概括和扩展:一、中国以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因而农民不是发展政策的牺牲品,而能够被动员起来促进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模式,因为农民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中国共产党毋庸争辩地是一个农民党;二、毛主义强调意识的重要性。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因此把一种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意识逐渐灌输给农民是必要的,使资本主义阶段 ――无论在实际发展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缩短而入社会主义阶段,就已经意味着这种灌输需要增强,因此就有了“文化革命”;三、毛在30年代开始形成的游击战争的理论是以农民的积极合作为基础,已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广泛的影响;四、中国已经进行过多种形式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意义已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阐明,并在“文化革命”中――虽然毕竟总在党的控制下――付诸实践;五、毛主义含有一种道德的、清教徒式的调子,即强调罗素向往的那种节俭和对于普遍的善的献身精神。显然,在这样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处处感觉到“史华慈模式”的影子,可见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学派的影响。
一本半个世纪以前写给外国人看的书,对于身处21世纪的中国人有何意义呢?换言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的现代价值究竟何在?依笔者之见,该书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今天的“我们”,具有启迪意义。
其一、作为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是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之学术史和思想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必经桥梁。如果用目前流行的制度学派的术语表达,那么,我们可以说,“史华慈模式”就是那产生“路径依赖”效能的端口。正是它奠基、影响、引导、甚至规定了后来西方丰富多彩的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格局。站在50年后的角度上看,虽然在史料价值方面,史华慈教授的引证几近“常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就他的基本结论而言,至今仍足以使后来的学人难脱其臼。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史华慈模式”对现代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渗透已经到了如此深入的程度,以至于在西方学术圈内再专门提起它就几乎变成了缺乏常识的代名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已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某种带有象征意义的“研究隐喻”(metaphor for studying)。
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部著作也就名副其实地成了解和理解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必读入门书了。
其二、史华慈书中关于中国与苏联两种不同性质之共产主义政治社会模式的论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所证实,从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直到90年代苏联的最终解体和中国的持续运转。历史学者当然不是算命先生,但真正的“比较历史研究”则会以自己的方式对社会结构的重建产生影响。“史华慈模式”的真正方法论意义在于,他说明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理论体系,在对具有特殊性的对象发生影响时,必定会产生多样化、甚至是无法预料的后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原本的理论结构和推导逻辑在实践中的“异端化”、“偏差性”以及 “扭曲” 和 “修正”,与其说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不如说是情理之中的必然结果。人们之所以会对这些后果感到困惑,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把握住自身历史的独特脉络。因而“地方性知识”是比较历史学和比较思想史研究不可忽略的绝对基础。我们在史华慈教授的著作中,压根就没有发现横遭后现代主义质疑的“本质论”和“ 整体论”之“宏大叙述”的丝毫意识。这不仅说明了一位优秀历史学家的先见之明,而且更显示出教导历史学家之历史主体自身的严肃与神圣。
其三、为了进一步理解“史华慈模式”历史分析的精髓,书后附录了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著名学者林毓生教授精选推荐的三篇史华慈的重要论文。其中两篇题为《道德王国: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史的宏观透视》和《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摘自史华慈1996年亲自选编的最后文集《中国与其它事务》;另一篇摘自由麦克法考尔主编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前两篇论文中史华慈在政治哲学的深度上,试图把现代社会的道德缺失与价值迷茫与毛泽东政治象征及其他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深层意图联系起来,认为“考虑到传统价值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衰落,“民族领袖”(ethical vanguard)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政治法令创造出新的社会道德、新的公意,政治上的这些作为也不能仅仅视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工具,它们有着十分紧迫的现实需要”。史华慈还认为“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特征之间是声气相通的”,而卢梭关于道德与政治形式之间关系的论述与中国传统道德-政治思想某些侧面之间的共鸣,或许比其他社会的传统道德更大。这种宽广、独特的比较视阈是值得中国学者再三深思的。而后一篇论文则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Total Redemption)与“全面挫折”(Utter Frustr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使我们看到,处于现代中国内外关系背景之中的毛泽东,其思想是一种紧张、困惑、冒险、民族自立、一党执政和大众主义等诸多要素所组成的混合物。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运用费正清学派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经典之作。
相对于人类的即时行动,历史的书写永远是滞后的,但正是在这滞后所产生的距离感中却隐含着冷静、智慧和公正。如此而言,一部50年前由思想名家所“做”之历史名著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品味再三吗?!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经由本文合作者王文涛教授同意,在此刊用。
注释:
① 史华慈:《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方法问题》,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1987年,第56期。
② 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世界汉学》,北京:第二期。
③ M. Meisner and R. Murphey ed.The Mozartan Historian: Essays on the Works of J. R. Levenson. 1975,107-108.
④ 参阅:陈少明《穿越理解的双重屏障--论史华慈的思想史观》,《开放时代》,广州:2001年第5期。
⑤ 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世界汉学》,北京: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