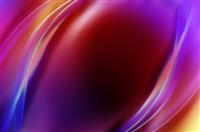
摘要: 在我国的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艺术自由被作为文化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保障。在国家与社会二分的立场下,艺术自治应该是国家与艺术关系上的根本原则和出发点。受宪法基本权利保障的艺术生活领域是以特定形式进行的人的自我表达的结果,因而由艺术本质出发在规范面向上就意味着对以多数决形式所做出的立法干预和个案衡量之下的行政干预行为形成了不同的正当性证立负担。我国宪法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大量的文化政策条款,它以某种核心价值观强调了国家对文化发展的主导性作用,这在客观制度面向上为国家对艺术自由的限制保留了巨大的空间,使得艺术自由之上的保障和限制关系面临着来自宪法体系内部的巨大压力。
1982年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里所明确列举的自由通常被人们称为“文化权利”。从该条的规范结构看,“文化权利”显然不是一项单一的权利,而是一项复合权利,艺术自由即属于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宪法上直接的保障依据。立足于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体系,从文字和体系解释出发,这里首先涉及了一些重要的宪法认知:其一,艺术自由是文化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符合文化权利的本质特征,受制于文化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其二,艺术自由“涉及国家对艺术创作和发表领域的保障意义”以及“国家鼓励人们从事创造性的艺术工作的积极意义”,也就是主观防御权利与客观法——以创造性为代表的艺术自治以及国家的艺术促进义务——两个面向。
除了文化基本权利条款,现行宪法还在序言和总纲部分规定了有关文化主题的内容:第一,序言第7自然段中的文化事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二,序言第7自然段中的文化发展目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第三,第22条所确认的文化事业的前提:“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等;第四,第24条第1款所涉及的精神文明建设:“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第五,第24条第2款中的思想道德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1]可见,我国宪法中贯彻的是一种与文化多元性不同的一元化的文化政策,它强调的是核心价值观。在这种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对文化的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文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达到某种目标的手段。[2]借鉴德国宪法学界的通说,我国宪法中明确设定社会文化政策的宪法规范属于“国家目标条款”(Staatszielbestimmung)。[3]从规范效力而言,“国家目标条款”是以国家任务(Staatsaufgabe)的实质内容而成为规范所有国家行为的方针(Richtlinie)和训令(Direktive),它的位阶高于一般政策目标,在此面向上拘束立法者,限制其政策形成自由,至于手段上如何实现该目标乃立法者的权限与自由。[4]同时,“国家目标条款”基本上归属于“宪法原则”,其拘束力比属于“宪法命令”的“立法委托”强,拘束的对象又并不只限于立法者。[5]因此我国在文化上的国家核心价值观及其目标,以宪法规范所确定的文化的国家目标条款的形式,对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立法也能产生直接的约束力。
不同于中国宪法,德国基本法对有关社会政策的问题则采取了开放性的预设,比如对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文化制度等都没有进行限定,而是交由一般法律来加以确认。当然,基本法在价值观上是中立的(weltanschauliche Neutralitaet),但其并不是价值中立的(wertneutral),宪法的价值秩序表现为对立法者产生直接约束力的基本权利价值决定。其具体的意思是指,立法者只要尊重基本法(尤其是它的基本权利条款),就可以采取任何他认为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
两相比较,我国虽然也把艺术自由明确纳入了公民基本权利的清单之中,但宪法同时还规定了相应的文化政策条款,这就决定我国无法直接照搬西方的宪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仅从基本权利体系内部去探寻艺术自由的具体内涵,而是要从我国整个宪法体系出发去分析艺术自由真正的规范轮廓。虽然如此,无论釆取哪一种立场与模式,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艺术自由的实质理性始终在于公民自由与国家限制两个面向及其各自正当性理由,因此问题的关键最终还是会聚焦于艺术自由形成与限制交集之处的立法者,而落定在确定国家干预允许的界限之上,这使得两国有关艺术自由的宪法保障之间的比较与借鉴具备了适当的理论框架与平台,并藉此在各国有关艺术自由宪法保障显而易见的差别之上明确是什么更高的价值和判断影响了各国的立法和司法走向。因此,本文主要分成以下三个部分来展开:第一部分是寻找国家与文化的关系模式之下艺术自由的本质;第二部分致力于探讨国家如何在艺术自由的法律形成与实施中保障艺术的本质;第三部分是重点分析国家对艺术自由的合理性限制及其论证。
国家对艺术自由如何以法律保障的形式加以确认并形成,这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律推理过程。艺术自由是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正是在此意义下形成了国家对艺术的基本认识。
按照德国学者Dieter Grimm的归纳,由国家对待文化的不同立场出发,国家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有四种模式:(1)指挥模式,即国家依照政治定律操纵文化;(2)二元模式,即国家与文化分离;(3)功利主义模式,即国家为了国家文化目的以外的其他利益关照文化;(4)文化国模式,即国家为了文化本身的目的关照文化。[6]在十八世纪前,文化作为由国家所确认的单一价值受到严格的拘束,但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封建制度逐渐弱化后,在国家与社会二分的立场下,文化事务逐渐被归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而要求国家与之保持距离。然而,欧洲的“理性法国家理论”一直强调国家应该被视为确保人民自由与安全的机制,并且现实中也始终存在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现状,这些都对国家在文化事务上的适当介入提出了要求。[7]从国家与文化互动关系的回顾中,我们不难做出在文化问题上宪法国家积极在场的基本判断,但国家对文化领域的干预行为有着正当性证立的负担,只是在不同模式下由文化以外的目的或者以文化本身的目的来获得正当性的区别。
因此在上述国家与社会二分的立场下,如果承认文化自为目的而非手段的基本观点,艺术的自治就成为了国家与艺术关系之上的根本原则和出发点。艺术自治首先意味着国家对艺术始终应该保持距离和维持中立性。早在1924年德国学者Ernst Beling就曾提出“艺术与法学实际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发展”。[8]因此即使在宪法基本权利保障之下必须对艺术生活领域进行确定时,这也不是以界定“艺术是什么”的本体式提问来加以应对的,因为这样的追问原本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本假定上,这样的追问方式注定会落入将艺术现成化和物化的陷阱。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只能被视为一个直接关系到人的存在意义的求索过程。[9]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在动态中考察艺术的本质,便不难发现:所谓艺术就是人们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利用物质媒介或观念符号所创造的、能够诉诸欣赏者感觉器官并引发情感体验的人工制品。艺术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先锋性而一直致力于艺术界限的突破和扩展,艺术在本质上的多变潜能决定了宪法中的艺术自由不应是静态的自由保障,而应是动态的自由保障。在此意义之上,[10]艺术自由才被国家视为纳入宪法中的个人基本权利加以保护的法益,并形成了与其它基本权利之间的界限。
由艺术的本质出发,艺术的生活领域并不是一个“是什么”的先验的、静态的、形而上学的界定,而是以一定的形式所进行的人的自我表达的结果,因此宪法对艺术自由的保障就是对人基于自由意志自主形成行为的自由中自我表现的保障,艺术自由也正是基于其作为促进自我实现手段而受到了宪法保护。艺术自由的目的在于表意人本身,其并非追求真理或社会发展的工具,而是为了确保个人独立自主地表现自我,进一步促进个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实现也正是文化基本权利的保护核心,当然也是艺术自由作为文化权利的本质要素。[11]正是在此意义下,美国宪法和日本宪法中通常把艺术自由视为表现自由尤其是象征性的言论自由的保护内容。[12]也正是因为如此,各国无论是把其归入言论自由还是艺术自由或者人格权利的保护法益中来加以保障,从根本上来说,其都是被归于对个人自我表达与实现意义的保障,这才使得宪法规范的艺术自由背后的诉求可以与艺术的本质特征间保持和谐一致,并得以解释为何其在基本权利清单中往往会受到特别的强调与保护。
三、艺术自由规范内涵的形成——三阶的构造结构
基于上述分析,艺术自由的权利规范背后的诉求在于对艺术自治下的自我表达的保障,这一观念还必须放置于特定宪法的整体框架下,从规范形成与规范适用两个面向中去进行具体的理解,因为这还涉及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一些基本价值判断。
以德国基本法为例,德国的立宪者放弃了将基本权利的限制完全交由某项概括性条款来完成的传统做法,而是选择在每项基本权利的保护领域后,分别描述该项权利的限制性规定,而这些具体的基本权利限制又是藉由区分不同类型的法律保留来完成的。根据规范限定的繁简程度,德国学者将基本权利条款中的法律保留区分为简单法律保留(einfache Gesetzvorbehalt)、特别法律保留(qualifizierte Gesetzvorbehalt)[13]与“无法律保留”(ohne Gesetzvorbehalt)[14]。德国基本法中的艺术自由的保障条款是第5条第3款,属于典型的“无法律保留”保障的基本权利。该基本法在法律保留上的差异性处理使立法者针对不同的基本权利具有了不同的限制权能:在简单法律保留中,立法者所获授权的弹性最大;在特别法律保留中,立法者进行利益衡量的权限因为宪法的周延规定被大大限缩;而对于不受法律保留限制的基本权利,立法者的这种权力则被彻底排除了。立宪者之所以对基本权利设置不同的法律限制,主要是基于基本权利属性和特征的差异:宪法以法律保留形式所提供的保障强度与其被立法破坏的可能性之间成正比,即立法者虽可对这些权利进行限制,但必须满足权利条款中的各项条件。而如同艺术自由、学术自由、宗教自由以及人格尊严这些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以历史经验来看,具有“保障少数人”的特质,并不适宜由立法所代表的多数民主来决定。[15]这样的规范形成从防御国家侵害(尤其是立法侵害)的角度体现出了国家与艺术关系的第一层构造。
因为只有一个可描述且可建构的保护客体,法律(包括宪法)才能在规范意义上对其进行保障,所以界定艺术的法律定义是国家与艺术的第二层构造。在法律的范围内去定义艺术的概念一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首先,在国家与社会二分的立场下,为了保持艺术自治的特征,要考虑的是“定义的权能”(Definitionskompetenz),即艺术的自治是否意味着艺术的定义权应该始终保留在专家或者权力相对人的手中,在法律上国家和有民主正当性的机构对艺术概念的定义权能是否会破坏艺术自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判决认定:为了实现规范意义上对艺术自由的保障,在确定保护范围的意义上必须对艺术的概念限定一个事实性的范畴,因此在法解释学涵义之下并不存在所谓的“定义的禁止”(Definitionsverbot),而更应该是一个“定义的要求”(Definitionsgebot)。[16]但是同时为了避免艺术的规范性概念中的“艺术法官化”(Kunstrichtertum)的困境对艺术自治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内容上首先采取了排除式的规定形式,即基于艺术自由的宪法保障目的以及艺术自由基本权利主体的自由地位(status libertatis)而导出了国家的评价禁止义务,明确其不对艺术内容品质以及效果进行实质判断(Ausschluss staatlicher Niveaukontrolle)。[17]其次,艺术概念定义的任务主要被落实在了艺术自由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确定之上。因为在法律上不能对艺术作实质内容的定义,所以仅能在技术、形式及种类上加以界定,在“艺术”概念定义的发展上先产生了所谓的“形式的艺术概念”(Formaler Kunstbegriff),即通过例如诗歌、绘画、舞蹈等形式或种类来认定法律上受到保护的艺术,凡逾越此形式的任何法律定义都是不被允许的,这就是德国学者Wolfgang Knies所发展出来的所谓“形式——技术理论”(formal-technische Lehre)。[18]但很快人们就意识到形式艺术概念无法适应艺术创作持续不断的创新进步。联邦宪法法院为了克服艺术类型化观察上的局限性,尤其是在Mephisto-Urteil开始转向于对艺术概念进行了实质内容上的检验,而产生了所谓“实质的艺术概念"(Materialer Kunstbegriff)。特别强调了艺术活动的本质是一种自由创造的形成(die freie schoepferische Gestaltung),在艺术创作中产生的主要不是信息(Mitteilung),而是风格(Ausdruck),且是艺术家个人人格的直接风格。[19]在学界对艺术实质概念还存在着其它不同的定义,有些学者认为必须考虑是否有“艺术思想的放射性”(eine Affinitaet zum kuenstlerischen Idee);[20]也有学者认为“艺术至少是一种心灵思想的产物,其本质要素在于想象与美学,至少要显现创造的特性”。[21]对实质艺术概念的批评,除了其逾越了概念价值中立的界限之外,还在于定义中包含了太多的要素,以致总会把根据艺术家自我理解、根据社会的观点及专家判断被视为艺术创作的现象排除出保护范围。[22]不同于以往对艺术概念进行定义的屡次尝试,联邦宪法法院在Anachronistischer Zug判决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艺术加以一般定义的不可能性”(Unmoeglichkeit, Kunst generell zu definieren)。[23]在传统的形式与实质艺术概念的对立之后,联邦宪法法院提出了多样性的开放艺术概念。该法院指出:“艺术表达内容的多样性……以至于产生一个实际上取之不尽而多阶段的信息传递。”[24]因此有学者也将此定义称为“沟通理论的艺术概念”(kommunikationstheoretischer Kunstbegriff)。联邦宪法法院在 Anachronistischer Zug 判决中并未在现存的几种对艺术的规范性定义中做出选择或确定,而是首次以艺术特征的整体方式进行了具体个案上的涵摄。整体而言,“艺术也就是以传统艺术类型或类似的新形式(in aehnlicher neuartiger Formgebung)所进行的每一种创造性的形成(jede schoepferische Gestaltung)”。[25]
站在宪法学的角度去审视“艺术”,并非要以哲学的观点去探求艺术的本质,而是寻求一个具有宪法规范目的的艺术概念,使我们在宪法解释上可以明确进行构成要件的涵摄。在开放的、不可定义的艺术概念之下,“艺术概念的特征”成为了宪法上艺术自由保护法益的连接点,这既不会因为针对艺术实质内容的判定而涉入价值判断的泥潭,也不会受制于形式定义的“局限性”。相对于迄今为止所提出的艺术定义或描述,其更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此并未给出一个封闭的模式(keine abschliessende Formel),而是指出了相当开放的宪法决定要素,[26]这不仅实现了无论是艺术的可能内容还是艺术的展现方式都不由宪法来做出明确限定的目的,还同时实现了对具体个案中在宪法法律上艺术自由保障的保护范围是否被打开的判断,即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功能。上述德国基本法中艺术自由宪法保障在规范形成与规范适用中的二层构造是我们可以共享的对艺术自由提供法律保障和进行规范解释的基本理性与逻辑,因为它具体地体现出了国家对艺术的尊重与促进义务,以及如何在规范框架里给予艺术尽可能宽广的创造空间。
然而,任何权利和自由都不是无限的,为保障社会共同体和他人的权益,国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做出限制,当然,国家的限制只有在符合了限制理由和要件时才是合宪的。因而,“合宪的限制”成为了第三层构造,在此衡量之下方能最终确定国家与艺术间的关系。不同国家实在法中所规定的限制理由和要件,使得各国的艺术自由可能具有了不同的规范内涵,这对确定中国宪法中的艺术自由的规范内涵意义尤其重大,因为中国宪法中不仅规定了艺术自由的条款,还有统一的基本权利限制条款(第51条)以及文化政策条款,它们共同作用于对艺术自由所进行的限制。
四、艺术自由的限制——立法与行政规制的正当性论证
国家公权力与社会自治分离与制衡的关系就像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国家公权力如果过于强大,那么社会自治的空间就会不断萎缩,导致社会创造的积极性窒息。而如果社会自治的不断扩张在社会自治领域完全排挤出国家公权力,最终社会自治也不能自保。[27]德国基本法中作为不受法律保留限制保障的艺术自由是经由联邦宪法法院判决中对无法律限制保留的基本权利所发展出的“宪法内在限制”而达致了两者间的平衡,即宪法应被作为一个统一的系统,第三者与之冲突的其它权利以及宪法所保障的其它法律价值和秩序,对这些不受法律保留限制的基本权构成限制。[28]宪法的内在限制要求立法者在面对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和宪法价值时必须承担进行利益衡量的义务,为了避免立法者在进行法益权衡时忽略宪法规定的显而易见的差异而过度挤压那些无法律保留限制的基本权利,联邦宪法法院还特别强调要遵循“实践调和”(praktische Konkordanz)的原则,即立法者不得偏重某项价值并使其获得最大程度的维护,而是要使所有的法律价值都能得到最妥善的衡平。[29]经由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艺术自由在限制层面常常会受到挑战的原因逐渐具有了清晰的轮廓,其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类型:(1)基本权利冲突(比如人格权、青少年保护);(2)刑法中有关风俗法的具体规定;(3)自由的基本秩序;(4)对国家象征的侮辱;等等。
以与人格权侵害相关的Anachronistischer Zug的判决为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首先确认了:在宪法内在限制的情况中,艺术自由与人格权互为界限,须在艺术自由与受到的人格权侵害之间做出权衡,即立法者的理性只在于确立一个不偏袒任何宪法利益、可供个案衡量的框架,在个案衡量上则要探究人格权受侵害的严重程度是否己到对艺术自由的保障应予退让的程度。首先,鉴于艺术的高价值,微小的侵害或者仅仅是一个严重侵害的可能性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但在相互竞争的法益之中,被确认无疑是对人格权利的严重侵害时,是不能通过艺术自由而获得正当性的。其次,人格权受侵害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个案中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让观众从其作品整体内容中连结到真实的人物,以及当观众得以建立此等整体连结时所造成的人格权侵害强度。[30]具体而言,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判例还确认了一些重要的标准,比如艺术家的表达是可以被解释以及需要被解释的,对解释来说不可缺少的解释要素就是对作品的整体观察的要求以及对作品多种解释可能之下的选择标准。在Anachronistischer Zug的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在权衡的标准中认为应从艺术美学的观点出发,考虑的是一个普通受众对这些艺术作品在其所使用的素材及素材的结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时所形成的观点。当然,对人格权侵害程度的判断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单纯考虑作品在“非艺术的社会领域”中的影响程度,有时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到其在艺术领域的独特标准等,同时还需要考虑艺术自由是否侵害到了属于人性尊严核心领域所保障的一般人格权。[31]上述衡量原则与标准的确认之中最核心的内容在于,艺术表达的规范解释与涉入人格权领域程度在论证的逻辑关系上并不属于先后或阶段式的,故而要决定对人格权的侵害程度时,两个相关衡量因素在关系上是交互作用的,并且只有在个别情况下综合了所有事实才能做出个别性的判断。
虽然立法者是透过人民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下所产生的,而法律也是经由立法者以民主化或多数决的程序所制定的,但有一些基本权利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展现出了其保障少数人的特质,面对公益及国家目的,艺术自由在历史上极具易被否定的倾向。[32]在上述基本权利教义学的结构之中,艺术自由不仅避免了以本质上不适合的多数决的构成要件来加以限制,而且为国家基于审慎衡量后的限制保留了空间。一个合乎时代和定位于社会的基本权利的解释使得艺术的价值和自身规律在法律的视野里得到了充分注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对于德国基本法将基本权利的限制规定放在每个独立基本权利中加以规定,我国宪法则是通过第51条整体上规定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33]这属于用统一规定的形式将“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列为法律限制基本权利的正当理由。这里包含了两层宪法意义:一是宪法在保障基本权利的同时,肯定其与他人利益及公益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故授权立法者可以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针对立法者所设置的限制,宪法决定立法者只能出于必要的他人利益和公益目的,始得限制基本权利。就此而言,此条款具有双重限制的功能;既限制主张基本权利的公民又限制立法者的立法裁量。
这样规范的结构,造成我国宪法中规定的所有基本权利都可以由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加以限制。所谓“防止妨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是要求基本权利主体不得超出自己的权利范围去侵犯他人的权利范围,属于禁止权利滥用的概念。[34]因此这里涉及的是基本权利冲突的问题。也就是说,此时国家要介入个人的生活领域必须是因为个人的基本权利己直接侵犯到他人的基本权利,国家必须对此做出利益衡量而去限制个人的基本权利。这其实就是德国宪法学说中的“宪法的内在限制”的内容。
然而,在艺术自由不妨害“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公共利益”的限制之中,重点在于确定何为“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关键之一是用来确定“公共”的范围的受益主体;关键之二则在于确定利益意义的利益内容,一般认为应以价值为利益的中心要素。利益就是主体与客体间一种价值形成的过程,客体被评价为能给主体带来好处或目的,所以利益的建构需要一个评价标准。通常的观点认为“公共利益”涉及社会上多数人的主流意见,牵涉到民主的多数决问题。因此在对艺术自由的公共利益限制中,国家和社会主流文化族群都可以依据其多数的权力优势而通过立法排斥少数的非主流文化。但是正如本文前述分析所表明的,
艺术创造内在所具有的反多数特质决定了其与公共利益间的冲突并不能全部交由立法者的民主多数程序来决定。因为宪法原本就是一系列价值理念的结合体,公益的客观评价标准自然应导源于此,以便使公益有一个更客观的评价基础。国家目标条款可以被视为是宪法中依具体事项而进行具体化的公共利益,也就是制宪者或修宪者刻意设定的客观价值标准,判断某些事物、行为或状态对不特定多数人是有利的,并且从效力上来说它也可以直接约束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因此,透过宪法上的“国家目标条款”规定,制宪者或修宪者己明确断定了共同体值得追求的宪法上公共利益的具体轮廓。如前文所述,我国宪法在序言和总纲部分详细制定了有关文化主题的客观规范,可以从中得出宪法中的文化政策强调的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某种核心价值观。现在的宪法理论一般认为,当基本权利的限制是来自于宪法本身的限制规定时,公权力的干预当然具有正当性并且是合宪的。[35]那么在法教义学的框架中,简单地以不妨害公共利益作为艺术自由的前提正好给予国家管制艺术自由以充分正当性空间。黑格尔曾提出的国家干预市民社会为正当的两个条件之一,就是为了保护国家自己界定的人民普遍利益时国家可以直接干预市民社会的事物,这实际上是从“国家高于社会”的理论上去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多少含有“国家优于社会”的理念。事实上国家也就此化身为了公民的道德和文化领袖,艺术自由概念本身的创造性特性很容易因应社会主流意见的影响而逐渐丧失。
我国宪法中的艺术自由似乎藉由这一保障和限制的框架而获得了一个不同但清晰的规范内涵。但是如果把研究重新返回到宪法中有关规定艺术自由的条款这一起点,我们普遍承认作为基本权利的艺术自由首先是个人的基本权利(Individualgrundrecht),却经常忽略了它还是重要的基本原则规范(Grundsatznorm)。这意味着艺术自由保障首先包含了一个调整艺术生活领域与国家间关系的客观原则规范,同时这个规范保障每一个在此领域的行动者有个人的自由权利,即艺术自由不仅是对于自由的艺术活动(die freie kuenstlerische Betaetigung)而言最为重要的基本权利,而且是对于艺术领域(der Lebensbereich Kunst)而言作为价值决定的基本原则规范。[36]因此宪法第47条对艺术自由的保障并不是在陈述一个既存事实,而是在表达制宪者的目的和价值判断。在1982年宪法修改过程中,宪法修改委员会对艺术自由条款几乎没有进行讨论。但是每一部法律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背景,这一背景对于法律含义的确定至关重要。1954年宪法第95条本来规定了公民有艺术创作的自由,1975年宪法却将其删除。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作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37]相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艺术自由遭到严重践踏的事实,艺术自由重新进入宪法或许已经表明了1982年宪法修改者再明确不过的目的。因此,源自艺术活动本身的免予过度干预的自治要求与我国实证法中国家公权力发动限制的广泛依据间的矛盾,体现出了我国宪法文本体系内部的张力。到底是基于本质上保障少数人特质的艺术自由而对在我国宪法中宪法管制正当性理由应进行严格检验,还是把实定宪法中的文化国家目标条款作为广泛限制的正当性理由,这可以被简单化为宪法理论中以宪法解释为解决方法的具体问题,但从艺术自由的宪法保障政策而言,我们其实面临一次更艰难的选择。
注释:
*本文受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资助。
[1]沈寿文:《关于中国“文化宪法”的思考》,《法学》2013年第11期。
[2]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3]“国家目标条款”是指宪法中对国家目标的明文规定,指的就是一些内容在于为现在以及未来的国家行为设定任务与方向的具有拘束性的宪法规范。可参考 Mueller-Bromley, Staatszielbestimmung Umweltschutz im Grundgesetz?, Berlin 1990,S.41 f. K. Hesse, Bedeutung der Grundrechte, S.143.; Ulrich Scheuner, Staatszielbestimmungen, in: Josef ListlAVolfgang Ruefiier (Hrsg.), Staatstheorie und Staatsrecht. Gesammelte Schriften, 1978,S.223 ff.;关于“国家目标规定”的定义常被引用的还有专家委员会(Sachver- staendigenkommision)1983年在“国家目标规定/立法委托”报告书中的定义,请参考 Bericht der Sachverstaendigenkommision Staatszielbestimmung/Gesetzgebungsauftr?ge von 1983,S.21。
[4]Alfred Katz, Staatsrecht, Grundkurs im ?ffentlichen Recht, 18 Aufl.,2010 Mueller, S.69.
[5]关于任务规范(Aufgabenormen)的分类,可参考 Mueller-Bromley, Staatszielbestimmung Umweltschutz im Grundgesetz?, Berlin 1990, S.31 ff。
[6] Dieter Grimm, Kulturauftrag im staatlichen Gemeinwesen, WDStRL 42, Berlin und New York 1984,S.46fF.
[7] Dieter Grimm, Kulturauftrag im staatlichen Gemeinwesen, WDStRL 42, Berlin und New York 1984,S.47ff.
[8] E. Denninger, Freiheit der Kunst, in: J. Isensee/ P. Kirchhof(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republik Deutschland, Bd VI, Heidelberg 1989,§146,S.848.
[9]钟华:《论追问艺术本质的方式之误——海德格尔艺术本质之思的启示与局限》,《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
[10]陈炎:《艺术本质的动态分析》,《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
[11]许育典:《文化宪法与文化国》,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95页。
[12]沈玮玮:《论象征性言论的限制与保护——以美国法例》,《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
[13] Hartmurt Mauer, Staatsrecht, C.H.Beck 1999,S.61.
[14]Bodo Pieroth & Bernhard Schlink, Grundrechte II, C.F. Mü 11er Verlag 2004, S.61.
[15]许育典:《宗教自由与宗教法》,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9页。
[16]比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就曾在有关色情是否属于艺术的判决中,对“色情”(Pornografie)给出过如下的定义:“色情是指在排除了其他人性因素的情况下,以粗野纠缠的方式引发对性过程的注意,并且从整体趋势而言,只是或者主要的是针对观察者对性的淫荡的兴趣时的一种描述。”
[17] BverGE 75,369(377);81,278(291)o 具体可参见 Vlachopoulos, Kunstfreiheit und Jugendschutz, Berlin 1996,S.159f。
[18] Wolfgang Knies, Schranken der Kunstfreiheit als verfassungsrechtliches Problem, Muenchen 1967,S.214ff.
[19] BverfGe30,173(188f.).
[20] Th. Maunz/ G. Duerig/ R Herzog/R. Scholz(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 Art.5 Abs. III, Rn.28.
[21] Horst von Hartlieb, Die Freiheit der Kunst und das Sittengesetz, UFITA Bd.51,S.24f.
[22]E. Denninger, Freiheit der Kunst, in: J. Isensee/ P. Kirchhof(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republik Deutschland, Bd VI, Heidelberg 1989,§146,S.853.
[23]BverfGE67,213(225).
[24] BverfGE 67,213(226f.).
[25] H. Mangoldt/ F. Klein/ Ch. Starck, Das Bonner Grundgesetz, Bd. I, Art.5 III, Rn.304.
[26]E. Denninger, Freiheit der Kunst, in: J. Isensee/ P. Kirchhof(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republik Deutschland, Bd VI, Heidelberg 1989,§146,S.853.
[27]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页。
[28] BVerfGE 28,243(261).
[29] BVerfGE 93,1(21);97,169(176).
[30] BVerfGE 67,213(229f.)
[31]BverfGE, 67,213(230).
[32]德国学者格罗塞曾经指出:“差不多每一种伟大艺术的创作,都不是要投合而是要反抗流行的时尚。差不多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不被公众所推选而反被他们所摒弃。”具体可参见杜强强:《宪法上的艺术自由及其限制——以“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案为切入点》,《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34]陈新民:《论宪法人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载《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88页。
[35] Afeld. Katz, Staatsrecht, Heidelberg 2005,S.303.
[36] Armin Klein, Kulturpolitik, eine Einfuehrung, 3. aktualiesierte Aufl., Wiesbaden 2009, S.79.
[37]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张慰,南京大学法学院暨中德法学研究所讲师,德国图宾根(Tuebingen)大学博士候选人。
来源:《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