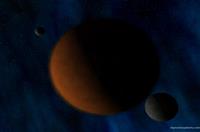
【摘要】在欧伯格菲诉霍吉斯案中,肯尼迪大法官代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撰写了支持同性婚姻合宪化的判词。面对这一引发巨大社会争议、却几乎从未在最高法院的判例法脉络中作正面处理的议题,可以想见,肯尼迪经历了艰难的法律论证过程。一方面,他尝试着从个人自治、私密关系等要素出发,搭建作为宪法权利的结婚权与同性伴侣之间的必要联系;另一方面,他也严肃回应了本案少数派法官们依托“民主过程理论”对司法权介入同性婚姻议题的愤怒指责。持平而论,肯尼迪在法律论证上的表现差强人意,但与此同时,他运用娴熟的修辞技巧在相当程度上补强了这份判决意见的整体说服力。
【关键词】同性婚姻 结婚权 私密关系 民主过程
同性婚姻的法律问题在美国已争议许久,早在20年前即有人预见到,这一问题终将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这一天终于到来。2015年6月26日,在欧伯格菲诉霍吉斯案1中,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领衔多数意见,判决同性恋者享有宪法意义上的结婚权(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marry),被诉相关州法因拒绝承认同性婚姻而被宣告违宪。我们可以说,除非反对该判决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能够最终促成修宪,否则美国将从此进入同性婚姻合宪化的时代。无论减否,本案己然载入史册。
如同其他引发巨大争议的案件一样,欧伯格菲案也是以5:4的票数定案,加入肯尼迪法官一方的是一向立场坚定的四位“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布雷耶(Stephen Breyer)、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和卡根(Elena Kagan);而提出反对意见的则是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以及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阿利托(Samuel Alito)这三位大法官。在意识形态两极化越来越延伸至司法机关的今天,2肯尼迪再次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其实,与其说肯尼迪领衔了自由派阵营,莫如说自由派法官成功赢得了肯尼迪的支持——他们并非总能做到这一点(2010年的联合公民案3即是反例)。至于为何多数意见的判决书也交由肯尼迪来撰写,相信这与他在同性恋议题上的既有立场密不可分:既然1996年的罗默诉伊文思案4、2003年的劳伦斯诉德克萨斯案5、2013年的合众国诉温莎案6的法庭意见都是由肯尼迪执笔,那么这次同性恋婚姻合宪化的“划时代荣誉”对他来讲自然也是受之无愧了。当然,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否真的可以承受,就要看肯尼迪给出的判决意见是否强有力:一方面,我们要考察其是否提供了合乎既有宪法理论、判例法规则和司法审查框架的理性化的论证;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妨品评一番其修辞上的表现——是否有精辟的措辞、雄辩的句式、高屋建领的结构布局,甚或恰到好处的煽情。因此,本文专注于本案判决书的文字作剖析,希望由此助力于对同性婚姻问题作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
一、同性恋者是否可以主张结婚权?
正如肯尼迪所说,欧伯格菲案是最高法院第一次直接处理同性恋者的结婚权(婚姻权)问题。这一问题可以沿两个互有交叠的逻辑链条予以陈述:其一,作为更一般化概念的结婚权,是否能超越异性伴侣这一传统保护对象,将同性伴侣囊括在内?其二,同性恋者依据宪法所享有的——作为公民的——一般自由,是否可以包含缔结合法婚姻关系这一具体行为?实际上,肯尼迪就是分别沿着这两条路径来试图达至承认同性婚姻这一共同结果的。
他首先指出,结婚权属于根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可以享有宪法上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所提供的保护。众所周知,美国联邦宪法上原本仅具有程序保护意义的“正当程序条款”早已被判例法注入了实体性保护的功能,这一条款可以被援引来审查某些在程序上并无瑕疵,但对实体价值、自由或权利构成限制的立法。这一司法上的创造从始至终都伴随着严厉的批评,因此其适用范围是有相当程度限定的——最高法院所达成的共识是,权利法案未予列举、但可被承认为“根本权利”的那些权利或自由可以获得“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美国宪法文本中没有出现“结婚权”的字眼,但其在司法层面上或承认为“根本权利”则是有迹可循的。肯尼迪首先提到1967年的Loving v. Virginia案7——这是一桩有关禁止跨种族婚姻法律之合宪性的案件——并强调,最高法院在这一桩案件中一致判定,婚姻是一个自由的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个人权利之一;紧接着,他援引了1978年的Zablocki v. Redhail案8,该案中被诉违宪的法律禁止己离异、但未能及时履行子女抚养费支付义务的男性再婚,而最高法院认为这构成了对结婚权的限制;他更进一步援引了1987年的Turner v. Safley案9,该案判定剥夺监狱服刑人员结婚权的法规(regulation)是违宪的……在判例法传统中,每多罗列出一宗同类判例,就多了一分寻得“正确判决”的底气。通过这些梳理工作,肯尼迪轻松地证明了,结婚权的确已在美国宪法上确立了其作为根本权利的地位。
但是,欧伯格菲案的最关键要素尚未被触及。肯尼迪行文至此,很诚实地补上了一句实情:“本院迄今为止所审理的结婚权案件都假定了婚姻关系是异性之间所缔结”。这既避免了反对意见过于轻松的反击,但也明显弱化了己方逻辑链条的延伸性——即上述先例充其量证明了结婚权是根本权利,但并不能无争议地表明同性恋者也可以主张这一权利。恰恰相反,1972年下判的Baker v. Nelson案10表明,州法对于同性婚姻之否认曾被排除在联邦管辖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反向诘问“为何同性恋者不能主张结婚权”,判例法也已经给出了不利于同性恋者的回答。因此,面对欧伯格菲等上诉人,肯尼迪对宪法判例法(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所能作的准确描述只能是:结婚权尚未被承认为可延伸至同性婚姻。
于是,肯尼迪暂时转换了跑道,强调了另外一个系列的“表达了更具包容性的宪法原则的先例”("This Court" s cases have expressed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f broader reach"),如劳伦斯诉德克萨斯案、格里斯沃德诉康涅狄格案”等。很明显,这些案件都不是结婚权案件——1965年的格里斯沃德案牵涉一部禁止已婚人士使用避孕措施的刑事法律的合宪性,2003年的劳伦斯案所审查的是一部将同性肛交行为(sodomy)入罪化的州法的合宪性——但其共同点是,最高法院依循“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审查路径,一概承认这些案件中所牵涉的个人行为(避孕和同性肛交)均属于宪法所承诺保护的个人自由(liberty)。其实,通常所谓同性恋者权利案件(gay rights litigations)在宪法诉讼的语境中一般都会具体转化为不同宪法条款之下的违宪审查操作,而不一定要以确立“作为一项单独权利的同性恋者权利”的宪法地位为前提。最明显的佐证就是,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劳伦斯案中坚称,“本案多数意见中没有哪一处文字承认了同性肛交行为是正当程序条款保护之下的根本权利……”——确实如此,该案多数意见(肯尼迪执笔)并非建基于承认“同性肛交是根本权利”,而是说,“成年人之间的私密行为作为一种对自由之行使应当获得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却伯(Laurence-Tribe)教授把这种论证方式称为“在足够抽象的层面定义权利”,也就是说,通过避开“同性肛交”的字眼,转而依赖更加抽象、一般的“自由”“私密关系”“私密行为”等话语,转化了法律论证的方式,从而更有利于为非传统权利或少数人权利争取宪法上的保护。至此,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肯尼迪特意用到“更具包容性的宪法原则”这一表述时的苦心孤诣了。他的潜台词是,既然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私密关系而私密关系可以包含性行为,那么这一逻辑为何不能用于缔结婚姻关系?当然,此处的“逻辑跨越”不见得比前述第一条路径来得轻松。如上文所述,正当程序条款的“实体化”一直受垢病,因此,这一条款中的“自由”一词的含义只能接受严格的限定,不能任意解读。婚姻权首先意味着一种获承认的法律地位,而在当代美国,附着于合法婚姻之上的更是系统性的制度架构和种类繁多的具体福利、利益,所以,要想从劳伦斯案所理解的“自由”——即同性恋者之间的性行为可免予刑事责任——推导出同性恋者有权要求其结合被承认为合法婚姻,或者说在法律上(无论州法或联邦法)扩展长久以来对于婚姻的定义,难度仍然是很大的。
肯尼迪当然看到了这里的困难,因此决定在理论层面作一些努力。他作了一句很关键的铺垫,“在定义结婚权的过程中,这些案件(包括同性恋者权利、结婚权这两个判例法轨道上的案件)己经确认了这一权利的核心要素,而这些要素是植根于历史、传统以及这一私密关系所包含的其他诸多宪法自由之中的”。12看起来,他再次运用了在劳伦斯案中使用过的技术——在足够抽象的层面定义权利。他提出内含于结婚权之中的“核心要素”,并试图在这一深层次概念与所谓“历史、传统和其他诸多宪法自由”之间建立联系。其实,“历史”也好,“传统”也好,这都是只是陪衬,肯尼迪最希望突出的是同性伴侣关系这一“私密关系”中所彰显的“宪法自由”,他甚至以复数形式(constitutional liberties)暗示宪法所认可的能够用以支持这一私密关系的自由远不止一种。至此,他已经把结婚权与一般自由结合为一个问题了,其最终答案都藏于“核心要素”之中。那么在他看来,这些核心要素是什么呢?
第一,他谈到了个人自治(individual autonomy)。他认为相关判例己表明,个人自治的概念中固有地包含了对婚姻作自主选择的权利,这几乎是一个人最为重要的选择之一。借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话来说,是否结婚和与谁结婚是人生之中关涉到自我认同这一问题的关键选择,其塑造了个人尊严。13肯尼迪还说到,婚姻的本质就是,通过这一长久的结合,两个人可以一起享有其他自由,诸如表达、亲密性和精神生活,这些对于任何人都是适用的,不管其性取向为何。尽管这一说法遭到斯卡利亚戏谑式的嘲弄,14但无可否认,经由获认可的婚姻以及通过婚姻得到的那些“好处”,同性伴侣将赢得更多的尊严。事实上,从同性恋者对于婚姻这一向来将其排除在外的“社会制度”的追求可以看出,同性伴侣关系——至少是严肃地追求婚姻关系的那些伴侣——试图在最大程度上靠近、模仿和遵循既有的婚姻关系所包含的那些特质、标准、模式或价值,其试图作出一项重大的自主选择。这里当然不能否认同性恋者基于其与异性恋者在最低限度上的差异而产生的对于个人自治之内涵的不同理解,但关键在于,这些不同是否足以否认同性恋者的自主选择所应获得的承认(recognition)。
肯尼迪没有正面回应托马斯大法官基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二分法而提出的质问,后者坚持认为个人自治意味着与政府完全隔绝,所以同性伴侣关系这一社会性的事实就已经是个人自治的实现。从判决意见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在肯尼迪大法官看来,即便可以从观念上精致区分因政府之克制而享有的个人自由(freedom from governmental action)和因政府之承认而享有的个人利益(entitlement to governmental benefits),但就结婚权而言,这里体现的个人自治从来都包含了政府最低限度的承认与保护,如颁发正式的婚姻关系证明文件、创制必要的规则以解决某些由婚姻关系引发的法律争议(如财产、子女抚养等)——这当然就会“占用”“耗费”一定的公共资源,
可是这难道不是无需赘言的常识吗?托马斯以一种极端古典主义的笔调宣称,宪法上的自由所能容纳的“婚姻”的最大限度仅仅是,政府不对其施加任何物理上或人身上的限制,而绝不包括来自于政府的“承认”和 “利益”,并且说,这就是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 )、洛克(John Locke)和美国制宪者们一代所理解的“自由”。先不论这种近乎知识考古学的原旨主义进路从来都不过是美国最高法院内“哭得最响亮的孩子”而己,其对于“承认”的排除已彻底偏离关于正当程序条款的基本共识。
如果按照这种理解,婚姻权系列判例中的大多数就根本算不上是宪法案件了,因为几乎没有哪一宗案件是在结婚权的概念中剔除了“承认”的。所以,如果作为宪法权利的结婚权还有任何意义的话,必然同时包括免予千涉的自由和获得政府承认的资格(entitlement to governmental recognition)。也就是说,异性婚姻与同性婚姻的差别待遇不可能建立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相区分的基础上,同性婚姻并不会向政府索取更多,这也不应成其为被宪法拒绝的原因。由此可见,托马斯看似在讨论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但其实从现时的判例法角度来看,肯尼迪确实没必要作专门回应。
第二,肯尼迪认为,同性婚姻包含有与异性婚姻一样的私密关系,因而可以主张结婚权。他认为此前的判例法已经表明,“结婚权之所以是根本权利,在于其支撑了一种‘二人’之间的联结,而这种联结关系对于个人的重要性是超过了任何其他一种关系的”。15他在表述婚姻关系时特别以“二人”关系(two-person union)代替“夫妻关系”,当然意有所指。他进一步说,劳伦斯案已将同性伴侣在性方面的私密关系去罪化,而最高法院在当时就指出,“对于一种持久的关系而言,性行为只是其中一种要素而己”,16因此他认为,自由不应止于此——潜台词就是,缔结婚姻才是“对自由之承诺的完全兑现”。
婚姻关系的一大本质特征确实是其私密性,但从劳伦斯案延展开去时,肯尼迪始终没有交代清楚同性私密关系如何从保护私密空间里的性行为扩展到承认一种——与异性婚姻一样的——基础性的法律关系。更为尴尬的是,肯尼迪在此处有作循环论证之嫌疑:首先,他的论证任务本来应该是凝练出宪法在给予同性恋者之私密关系以保护时所体现的“核心要素”,可现在却直接将这一“核心要素”称之为私密关系,相当于什么也没有证明;其次,如果说他的意思是婚姻关系是一种私密关系、因此私密关系应该被认可为婚姻,那也是漏洞百出的——当然不是任何一种私密关系都可以或有必要被承认为“婚姻”的。肯尼迪真正需要证明的是,如果异性婚姻所体现的私密关系有任何值得宪法保护之处的话,同性婚姻也包含有几乎相同程度、相同质素的这种关系,以至于不存在有说服力的理由可以支持一种本质性的区别对待。遗憾的是,判词在这一方面始终语焉不详。
除此之外,肯尼迪大法官还谈及婚姻权对于保护儿童与家庭、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他提醒我们,鉴于不少同性伴侣在事实上养育了子女,将他们排除在合法婚姻之外会对子女造成消极影响,这就背离了婚姻权的目的。而同性伴侣无法获得合法婚姻关系将导致这一伴侣关系处于不稳定之中,而这本来是婚姻制度意图避免的。毫无疑问,这两方面的论点如果成立,对支持同性婚姻这一结论会很有帮助,但这两个论点非常依赖于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统计和研究所提供的证据,并不是纯粹依靠规则演绎或法理论辩就可以达成一致的。肯尼迪没有在判词中引用足够的证据,因此这一段的文字给人的总体观感就是,理论抱负虽不小,实际论证效果却差强人意。
二、“民主过程”作为证成根本权利的首要管道?
美国最高法院的内部运作方式决定了大法官们在提笔撰写判词之前就知晓彼此之间对案件的大致态度,因而在判词中呈现出同时态的彼此回应与点评是很常见的。如同很多涉及根本权利的案件一样,欧伯格菲案的反对派大法官(如罗伯茨)极力倚重的一个观点就是,法庭并非议决一项非传统权利的合适场域,这类议题应当交由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去解决,也即民选议员所组成的国会(或各州议会)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承认某一项新兴权利。这就是所谓“民主过程理论”。
肯尼迪对此给出了果断而明确的回应。他指出,宪法虽承认民主过程是容纳婚姻制度(不止于结婚权)之变迁的合适管道,但前提是这一管道不得剥夺根本权利。“宪法体制的运行机制是,个人并不是必须等到立法者采取行动之后才能主张一项根本权利”。他援引著名的巴内特案17的判词,指“宪法的本意是,将某些议题从政治争议的纠葛中抽离出来,置于多数人和政府官员力所不及的地方,从而成为法庭可予以适用的法律原则”。不必高估这些论述的原创性,这不过是对联邦党人思想的再次呼应与确证罢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说,“司法完全独立,是限权宪法的独特基本内容。据我理解,限权宪法,是一部对议会的立法列出特定例外的宪法……要维持这些限制,除了通过法庭这个机构,没有别的办法。法庭的职责,在于宣布所有违背宪法公开旨意的立法无效,没有法庭的这项功能,宪法为公民保留的特定权利和特权,就会变为一纸空文”。18在他看来,司法机关就是处理例外情况的合适机关。民主的高潮、狂妄与专横,是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之后、联邦制宪之前的深刻体验,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曾把弗吉尼亚州众议院斥为“173个暴君”19,因此,在一个己实现代议制的地方,民主是一种必须予以驾驭、疏导和缓和的力量。若反对意见只是在抽象层面主张民主过程理论来批判多数意见的司法冒进,则所引发的反驳将是同样有力的。毕竟,宪法作为遏制多数、保护少数者权利的制度设计已经是理论常识,那种诉诸司法机关的非民选性的说法恐怕只有“第一眼吸引力”。或者说,民主过程理论本身也必须将某些恒常的原则、价值予以消化之后,才能在有限的论域内捍卫其主张。
第一,民主过程理论假定,民主过程能够得出更恰当的结论,但有些议题即便经历长时间的公共辩论也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如果民主过程的最终决定只能表现为立法机关中多数相对于少数的微弱票数优势的话,那么这看上去又比“5:4”好多少呢?同性恋者永远都是人群中的少数派,很难在简单多数决的决策架构中赢得优势;与此同时,他们事实上又不可能隔绝于“多数人”的社会而生活,因此哪怕是形式意义的“隔离但平等”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得他们陷入一种选项很少的处境。其实,司法过程作为对争议问题的理性展开的意义被低估了。实际情况是,阅读过诉状、考察过法庭之友意见书、全程参与口头辩论并与出庭律师直接互动、最后经过内部会议的讨论之后,一名大法官会比一名议员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同性婚姻这一议题。不论赞同或反对,法官的决定起码是一个基于论证的结论(a reasoned judgment)。由此看来,民主过程是否比司法过程更有可能接近“正确”答案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民主过程有其成本,而对该成本的负担却不见得是均衡的。颇为讽刺的是,在同性婚姻是否应当合宪化的辩论中,其中一方是其权利从来无遭受侵害之虞的人,而另一方则是苦苦争取这一权利的人,若辩论无限期进行下去,对于前者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这就使得同性婚姻的议题与是否应当提高消费税、是否应当开采近海油田、是否应当增加对公立大学的财政支持等有着明显区别。欧伯格菲案的部分当事人实际丘在为争取对其过世伴侣的遗产继承权而努力,司一见很多抱有婚姻理想的同性恋者终其一生也等不来一个“民主决定”,这种时间成本的不公平分配显然己经伤害到民主过程本身的正当性了。
因此,当下的关键问题是,在一桩具体的违宪审查案件中,相关权利能否被证立为根本权利。假如它被无争议地接受为根本权利,罗伯茨自然也不会坚持民主过程理论,根据现有的违宪审查框架,此时将启用严格审查标准来评估被诉法律的合宪性。但这就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即结婚权是否算作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根本权利。很显然,肯尼迪与保守派大法官之间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当然,肯尼迪绝不是否定民主过程的价值:与反对意见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很不幸地中断了本已方兴未艾但未臻成熟的公共辩论不同,肯尼迪认为截至目前的公共辩论已经足够——超过100份的法庭之友意见(amici)已经呈现了来自政府机构、军队、商业机构、工会、宗教组织、执法部门、市民组织职业团体以及大学等社会各方面对此议题的看法,因此己经到了在宪法层面上拿出解决方案的时候了。如他所说,在最高法院接手本案之前,已有大量同类案件诉至联邦的各个地方法院和上诉巡回法院,然而终审判决的缺失使得这一极端重要的法律规则处于未定状态——这是不宜持久的。既然相关的下级司法意见已经足够多了,那么最高法院也就无需再等待了。20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评价肯尼迪大法官对于民主过程理论的处理:(1)在判例法层面,他实际上坚持了一项包括罗伯茨、斯卡利亚等人在内亦不会否认的原则,即根本权利将获得最严格的宪法保护或者说采用严格审杳标准,民主过程的决议(即立法)仍是被审查的对象。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自由派法官认为不能拘泥于历史传统或所谓“原旨”来认定(identify)根本权利,而保守派法官则坚持权利的根本性必须建基于其历史传统中的根基(deeply rooted in the history or tradition of this nation );(2)在宪法理论层面,肯尼迪则采取了一种灵活的态度来安置最高法院与民主过程的关系:即便对根本权利而言,最高法院同样可以全盘考量公共辩论的进程、结构、质素以及可能的结论,甚至可以理解为最高法院以其特定身份参与到了这场公共辩论当中——如果主流民意恰好站在他们这一边,那就更好了(本案正是如此)。当然硬币总有另一面,这种务实的、灵活的处理方式必然包含着对原则性和一致性的些许牺牲:如果说原旨主义者(如斯卡利亚)保持了其“根本权利理论之一贯性”的话,那么肯尼迪这样的大法官则始终在作理论闪躲,既不愿对民主过程的决议照单全收,也绝不会愚蠢到拒斥民主过程——万一对自己有利呢?
三、作为法律论证的修辞——绝非文辞炫技而已
判例法传统中,判决书的论辩性常常隐含于其文学性当中,重大争议案件的终审判词尤其如此。我们大抵可以这样理解,判词本身即是一件文学作品,论证即修辞、修辞即论证。也许是因为同性婚姻权固有的逻辑困境,也许是因为肯尼迪恰是一个喜好作文辞修饰的法律人,欧伯格菲案的判决意见处处展现了文学语汇和法律语汇的交替与交错。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不乏精彩段落。
在判词的第IIA部分,肯尼迪首先回顾了婚姻制度的历史,承认截至目前的普遍理解仍是将婚姻视作异性伴侣之间的结合;但他话锋一转地指出,“上诉人承认这一历史,但认为就当前的案件而言,历史的车轮不可停止于此。若他们的意图是贬低婚姻的观念或其存在的价值,那么他们的诉求将会完全不同。但那绝不是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他们所提出的主张。相反,支撑上诉人之法律主张的是婚姻一以贯之的重要性。他们说,这是唯一的重点。与试图贬低婚姻之价值恰好相反,上诉人之所以为自己争取婚姻,就是因为他们尊重且渴望婚姻所带来的权利与责任。而他们不可改变的天性己决定了,同性婚姻是他们通往婚姻这一庄严承诺的唯一可行道路。”21,了解到会有人基于保护传统婚姻的价值而反对同性婚姻这一新形态(如阿利托大法官),肯尼迪此处极力褒奖了欧伯格菲等上诉人对于婚姻的真诚期待。确实,不论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否会对坚持传统观念的人士形成冒犯,或是否会给既存的异性婚姻带来损害,
我们似乎不能否认寻求合法婚姻的同性恋者的这一追求的严肃性,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赢得大法官们最低限度的同情。
在判词第Ⅲ部分对最高法院的婚姻权判例进行梳理之前,肯尼迪特意埋下了一个论证伏笔,即法院应当以何种态度来回应基于根本权利的宪法保护请求。他深知,无论是从结婚权作推导,还是从正当程序条款下的一般自由作推导,终究要对“同性恋者能否结婚”这一议题表态,而这就是在创建新的宪法权利。于是他说,“对根本权利予以认定并给予保护从来都是宪法解释这一司法职责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一职责并没有被简化为任何公式;相反,这一职责要求法院去做的,是在认定个人的根本利益——足够根本以至于国家必须予以尊重——时提供基于说理的判决(reasoned judgment)。这一说理过程要受到诸多方面的考量的指引,而这些考量在分析其他宪法条款时也是同样相关的,它们设定了宽泛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要求。历史和传统的确指导并规限了这一分析过程,但并没有设定其终极边界。这种分析方法既包含了对历史的尊重,又确保我们在向历史学习的同时并不会陷入‘让过去统治现在’的局面”。22所有人都知道这段话是说给谁听的,这几乎就是自由派法官在根本权利立场上的宣言书啊!肯尼迪为了给同性婚姻权的论证留出足够空间,不惜连续使用含义宽泛同时也难以反驳的词汇,比如“基于说理的判决”“分析其他宪法条款时同样相关的那些考量”23“宽泛的原则”等。试想,斯卡利亚也好,托马斯也好,或者罗伯茨也好,谁又能否认这些显然正确但似乎又什么也没说的观点呢?我们千万别忙着抱以轻蔑的微笑,这些修辞性的铺垫绝不是白费功夫。以这些抽象语汇为基础,往前走出的任何一小步都可能是对于权利证成的直接推进。这种积趾步以至千里的语言妙用,如不是长期浸淫于判例法的思维与训练当中,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习得的,肯尼迪法官给出了一个很漂亮的示范。
如果说上述文字确实修辞性太多,以至于拖累了判决意见的论理性,那么接下来,肯尼迪则适时地展现了其法律论证范式之内的修辞技巧或者说论辩技巧。反对意见提出,最高法院于1997年审结的格拉克斯堡案24已表明,“对于根本权利的描述应当是谨慎的”,欧伯格菲等人并未主张结婚权,而是同性恋结婚权(right to same-sex marriage)——言下之意,同性恋结婚权是不同于结婚权的另一种权利,尚未被宪法接纳为根本权利。肯尼迪反唇相讥地说,"Loving v. Virginia案的当事人并未主张‘跨种族婚姻权’;Turner v. Safley案的当事人并未主张‘狱中同居者婚姻权’;Zablocki v. Redhail案的当事人也井未主张‘负担非监护关系子女抚养费之离异男性的再婚权’。与此相反,以上每一宗案件对婚姻权的考察都是在其完整意义上进行的,法庭所需要做的就是评估一下是否存在足够的理由去把相关群体排除在这项权利之外。”从根本上讲,法律概念的功能就是提供必要的涵盖性、包容性,以便用简练的语言描述一系列具有某种共性但必然不尽相同的对象。假如言论自由权必须在宪法上被分别定义为发表街头演说的权利、家中闲聊的权利、教师授课的权利、商务谈判的权利、远程通话的权利、广告营销的权利……那么不但立法技术上不能承受,更将从根本上颠覆法律体系得以被建构的方式。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轻易地忽略掉“谨慎小心地定义权利”这一警示,而是说,在权利可能被定义的不同抽象层面之间,始终存在着论辩的空间。肯尼迪在此处的用意很明显,即强调结婚权的一般性以掩藏其主体上的限定性。这至少不是一个失败的论述。
但通观全篇判词,肯尼迪真正在逻辑上直接回应了同性恋者为什么应该享有结婚权这一问题的,是一些散落在各处的,或隐或显地提示我们留意社会观念变迁的短小语词,比如“新观念”(new insight) 25“对于宪法规范如何定义自由的更深刻理解”( a better informed understanding of how constitutional imperatives define a liberty) 26 “或许长久以来,将婚姻限定于异性伴侣之间看上去都是自然且公正的,但现在,这一做法与结婚权这一根本权利的核心含义之间的冲突己很明显”( The limitation of marriage to opposite-sex couples may long have seemed natural and just, but its inconsistency with the central meaning of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marry is now manifest) 27,还有“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在当下就看到不公正——这就是它的特点”( The nature of injustice is that we may not always see it in our own times)28。这些文字反而让读者有干脆利落的感觉:时代变了,潮流变了,对宪法的理解也应当跟着变了。尽管有四位大法官不同意这一点,但汹涌的民意已经替肯尼迪作了背书。
【注释】
黄明涛,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
1 Obergefell v. Hodges,576 U.S._ (slip opinion)(2015),以下简称欧伯格菲案。
2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在重大争议性案件中的判决投票形态越来越呈现出“依意识形态而站队”的特征。目前,在9名大法官当中,被认为明显归属于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法官在人数上基本势均力敌,所以判决投票结果常常出现5:4这样的“险胜”(或“惜败”)局面。
3 Citizen United v. FEC,558 U.S.310.(2010),即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在这宗投票比数同样为5:4的判决中,肯尼迪与四位保守派大法官一道组成多数意见。
4 Romer v. Evans,517 U.S.620(1996),科罗拉多州通过一项州宪修正案,规定不得对同性恋者提供法律上的优惠待遇、少数人地位、性取向歧视诉讼请求权等。联邦最高法院依据宪法平等保护条款裁定其违宪。
5 Lawrence v.Texas,539 U.S.558(2003),本案裁定一部将男同性恋者的鸡奸行为入罪的州法违宪。
6 United States v.Winsor,570 U.S._(slip opinion),本案裁定联邦法律《保卫婚姻法》违宪,该法在联邦层面拒绝承认州法认可的同性婚姻为合法婚姻。
7 338 U.S.1 (1967).
8 434 U.S.374(1978).
9 482 U.S.78(1987).
10 409 U.S.810(1972).
11 Griswold v.Connecticut,381 U.S.479(1965).
12判词原文为:“In defining the right to marry these cases have identified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hat right based in history, tradition, and other constitutional liberties inherent in this intimate bond."。
13 Goodridge,440 Mass.,at 322,798 N.E.2d,at 955.
14斯卡利亚大法官针对肯尼迪的这一论述反讽道,”如果私密关系算是一种自由,人们大概会说婚姻剥夺了,而不是扩大了这种自由吧”。参见576 U.S._(slip op.,at 8)(Scalia,J.,dissenting)。
15 576 U.S._(slip op.,at 13)旧pinion of the Court).
16 539 U.S.,at 567.
17 West Virginia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319 U.S.624(1943),本案裁定,对于其宗教信仰禁止向国旗敬礼的学生而言,公立学校如强制其敬礼,则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条款。
18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詹姆斯?麦迪逊、[美]约翰?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536页(第78篇)。
19 [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汝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9页(弗吉尼亚笔记)。
20 576 U.S一(slip op.,at 23)(Opinion of the Court).
21 576 U.S.-(slip op.,at 4)(Opinion of the Court).
22 576 U.S.-(slip op.,at 10-11)(Opinion of the Court).
23原文为,"the same consideration relevant to analysis of other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24 Washington v.Glucksberg,521 U.S.702(1997).
25 576 U.S._(slip op.,at 7,11)(Opinion of the Court).
26 576 U.S一(slip op.,at 19)(Opinion of the Court).
27 576 U.S._(slip op.,at 77)(Opinion of the Court).
28 576 U.S._(slip op.,at 11)(Opinion of the Cou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