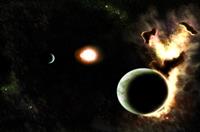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多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以主张“国家中心论”而著称的“回归国家学派”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和不断壮大①。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国家建设为核心主题的国家理论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在该研究领域中,国家建设的模式问题由于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意义而备受学界的关注和青睐。本文在相关研究成果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概括出国家建设模式的一般类型:阶级建设国家模式、军队建设国家模式和政党建设国家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对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建设模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并对政党建设国家模式的内在逻辑和转型等问题进行尝试性的回答。
一、国家建设模式的类型:三种模式涵义及其比较
在讨论国家建设模式之前,有必要对现代意义上国家和国家建设的涵义进行界定。韦伯曾指出:“国家是在一定区域内的人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区域之内——这个‘区域’属于特征之一——要求(卓有成效地)自己垄断合法的有形的暴力。”②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①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7页。)。而查尔斯蒂利则明确指出:“国家是这样一个组织,它占据着明确的疆域、并且控制着疆域上的人口,从同一疆域上的其他组织中分化出来,它是自主的、中央集权的、结构分化的组织。”(②Charles Tilly 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p.70.)由此可见,同传统国家相比而言,现代国家具有民族国家、民主国家、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成员等多重身份属性。
综合相关文献,我们可以从推动国家建设的支撑性力量或主导性因素的角度将上述多元化的道路概括为下列三种类型。
(一)阶级建设国家模式
这一模式认为,在传统国家中存在、孕育或萌生出来的社会阶级力量对现代国家建设具有根本性意义。正是在这些社会阶级力量的主导、积极推动和互动作用下,传统国家通过不同道路和方式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最终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换言之,该模式强调内生于传统社会中的原有阶级或新阶级是国家建设的支撑性力量,原有阶级力量和新阶级之间的此消彼长和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实际上就是传统国家不断解体或转型的历史过程。从本质上讲,这种模式属于“社会中心论”的理论范式,它认为社会中的各种新旧阶级、阶层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一定的阶级结构,对建构现代国家的组织、价值和制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观点是由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提出的。在该书中,摩尔认为在17-20世纪之间,由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演变过程中,不同国家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并分别走上了三条不同的道路:英美的自由民主道路、德日的法西斯道路和俄中的农民革命道路。他认为仅仅用工业化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国家所发生的政治变化,解释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关键在于不同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及其相应的阶级结构。“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影响。”
(③ ④ ⑤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前言,第2页。)也就是说,土地贵族、农民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组合模式的变化和转换,直接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路径以及对现代国家建设道路的最终选择。一般认为,该模式适用于一些社会内部新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和具有很多互动的早发现代化的国家。
以英国为例,摩尔认为它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是通过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来开辟的。“这类革命的关键特征,是兴起了一个有着独立经济基础的社会集团,它摧毁了来自既往的对于民主资本主义的种种阻碍。”④他认为,虽然城市中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为革命提供了主要动力,但是商业资产阶级所找到的盟友和遭遇的敌手对现代国家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最终,在以商人阶级为代表的社会阶级力量的主导下,英国的资本家们“消除了内部阻碍贸易的障碍,确立了统一的法律制度,以及现代货币制度和其它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政治秩序开始合理化,现代型国家在不长的时间里诞生了”⑤。因此,摩尔所谓的“从暴力革命到渐进主义”的英国道路最终建构起了一个现代自由民主国家,成为后来其他后发国家推动现代国家建设所借鉴、模仿的成功榜样。
(二)军队建设国家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是指处于后发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传统国家或专制国家在军队领袖或军官集团的领导下,最终建设起来一个军人政权或者由军人政权转型为民主的现代国家。“毫无疑问,军队是国家组织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第三世界,军事权力这样一种‘令人生畏的冷酷的力量’,其无言的存在与‘发言’的存在始终制约着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⑥陈明明:《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这实际上指明了军队或军事力量同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认真对待军队力量和军人集团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单而言,本文的“军队建设国家模式”强调的就是作为一种高度组织化力量的军队全面介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用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控制既有国家政权、以军人来统治和管理国家与社会。它既可能形成一种长期持续的军人政权格局,也可能是在短暂的军人政权统治后还政于民,逐渐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无论如何,这种模式认为:相对于其他力量而言,军队或军人集团在缔造一个新国家、保障秩序和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进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正如亨廷顿所言,“军事制度和军人政治化的程度,是国内政治组织脆弱和文职政治领袖无力处理国家所面临的基本政策问题的一个函数”(①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军队建设国家是在一种组织资源匮乏、国家治理相对失效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应对措施,军队力量对国家和人民所特有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对暴力资源的有效控制都使得这种应对措施可以成为现实。尽管军队不是常态化的主导或支撑国家建设的力量,但在某些特别时期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力量。在观察第三世界的国家建设历程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许多传统国家的转型情况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军队建国模式具有一定普遍性和解释力度。
这一模式认为,作为一种轴心力量和现代国家基本要素的政党对国家建设具有直接决定性意义和作用。“从国家与社会组织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个支撑的力量存在……缺乏了基本支撑力,任何社会都无法实现自我转换,其结果只能是自行崩溃。”(①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这一逻辑对于一个传统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而言同样如此。在政党建设国家(简称党建国家)模式中,政党先于现代国家而存在,在面对传统国家的严重治理困境或总体性危机时,政党可以凭借其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取代传统社会的官僚制,通过其强大的组织网络去动员整个社会,建设一个以政党为轴心的现代国家。
必须看到,党建国家模式中建立的国家虽然具备了集权化、渗透性、组织性等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但由于政党在国家大厦中的轴心地位及其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导致这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政党国家。这种国家建设模式的逻辑是:党在国先、以党建国、国家政党化、以党治国、党国同构、党国一体。因而在其运行过程中就面临着政党全能化和国家制度僵化、精英治理和政治制度化的冲突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使政党国家进一步的转型面临诸多障碍。
可以说,该模式主要适用于20世纪以来的后发展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例,布尔什维克党采用“党的干部委任制、政委制、对口管理制,把军队、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了比俄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的国家组织体系即政党——国家体制,从而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国家行政组织”(①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6月夏季卷,总第27期。)。由此可见,正是一个具有高度整合和动员能力的列宁主义政党的出现,使得风雨飘摇中的沙皇俄国被有效地重新组织了起来,俄国也最终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工业国家。在这一国家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政党无疑是轴心力量,它为沙皇俄国转型为一个现代政党国家提供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效的意识形态和具有高度整合能力的组织网络。可以说,没有一个坚强有效的政党(特别是列宁主义政党),一个具有现代性取向和特征的国家就难以被缔造出来。这是我们分析政党建设国家模式时必须注意到的基本事实。
(四)三种模式的比较分析
在厘清三种国家建设模式内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简要的比较:一方面,这三种模式最明显、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推动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不同,主导力量的不同导致最终建设的国家形态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在阶级建国模式中,不论是资产阶级(如英国)还是官僚阶级(如德国),它们都是这些社会中的主导性阶级力量,掌握着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而且具有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强烈意愿和能力。在军队建国模式中,军人集团在传统国家秩序混乱、治理失效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承担起建设新国家和新秩序的时代任务。在政党建国模式中,政党无疑是居于轴心地位的政治主体,政党凭借其在价值、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强势力量,将传统国家改造为政党国家,也具备了许多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每一种模式在具有某些共性的同时,都蕴含着自身独特的政治逻辑。阶级建国模式的内在逻辑就是:在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中各种新旧阶级力量之间的互动和一定的阶级结构会对国家建设产生决定性意义。这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阶级成长和阶级结构变迁同现代国家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军队建设国家模式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对特殊的国家发展道路的一种体制性选择,这就意味着“军人政权的成因与特征不应或者说主要不应从军队内部的结构规则来寻找,而应从军人政权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寻找”(①陈明明:《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而政党建设国家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些平铺化的社会面临崩溃和转型危机情境下的必然选择,政党因其特有的组织、动员和整合能力以及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而承担起了推动国家转型的历史使命。
可以看到,这三种模式是在对世界众多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的概括,因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一定的适用性。当然,每一种模式因其自身的特殊逻辑而分别适用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政治情境下的国家。例如,阶级建国模式在一个新兴阶级力量薄弱、平铺化和缺乏轴心力量的社会往往是不适用的;军队建国模式在一个阶级力量发展比较成熟和社会结构比较分化的社会也是难以实行的;政党建国模式在缺乏集权统治和强大政党领导的社会也是无法想象的。不过,笔者也承认,这三种模式并不能解释国家建设所有可能的情况,肯定还有其它模式如通过宗教力量建国的情况。本文提出的三种模式只是在具有典型意义和相对普遍有效解释性的情况下才具有模式的价值。
另外,阶级、军队和政党这三种力量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对三种模式的界定主要考虑的是居主导性地位和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力量。事实上,任何国家的形成过程都不是单一因素在起作用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实际上涉及到“历史合力论”的命题。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
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以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国家为例,“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种说法本身就表明了军队、政党和国家之间存在的密切而直接的关系,即中国共产党是在依靠军队力量和军事斗争的基础上最终建立起新中国的。回顾历史,三湾改编中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群众的重大问题;古田会议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这就是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就表明了政党牢牢控制着军队,是政党力量而非军队是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轴心力量。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国家建设模式是党建国家模式而非军队建国模式。
二、中国国家建设模式的选择及其内在逻辑
任何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其走向现代国家都不能脱离其自身特殊的历史和国情,这对于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历史虽然不能完全决定这些国家的现在与未来,但其深层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影响往往直接作用于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精神结构、生活结构和治理结构……在任何社会,政治都会对社会发展起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由于其基础结构不同,这种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也就不同,因而,也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社会建设现代国家的基础与逻辑。在中国,这种影响是比较明显的。”(①林尚立等:《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从帝国体系迈向现代国家的历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和逻辑的指导下进行的。
(一)阶级建设国家存在的先天缺陷
帝制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下的平铺化社会,在这样的文明成长的环境下,国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及其构成的主体官僚士绅的统治与治理是一个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而统治与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帝国的分合。近代中国面对现代化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传统的官僚精英主导的帝国体系无法超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鸿沟,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而成为一个全面涣散的原子化社会。结果,在孙中山等革命精英的积极推动下,辛亥革命终结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国体系,开启了以民主共和为取向的建设现代国家之路。可以说,中国最终迈向现代国家是以传统的帝国体系的全面崩溃为历史前提的。
由于传统中国社会是在帝国体系下被政治整合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自身缺乏强大的阶级、自组织力量和机制来实现自身的整体整合。因而,这样的社会的组织、运行和有效发展依然对国家、政府和政治精英有着强烈的依赖性。这就决定了传统官僚帝国崩溃以后,新的国家形态难以有效建立起来。所以,“要想在帝国体系的废墟上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首要任务就是形成能够担负起这样的历史重任的社会主体力量”(①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然而,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是一个以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但却是一个平铺化、无阶级的社会。钱穆曾指出:“这一种社会之最大缺点,则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既无世袭贵族,又无工商大资本大企业出现,全社会比较能往平等之路前进。”(①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页。)梁漱溟认为,“可以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其农工生产都不会演绎出对立之阶级来。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于土地分配”(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这就告诉我们,帝国体系下的社会由于缺乏主导性阶级力量的支撑,也缺乏推动整个社会朝着以民主共和为取向的现代国家转型的阶级结构,因而就必然失去了自我转型的阶级基础和政治能力。“随着王朝的衰落,共同的政治中心和晚期帝国有限的稳定让位于现代斗争形式和阶级冲突。”(①魏斐德:《中华帝制的衰落》,邓军译,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40页。)在面临西方冲击和内部矛盾的情况下就产生了总体性危机,曾经强大无比的帝国体系难以实现有效的转型而走向崩溃就是历史的必然。所以说,传统社会阶级力量的先天缺陷,决定了中国社会采用阶级建设国家模式是行不通的。
(二)军队建设国家的歧路和失败
在阶级建设国家存在先天缺陷的背景下进行现代国家建设,首先建设的就是国家权力核心,以便树立起一个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转型的政治权威和轴心力量。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最后的政权却落入了北洋军阀袁世凯等人手中。袁世凯死后,由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来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路军阀以省割据导致分裂。据陈志让研究,北洋和南方军阀变成军阀的过程是在义和团之后,中央势力渐趋微弱,地方势力抬头,到清室退位、民国成立时期。由于存在派系的分裂和地区的分裂,这个新兴的军-绅政权不能够统一中国。所以,他认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军队不是现代国家的军队,军-绅政权也不是现代国家应有的政权”(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事实上,在孙中山进行北伐和蒋介石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基于政治合法性价值的行为考量,“普遍地赞成国家统一,使所有军阀的合法性产生了危机,他们陷入了既希望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又无法否认国家统一原则的矛盾之中”(①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虽然最终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但由于其偏离了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国家建设道路,过分强调以军队为中心建设国家的重要性,使得国民党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强大、统一和有整合力的政党,可以说是走上了一条歧路。王奇生在对1931年以后国民党党治结构的研究中提出:“全代会、中常会和中政会之所以变得无足轻重,人数太多只是一个表面因素,实则党权已为其他力量所侵夺取代。而侵夺党权的力量,不外乎军权与政权,其中主要是军权。”“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依然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①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170页。)易劳逸也认为:“军队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这一政权的政治机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既没有建立坚实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创造出强有力的自主性……在整个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它们一直被军队的领导和政策需求所笼罩。”(①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这就说明了军队在当时建设国家的进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事实上,军队在国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同蒋介石重军轻党、过分迷恋军权的军治理念是有直接关系的。重军轻党在很大程度上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治和党机器组织建设的关注。这就会导致政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将整个国家推向政治军事化和社会军事化。这样也导致国民党在群众基础、党义和政治纲领以及组织和动员能力等方面都出现严重的问题,使得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看似独裁强大的国民党最终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与此同时,国民党本身是一个弱意识形态的政党,它在让军队服从党的意识形态和依靠军队将领的意识形态认同去控制军队方面(①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251页。)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同共产党相比,那更有很大的差距。此外,国民党内部存在的派系斗争、贪污腐败和纪律废弛也严重影响到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这就使得军队难以有效履行领导和推动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军队建设国家模式在中国也必然是没有真正出路的。
正如前文所述,帝国体系由于缺乏支撑性的阶级力量而走向崩溃,这就使得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国家依然面临着中心指导力量缺失的关键性问题。孙中山等革命先驱建立起了精英型政党——国民党和革命性军队,并以政党和军队等核心力量为主导,试图走一条“军政、训政和宪政”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孙中山曾指出:“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其实我们现在何尝有国?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后再去爱之”,“党有力量,可以建国”(①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393页。)。客观而言,孙中山先生构想的党建国家方案是很有远见的,也是具有可行性的。但是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过分推行以军统政、以军控党,使得国民党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政党。此外,国民党本身存在缺乏有效整合和渗透社会的能力等诸多致命问题,因而也就难以承担建设现代国家的使命和有效解决近代中国以来面临的主权、政权和民族危机。所以,孙中山开创的这条现代国家建设之路走上歧路,遭受多次严重挫折,并最终以失败告终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
我们认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最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的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最后由政党而非阶级和军队来完成的,这体现为党在国先、以党建国的特殊历史道路。通过强大的政党力量主导国家建设,然后以国家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成长,实现朝着现代文明的整体结构性的转型,这是中国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所在。汤森等人曾指出:“1911年的辛亥革命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完全不可信任的政治传统,它并未给它的继任者提供指导原则,而是导致了促使国家进一步分裂的政治真空。…… 然而,真正的权力和权威需要能对国家危机做出可靠反应的精英集团。…… 在需要新的领导和政策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威信与他们的竞争者一样好,最终还更好。中国共产党 …… 它是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代表者,并且是它未来的一个主宰者。”(①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全面开始现代国家建设的努力,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也由此开启。在这个历程中,国民党以党建国、以军建国的努力都最终失败了,而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他们“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建立了新中国, 开辟了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现代国家建设和发展历程, 并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 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内在逻辑”(①林尚立:《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实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邹谠也曾指出:“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特征,就是政党及其领袖的决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在一个更长的时期中,比其他国家更直接、更重大、更显而易见。”(①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这实际上强调了政党及其精英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突出重要性和特殊价值所在。
相对于阶级建国和军队建国模式而言,政党建国模式的优势是明显的。对于处于后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强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由于能够同时满足现代国家建设中“经济与社会对国家权威的需求”和“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后对国家民主的需求”(①参见林尚立等《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5页。),从而最终承担起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而共产党精英集团由于其在政党国家中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也必然就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核心力量。所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仅是一种意识话语和政治宣示,还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和制度变迁历程的真实写照”(①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6月夏季卷,总第27期。)。这实际上是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在逻辑的关键所在。
可以说,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政党建设国家模式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社会结构和政治精英等多方面因素形成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一模式也是对长期以来占据西方主导地位的阶级建国和军队建国模式的一种超越和发展。该模式下形成的国家形态是典型的政党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对国家建设模式进行类型划分并用它来分析和解释中国国家建设的情况,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无疑,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本来应该实现向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转型和均衡协调发展的目标。然而由于革命战争的内在逻辑和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特殊处境,中国的国家建设“不同于原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直接以民族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它是由组织严密的政党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因此,古典的国家形态转变的结果不是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而是从文化-国家转变为政党-国家。设定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那么政党-国家(party-state)就是现代国家的变异形态”(①任剑涛:《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学海》2010年第4期。)。政党-国家在一定时期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也必须看到它的内在逻辑是把政党变成国家,把国家变成无所不包的‘党国体制’,既泯灭了政党的原始机制——政党的功能高度行政化,政党偏离了政党的角色,又消泯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国家全面扩张最终吞噬了社会,反过来抽调了国家建设的物质和政治基础,导致国家政权建设的全面困境”(①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复旦政治学评论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显然,这样的政党国家形态是难以长期维系下去的,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市场化、社会利益分化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政党国家面临的困境和矛盾就更加突出,这些方面集中到一起,都客观上要求政党国家进行适应性的转型。
有学者指出:“党治国家的本质就是党建设现代国家,其使命有两个:一是全面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二是全面培育现代国家的公民。有制度、有公民,现代国家体系才有了确立的基础和运行的条件。”(①林尚立等:《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在这样的基础上思考当代中国政党国家的转型,就是要求政党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上述两个基本使命。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政党主导国家建设是必然的选择,但是这种政党主导并不是最终目的。政党主导的目的是最终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民主取向的现代国家体系,要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化发展。面对全球化条件下新的执政环境,中国共产党积极地从意识形态和组织两大维度进行“政党重建”,以保障执政地位和具备推动国家建设的能力。它主要从阶级斗争到阶层合作、从全能到法治、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内定任命到党内民主等方式进行着自身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开启了“政党国家的内部转型”(①参见David Shambaugh,?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ation,? Washington, D.C. and Berkeley, CA: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叶麒麟《政党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适应性研究》,《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显然,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动向。
客观而言,这一“政党重建”和“内部转型”的努力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积极成果,但离党建设现代国家两大使命的要求还比较远: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国家制度依然不够完善,特别是按照民主法治原则将执政党纳入到现代公共政治生活和制度体系中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另一方面,在强大的执政党一党领导和后全能主义体制下,具有现代意义的公民和公民社会的成长依然比较孱弱。这就必然导致中国现代国家体系确立的基础和运行的条件非常薄弱。这就表明推动政党国家进一步转型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如果政党国家推行的一些改革和转型措施仅仅是为了维持统治集团自身的生存,而不是进行积极主动的制度转型,那么它就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内部深刻的危机和外部的挑战,就必然会沦为“陷入困境的转型”(②Minxin Pei,?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因此,从当代中国的政治逻辑出发,执政党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积极主动地在价值、组织和制度等方面作出不断的适应性调整和积极的转型努力,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才能具有真正持续有效的轴心力量去支撑。这样的话,中国国家建设也才能真正地持续走向深化,并在调适和转型进程中最终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任务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