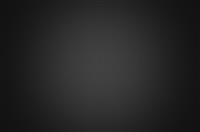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入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美国的自由主义也由传统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本文剖析了杜威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并分析了其在自由主义的理论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
就理论体系及其影响来看,杜威堪称美国新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新旧自由主义转型的旗手。台湾学者李日章指出,“如果说杜威的哲学是有时代遗迹的,那么,在今天看来,最能够表现出它的时代性的,实莫过于他的政治思想。”对于杜威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他认为,在美国的政治理论家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杜威更适于做新自由主义的代表。[①]本文将从杜威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出发,分析自由主义转型的一般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资本主义由自由放任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其自由观念也经历了一场“改革”:威尔逊以“新自由”作为施政纲领[②],罗斯福也以“四大自由”作为进一步实施“新政”的旗帜。[③]自由观念的变化反映了自由主义的变化,美国的传统自由主义正是在改革时代[④]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里转变为新自由主义。
杜威回顾了传统自由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杜威认为,洛克式的自由主义(Lockeian liberalism)混合了早期的政治思想,构成了自由主义哲学,在19世纪西方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这种自由主义阐发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所有的政府积极行为都是压制性的;它的准则是放权(hands off);政府行为只要可能就应该被限制,用以保护个体行为的自由而反对干涉其它个体在这一相同自由上的实践;自由放任的理论和政府限于立法与警察功能。”[⑤]
在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杜威抛开了霍布斯—洛克(Hobbes-Locke)的路线,而赋予斯宾诺莎—黑格尔(Spinoza-Hegel)路线以格外的重要性,试图用欧洲自由主义中对社会、对国家重要性的认同来或多或少地均衡英美自由主义过分重视个人的倾向。
杜威抨击了传统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杜威认为,“传统自由主义的道路并未臻自由之境。”[⑥]杜威批评传统的自由主义宣扬绝对主义,他认为,“这种绝对主义,这种对暂存的相对性的忽视与否认,是早期自由主义很轻易地便堕落为假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⑦]杜威认为,就自由主义的转型来看,密尔(John Stuart Mill)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旧自由主义的危机还没有明晰地显现出来时,密尔的思想就预示了这一点。[⑧]
实际上,杜威的新自由主义是传统自由主义的一个发展。杜威指出,关注自由与个人,这是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基础,这一基础仍然是无可置疑的,不然的话,新的理论就不是自由主义了。然而,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这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却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由已经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⑨]
杜威看到了生产社会化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改造。他认为,如果自由主义不准备更进一步使生产社会化,它所追求的自由将会在一段时间内迷失。[⑩]杜威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思想。他先是号召实践一种“不屈不挠的自由主义”(ragged liberalism),后又在大萧条期间进一步修正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一种激进的自由主义(radical liberalism)。这种自由主义更清晰地阐明,智慧是一种社会财富,是一种社会合作。在他看来,如果要取得进步,这种激进的自由主义就应受到尊敬。
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
赋旧词以新概念是杜威政治哲学的一个典型特点。为旧哲学注入新思考;在旧理解中加入新的要素,杜威试图赋予诸如个人、平等、自由、民主这样的概念以新的意义。正是在对传统自由主义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杜威建立了完整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一)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主体论
个人主义一直居于自由主义的理论核心,甚至有人将个人主义等同与自由主义。然而,从早期的斯多葛个人主义(Stoic individualism)到基督教个人主义(Christian individualism)再到原子个人主义(atomic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传统个人主义为传统自由主义提供了主体论的基础,而新个人主义的出现则为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准备。因此,新旧自由主义的转型首先体现在新旧个人主义的转型上。
杜威摆脱了传统自由主义孤立地认识个人的偏见,更多从共同生活的角度认识个人。他认为,个人“代表那些在共同生活影响下产生和固定的各种各样的个性的特殊反应、习惯、气质和能力。”[11]这样,杜威就在承认主体间性的同时,肯定了主体间交流的重要性。杜威否认所谓的个人权利独立地为个人所有的观点。他认为,“个人所以能有权利,全赖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国家的一分子。他的权利全赖社会和法律给他保障,否则便不能成立。这个观念是根本的观念。真讲权利的,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的组织。”[12]
杜威明确指出,人只有在他有权力的时候才是自由的;并且,只有依据整体进行活动,个体才拥有自由,这种自由因为从整体那里获得动力而得到加强。[13]为了使个体得以无阻碍地自由行动,社会、政府、制度、法律等安排必须符合与整体秩序相对应的合理性,杜威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本性”。[14]因此,杜威所主张的自由绝不等同于无限制的个人自由,而是“一种普遍的、共享的个人自由,且这种自由得到社会化的、有组织的理性控制的支持与导向”。[15]
就杜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来看,个人主义仍然是基础,但是,杜威眼中的个人已经不是那种“固定的、现成的、给予的”的个人,而是“达成的个人”,“依托于环境的个人”。他不但生活在社会中,而且,其本性更体现在集体的生活当中。因此,这种自由主义“对于有益的法律、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正面建设抱有兴趣”。[16]
(二)平等:新自由主义价值论
自由与平等是自由主义的两个核心主题。就美国改革时代自由主义的转型来看,人们在认同自由价值的基础上更强调了平等的价值。这种理论关怀不仅影响了杜威的理论体系,而且,也正是从杜威对平等的偏爱,我们可以看到杜威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倾向。
杜威看到了自由与平等这两种政治价值之间的冲突。杜威指出,自由与平等不是并立的,人们常常以为有更多的自由,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平等,然而,结果却是更多的自由“反而增加不平等”。杜威指出,种种经济界、劳动界的不平等,都是起于自由太甚”。[17]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杜威认为,应该调和自由与平等,既使自由得以发展,又使平等能够实现。
与传统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不同,杜威加强了对平等价值的弘扬。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指出,“西洋近日最重要的问题,是用国家的势力去平均社会,使不平等逐渐减少……”[18]杜威以哲学上的“存在之名”论证了每一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新自由主义的平等观。杜威一方面将平等看成是质量上的,强调个体的现实性和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又强烈指斥原子个人主义的自我封闭。因此,杜威的平等观既否定了孤立的个人主义,又向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开战。
在杜威那里,平等的信仰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贡献他所能贡献的东西,其贡献的价值应根据它在由同类贡献所组成的总和中的地位与功能来确定,而不是根据任何先定的地位。”[19]因此,杜威强调的平等仅仅意味着不能把世界看作是一种固定的序列,不论种类、等级还是程度。在杜威看来,平等是社会序列不断演进形成的平等,不存在静态的平等,也没有终极的平等模式。任何寻求终极平等的努力最终会丧送平等,从根本上阻碍平等的发展。
(三)工具民主:新自由主义制度论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与自由相比,民主更是一种手段,用于个体在国家领域中实现个体自由,通过政治参与,民主为普通个体参与国家政治程序提供了通道。
杜威更多从社会和道德的含义来定义民主,试图发展一种无所不包的民主概念。就其对民主的解释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即政治的民治主义、民权的民治主义、社会的民治主义和生计的民治主义。[20]杜威试图证明民主是一种社会行为,这也成为他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标志。杜威认为,通过民主,联合的生活能被改造为一种“伟大社会”的精神。
在杜威看来,成员利益的相互冲突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杜威认为,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这一基础上解决相互冲突的问题。也就是说,“相互冲突的要求如何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有益的情况下得到解决”。[21]杜威认为,民主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它“将这些冲突带到一个公开的场合,在那里,特殊的要求能被了解和评价,并在更为内在的兴趣的启示下被讨论和表达,而不是由其中的任何一个利益体独自地表达。”[22]
对于民主,杜威基本上持一种工具论的认识,然而,杜威的这一认识是灵活的。杜威认为,在一个基本的民主观念还没有树立的国家里,将民主表达为一种理想或是将民主视为达到理想的工具都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民主只能被当作为一种工具;将民主作为目的只是意味着一个阶级对权力所特有的攫取和保留的欲望。[23]
(四)科学与理性:新自由主义方法论
理性主义是自由主义政治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启蒙运动弘扬了理性,但却在将理性推上王位的同时以理性扼杀了个性与感情的多样性。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思想界的非理性主义甚嚣尘上,对美国思想界亦产生了重要影响。消解两种极端的倾向,重新确立理性的思维方法就显得极为迫切。新自由主义给予早期的理性概念以新的重要性,[24]强调理性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作用,“科学”与“理性”成为新自由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杜威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依据自己的理性对价值做出选择的权利;而每一个人又都能够在社会事务的处理中依据科学的方法。这就是一种“自由的知性”。“自由的知性”是杜威杜威自由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特征,在杜威那里,“一切探讨、讨论和表达都依自由的知性而进行”。[25]
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历来为人所关注。纯粹的民主只是一种个人偏好的表达工具,带有非理性、非科学的一面。在这里,杜威强调了自由理智的重要性。杜威认为,在人们心中,民主时常自然地和行动的自由联系在一起,这时,人们就有可能忘记了“为指导和保证行动自由所必要的自由理智的重要性”。[26]因此,杜威强烈反对依靠集中的强力达到目的。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造成损害,于事无补,最终还是要求助于理性的方法。
杜威强调,在研究社会哲学的过程中应该用科学的态度。他指出,“科学的方法”中可以应用于社会政治方面。”不但如此,他还坚定地认为,“吾们研究社会科学要用科学的态度,以学理帮助指导人的行为去达他的目的。”[27]事实上,正是杜威将哲学与科学应用到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才创造了所谓的“民主哲学”,杜威本人亦被奉为美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民主哲学家。
(五)积极与消极:新自由主义态度论
就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态度来看,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区别。当代自由主义大师伊塞亚·柏林(Isaiah Berlin)就此划分做了全面的论证,
并得到了西方政治哲学界如泰勒(Charles Taylor)、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等人的广泛认同。事实上,对两种自由的划分在拉吉罗(Guido de Ruggiero),甚至更早的格老秀斯(Hugo Grotius)那里就已经初露端倪了。
杜威区分了两种自由:一是选择的自由(freedom defined in terms of choice);一是行动权力的自由(freedom defined in terms of power)。在此基础上,杜威将“相互之间无阻的有效行为与选择之间的关系”问题视为自由的本质。[28]杜威指出,现在,我们有两类看起来各自独立的哲学,一种从选择本身寻求自由,另一种则从根据选择而行动的权力中寻求自由。[29]
与早些时候的英国新自由主义者格林(Thomas Hill Green)、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一样,杜威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带有明显的积极自由色彩。他指出,那些值得争取的自由,一方面通过废除那些压迫手段、残暴的法律和政府来得到保证,而另一方面,它正是“因自由而解放、拥有所有权、积极的表达权和行动上的自决权”。[30]
“民主的政治形式仅仅是人类的智慧在一个历史的特殊时期内所设计的一些最好的方法。但是他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观念作为根据的:即没有一个人或有限的一群是十分聪敏和十分良善的以致无需科别人的同意就去统治别人;这句话的积极意义是:凡为社会制度所影响的一切人们都必须共同参与在创造和管理这些制度之中。”[31]
这样,杜威就申明了民主制度的两个方面:民主制度不但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而且,处于这一制度下的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我们看到,杜威不仅强调了民主能够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且,他还强调了公民民主参与的重要性。
(六)演进:新自由主义发展论
就政治体系的发展来看,自由主义存在着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e rationalism)与演进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nalism)的两分论。建构理性主义相信,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可以借助于人的理性进行设计;而演进理性主义则认为,社会的发展是自发的,人类的理性不足以对政治制度进行设计。
杜威看到,人们总是在高谈“再造世界”、“改造社会”,但是,他认为,这些再造和改造“都是零的,不是整的”,都是“一件件的,不是整块的”。所以,他认为,“进化是零买来的”。他甚至鼓励学生说,“你们以各人的知识一点一点地去改革,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吾们理想中的大改造。”[32]
杜威并不反对激进的变革,但他又将方法与目的之间的一致性看得很重要。杜威主张,改革不是绝对主义的,而具有“历史的相对性”。杜威主张实验过程和实验的方法,力图使观念与政策同现实相符而不是相对。
杜威认为,社会变革不会在缺少权威指导的绝对自由中找到方向。杜威将稳定与变革看作两个相关的序列,提出了正确解决两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为稳定和变革划定分隔的“疆域”,而是要使两者融会贯通。[33]演进的民主需要权威来指导和调控,但这种权威又绝不是旧的权威。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杜威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成为新旧自由主义转变的吹鼓手。杜威在政治主体论、政治价值论、政治制度论、政治方法论、政治态度论和政治发展论等诸多领域均对传统自由主义均有重要的发展,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
[①] 李日章:《杜威小传》,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07页。
[②] [美]伍德罗·威尔逊:《新自由》,参见《美国读本》,戴安娜?拉维奇编,林本椿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26页。
[③][美]富兰克林·D·罗斯福:《致国会的年度咨文》,载[美]富兰克林·D·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9页。
[④] 美国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将美国内战到1890年的美国历史看作是工业化、大陆扩张和政治保守的时代,将1890年后到二战的历史称为改革时代,本文使用此称呼。考虑到延续性,本文在时间上略有出入。参见[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愈敏洪、包凡一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John Dewey,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Minton, Black&Company, 1931, p.278
[⑥]John Dewey,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Minton, Black&Company, 1931, p.283.
[⑦] [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集》,孙有中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7页。
[⑧]John 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35, p.29.
[⑨]John 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35, p.7.
[⑩]John Dewey,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Minton, Black&Company, 1931, p.88.
[11][美]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07页。
[12][美]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载《杜威谈中国》,沈益洪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13]John Dewey,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Minton, Black&Company, 1931, p.283.
[14]John Dewey,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Minton, Black&Company, 1931, p.284.
[15][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集》,孙有中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16][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集》,孙有中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17][美]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载《杜威谈中国》,沈益洪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18][美]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载《杜威谈中国》,沈益洪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19][美]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页。
[20][美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载《每周评论》第26号,1919年6月15日,转引自顾红亮:《实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1]Jonh 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35, p.79.
[22]John 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35, p.79.
[23]John 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35, p.86.
[24]John 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35, p.7.
[25] 李日章:《杜威小传》,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15页。
[26][美]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页。
[27][美]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载《杜威谈中国》,沈益洪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10页。
[28]John Dewey,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Minton, Black&Company, 1931, p.286.
[29]John Dewey,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Minton, Black&Company, 1931, p.282.
[30]John Dewey,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Minton, Black&Company, 1931, p.276.
[31][美]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页。
[32][美]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载《杜威谈中国》,沈益洪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33][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集》,孙有中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