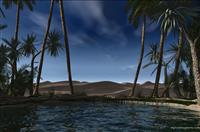一
施特劳斯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忠实拥护者,因此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严厉批评者。然而,施特劳斯并非纯粹为了厚古而薄今,也非纯粹为了薄今而厚古。施特劳斯明确强调,没有直接通往古人的便捷道路。只有深入理解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攻击及其意图,才能获得恰当理解古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施特劳斯不断要首先回到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处。
为了强调自己作为现代自由民主制的诤友身份,施特劳斯曾经说:“我们不可成为民主制的谄媚者,就是因为我们是民主制的朋友和同盟。对于民主制将自身以及人类的卓越性暴露在其中的危险性,我们不可保持沉默;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显然可见的情况:民主制将自由给与所有人,它也将自由给了关心人类卓越性的那些人。”[1] 通过这段话,施特劳斯首先表明他的批评是出于友爱,而不是出于憎恨。其次,批评理由是自由民主制自身之中蕴含着危险。除非已经认定现代民主制本身已经完美无缺,否则总需要思考它的缺陷,尤其需要思考制度本身是否蕴含着瓦解自身的危险因素。最后,施特劳斯说明了民主制的优点,它既然许诺给所有人以自由,那么它也向思考人类命运的思想家许诺了自由。在这里,施特劳斯没有点明,这个优点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它的宽容也将自由给了民主制的敌人。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表示,作为会思考的理性动物,如果拒绝倾听对民主制的批评,属不智之举。尤其需要倾听那些大思想家的批评,即便他们是民主制的敌人。[2]
施特劳斯多次表示自己是自由民主制的朋友,他的弟子也为他的这一角色一再辩护。虽然如此,他的批评姿态还是引来诸多不满。加拿大学者德鲁里(Shadia B. Drury)就断言,施特劳斯在政治上“反感”和“憎恶”自由民主制,不由自主地拥抱暴政;在思想上害怕和厌恶虚无主义,鼓吹宗教;在哲学上削弱自由平等的思想,以混杂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方式培养自我陶醉的精神“贵族”。通过这些论证和考察美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她得出结论说,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精神若合符节,其政治哲学奠定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3]
施特劳斯果真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精神导师吗?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施特劳斯对现代政治制度及其哲学的批评?施特劳斯所说的危险意味着什么?他重振古典政治哲学精神的意图是什么?要真正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考察施特劳斯思想中的古今之争,并思考施特劳斯为何重新提出古今之争的问题。
二
施特劳斯重新挑起的古今之争,也就是古今政治哲学之争。那么,古今政治哲学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争点?
首先,古今政治哲学对政治社会的起点理解不同。古代政治哲学家把有别于非常状态的正常状态(normal state)作为他们政治理论的考虑标准,而现代政治哲学家则例外和极端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或the extreme state)作为理论标准。现代政治哲学家之所以把极端状态作为理论标准,是因为他们认为,极端状态比正常状态更好地表明了公民社会的根源和真正特征。[4]在这一点上,霍布斯是一个绝佳例子。他的道德和政治理论都建立在对极端状态的理解之上。[5]非常的自然状态被确定为正常的政治状态的基础。施特劳斯本人则崇奉他所理解的古代政治哲学家,把正常的法律状态而不是把非常状态作为政治哲学的起点和标准。
其次,古今政治哲学对人性的看法不同。现代政治哲学家认为人性本恶,但是这种恶是无辜的恶。也就是说,它无涉道德之恶。为了摆脱和克服这种自然之恶,人类理性需要人为建立一个事实上的完美政治实体,并通过法律和惩罚来防范并彻底根除人间恶。古代政治哲学家则认为,人间恶是道德恶而非无辜之恶。这种道德恶的缘由恰恰是因为人性对自然理性的普遍不信任。为了驯顺这种道德恶,人类需要通过语言建立一个完美的政治实体。这个语言城邦的完美性彰显了人间的政治城邦未臻完美的事实,由此也说明了人间之恶积重难返。另一方面,这个完美城邦只存在语言之中,这个事实也表明了古典政治哲学家并不迷信人类理性能力的审慎态度。
再次,古今政治哲学对理性教育持不同态度。现代政治哲学认为人性恶属于无辜恶,可以通过理性教育来逐步克服。如此,它的方案是试图通过普世理性启蒙让世人彻底摆脱愚昧、摆脱宗教,建立一个理性的世界。现代政治哲学的理性启蒙对象是世间所有人,它相信,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而摆脱无辜恶,摆脱蒙昧状态。。这种启蒙教育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性教育,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普世教育。这种教育旨在建立理性的人类新社会,最终目标就是天下大同的理想。古代政治哲学对理性能力的态度没有现代政治哲学那么勇往直前。它对人类社会完全根据理性而生活的能力持谨慎的态度。也正因此,古代政治哲学始终把绝对的理想国家置于语言之中。由于它对人间道德恶的冥顽不灵有更为深刻的洞察,古典政治哲学对通过普世理性教育克服人间恶的想法并不乐观。[6]它所采取的教育策略是少数精英教育,试图通过结合哲学理性和政治激情,引导大多数人避恶趋善而驯顺人间的道德恶。
最后,由于对理性教育的不同态度,古今政治哲学对隐微/显白论的理解也不同。施特劳斯认为,所有真正的古典哲学家都坚持双重教诲论,并一直实践着隐微/显白写作的方式。这种传统并没有随着现代政治哲学的兴起而消失。在施特劳斯看来,至少迟至18世纪末段,仍有哲学家和思想家(比如莱布尼茨和莱辛)明确地坚持隐微/显白双重教诲,并实践这种写作的艺术。[7]只有在历史意识的兴起并主宰思想主流之后,原本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才逐渐衰落甚至消失。那么,古今政治哲学的隐微/显白论之间有没有实质分别?施特劳斯虽然没有明确区分两种隐微/显白论,但他确实指出了古今政治哲学对隐微/显白论的不同理解。由于对理性能力持审慎态度,古典政治哲学坚持认为少数和多数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因此坚持隐微的哲学真理不可能也不应该显白于天下。与古代政治哲学的审慎相较而言,现代政治哲学大胆地认为政治压迫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它希望通过理性教育的大众启蒙,也就是通过推行思想和言论的彻底自由,一劳永逸地解决哲学与政治、思想与社会之间的根本紧张问题。[8]
三
隐微/显白论方面的区别直接与古今政治哲学所持的不同文明理想相关。
近年来,已有论者注意到了“有条件的隐微论”和“无条件的隐微论”之间的分别,[9]并且区分了施特劳斯学说中的弱版本(也即现代版本)和强版本(古代版本)的隐微论。[10]后者也即古典的隐微/显白论,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绝对的隐微论。现代的隐微/显白论则是一种相对的隐微论。说它是相对的隐微论,也就是说现代政治哲学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隐藏了他们的真正观点,这种程度足以使自身避免遭受迫害便够了。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真正目的隐藏得更为隐秘,那么他们便不可能达成他们的意图:彻底根除政治迫害现象,大力推行大众教育,建立一个完全理性的公开社会。[11]
古今政治哲学对人类理想社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古典政治哲学家用语言编织出理想的国家图景,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其中,人类身体和灵魂将同臻完美之境。古典政治哲学家对此理想国家在事实上的实现并没有心存幻想。但依然将此理想树为人间政治的典范,以此提醒人类政治尚未摆脱那无可摆脱的恶这一事实。现代政治哲学家既认为无辜之恶可以通过政治法律手段来克服,便把目标转向未来,试图建立一个事实上的完美国家,也就是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霍布斯的利维坦、黑格尔的理性国家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可以理解作现代意义上的完美国家。
施特劳斯常说,现代政治哲学降低了古代政治哲学的道德标准,以实现自身的理想和目标。同时他又强调,古典政治哲学家所构想的理想国家仅存在于语言之中。恰恰因为仅存在于语言之中,较之任何现实城邦,古典理想国家都是非历史的、完美的和绝对的标准。现代政治哲学家试图历史化和现实化这个绝对城邦,使之成为人类历史的完美终结点。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现代政治哲学不得不首先降低道德标准。古代理想设想,人类身体和灵魂可以同臻完美之境。这个理想的实现前提过高,几无实现的可能性。现代政治哲学为了提高实现这种文明理想的可能性,便不得不降低古典政治哲学的标准。它放弃了灵魂方面的要求,仅满足于确保身体方面的安全。现代完美国家的首要任务在于确保公民身体的安全,灵魂方面的修养则属于国家不可随便侵犯的私人禁区。
现代政治哲学在道德标准方面的降低,一方面放弃了古典政治哲学家为人类政治生活所设定的绝对标准,另一方面为人类政治生活埋下了隐忧。一是,为了实现未来完美国家的理想,任何手段可能因此被认为是正当的。二是,既无绝对的理想标准,现实诸城邦之间便无善恶良莠之分,人类生活便处于无可救药的纷争状态。这种纷争状态就是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也就是德国虚无主义所要返回的虚无。
四
1941年,二战尚未结束,施特劳斯在美国发表了一个讲演,探讨德国虚无主义的本质及其精神渊源。这个讲演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来读。前半部分主要说明,德国虚无主义是对现代文明理想的反动;后半部分则进一步阐述,它不光是对现代文明理想的反动,而且是对文明理想本身的否定。[12] 现代文明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公平社会,建立一个彻底启蒙的光明王国。这个文明理想曾经激励了若干代的现代有识之士,至今血脉未断。然而,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这个理想曾经面对最可怕的政治挑战和最深刻的哲学挑战。最可怕的政治挑战就是自由主义政治在德国的衰落和纳粹政治的兴起。最深刻的哲学挑战就是对哲学理性原则的彻底历史化和时间化。这两股挑战力量同时出现并非完全偶然,它们共同折射了德国虚无主义的精神特征。
德国虚无主义不仅对现代文明理想——无论自由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不再心存幻念,而且抛弃了古今政治哲学共同保有的理性精神。德国虚无主义放弃了依据理性建立和追求至善社会的根本理念,也即放弃了理性原则本身。但是,德国的哲学虚无主义确有其深刻之处。它不是简单放弃或者忽视传统的理性原则,而是勇敢地对它进行了历史解构。根据这种解构,传统的理性原则不过是作为时间的存在,是存在的历史发生。在德国虚无主义那里,现代文明理想已经失落,理性文明原则本身也已被历史地解构了。
德国虚无主义自身的根基何在?回到虚无。准确地说,回到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当代政治理论最完美地体现这一点的是施米特的政治理论。施米特认为,政治的标准就是划分敌友的能力,就是清晰的敌我意识。这种敌友划分主要是就国家与国家关系层面而言。[13]施米特关于政治的定义是一个双重否定。它既否定了建立未来天下大同世界的现代文明理想,也否认了构筑完美政治理念的古典文明理想。施米特认定政治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宿命,连反政治的自由主义也无法摆脱政治的逻辑。[14] 由此,施米特揭示了一个可怕事实:政治是人类生活的生存命运。
人类理性应该如何面对这一残酷事实呢?
古典政治哲学的办法是通过语言辩证法建立一个完美的理想城邦,一方面以此来缓和人类生活的苦痛,另一方面以此来提醒人类建立文明的无比艰难。现代政治哲学抛弃了古代的完美政治理想,转而寻求建立天下大同的未来世界,以此来克服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和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状态。施米特的政治理论所代表的德国虚无主义则放弃了古今文明理想,转而采取勇敢直面冷酷政治事实的态度。
五
勇敢面对赤裸裸的人间政治事实,这是施米特政治理论的真诚态度。在施特劳斯看来,这种真诚态度既是对现代政治哲学未来完美国家理想的反叛,也是现代政治哲学对古典理想进行历史化的必然产物。它彻底放弃了古今政治哲学都抱有的理性文明理想。德鲁里看到了,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一样对现代政治哲学路线持批评态度。但是她没有看到,施特劳斯并不像施米特那样彻底放弃理性原则本身。
在《施特劳斯与美帝国的政治》中,诺顿(Anne Norton)试图区隔施特劳斯和施特劳斯分子。她将新保守主义仅仅与施特劳斯分子绑在一起,而把它与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分别开来。但诺顿的著作总体上流于轶闻故事,未能从思想上论证施特劳斯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15] 戈特弗里德(Paul Gottfried)则一方面认为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和新保守主义的关系不像德鲁里所说的那样直接,另一方面又认为两者并非全无关系。
[16] 虽然路线持中,戈特弗里德毕竟也没有阐明,施特劳斯所论古今之争及其文明理想和德国虚无主义之间的纠葛。史密斯(Steven B. Smith)的新著《阅读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犹太教》对施特劳斯和美国政治做了较为稳健的分析,从思想上分别了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精神。但由于过分强调了施特劳斯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史密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哲学理念的坚持。
[17]
德鲁里认为施特劳斯政治思想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这与她视施特劳斯思想为德国虚无主义的极端化这一立场密切相关。德鲁里断定,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将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神学化,因此也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极端化了。[18] 这个断定看到了施特劳斯和施米特批判现代自由主义的一致性,然而它忽略了,施特劳斯对施米特及其德国虚无主义精神的批判毫不亚于他对现代政治哲学的批判。其实,美国新保守主义所奉行的政治理念和政策暗中实行的是施米特的政治理念,而不是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种嫁接。它试图通过采取施米特的政治原则以延续现代政治哲学的文明理想,从而在新世纪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帝国。
施特劳斯始终都反对一个世界帝国的建立,遑论采取施米特的政治原则。他始终秉承古典政治哲学精神,通过辩证法建立语言中的完美城邦,并悉心教导其必要性、可行性和可能性。
--------------------------------------------------------------------------------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07JA720011)。
[1]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24.
[2] Strauss,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Leo Strauss, ed. Thomas L. Pang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 31-32.
[3] 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刘华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1页和第168-169页。
[4]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179; Idem,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 47.
[5]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196.
[6]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p. 33-34.
[7] Strauss,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p. 64.
[8]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p. 34.
[9] Paul J. Bagley, “On the Practice of Esoteric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3 (1992) 2: 231-47.
[10] Michael L. Frazer, “Esotericism Ancient and Modern: Strauss contra Straussianism on the Art of Political-Philosophical Writing,” Political Theory 34 (2006) 1: 33-61.
[11]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p. 34.
[12] Strauss, “German Nihilism,”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6 (1999) 3: 353-378. [edited by David Janssens and Daniel Tanguay]
[13]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8-148页。
[14] 施米特:同前引,第195页。同参施特劳斯:《〈政治的概念〉评注》,刘宗坤译,载《施米特与政治法学》,刘小枫编,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15] Anne Norton, Leo Strauss an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参见陈建洪:《评诺顿〈施特劳斯和美帝国的政治〉》,载《美德可教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61-263页。
[16] Paul Gottfried, “On Straussian Teachings,” Modern Age (Winter 2007): 77-81.
[17] Steven B. Smith, 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p. 156-201. Cf. Jianhong Chen, “Review of Reading Leo Strauss by Steven B. Smith,” Sino-Christian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ble,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2 (December 2006): pp. 220-225.
[18] 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第95-109页。
(原刊《世界哲学》2008年第1期:第51-55页。)